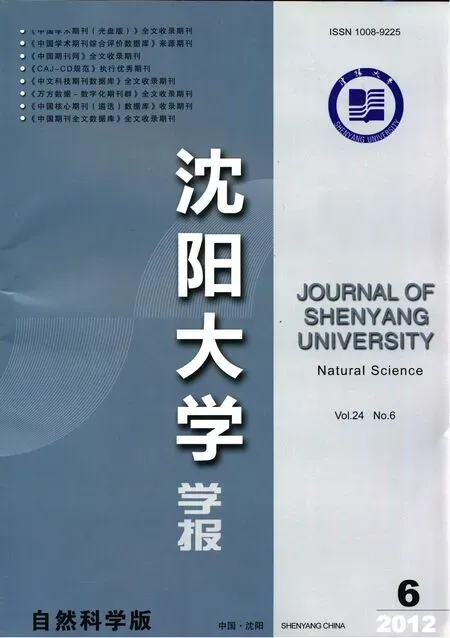论格非小说中的孤寂生存意识
2012-04-12常健男
常健男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格非的作品好比一个世界,“我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1]在格非的世界里,他用一个个神秘、曲折、悬念迭出的故事,用一幅幅意象别样的画面,展现了一个个历史与现实的梦幻。梦远不及现实那样真实,但是格非在小说中营造的梦境却深刻地照进了现实。他感触到的生存境况是孤寂的,这种孤寂的漂浮感贯穿了历史与现实,贯穿了城市与乡村,贯穿了人们冲破欲望和寻找希望的整个过程。
一、人生的孤寂感与历史和现实
1.人生的孤寂感
对于生命意义、生存状态的追问是格非小说中一直贯穿的主题,格非所体悟到的是一种生存的孤寂,一种生存的绝望。孤寂感是一种荒诞又虚无的存在,也是一种边缘的存在。格非索性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边缘》。“边缘”无疑是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处于时间和空间的边缘。“我”的人生故事分为“少年麦村阶段”“军旅生涯”和“晚年麦村阶段”。在生命的尽头,“我”体悟到了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如何超越在漫长的人生舞台上上演的悲喜剧带给人们的震颤。《边缘》试图通过一位老人的灵魂超度和升华的过程,来完成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老人经历了人生所有的苦难,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只有安静的凝视,没有扭曲的挣扎。格非以一位作家的目光,充满深情地注视并关切着人类的命运,使我们感受到了在无边的时间和空间里,个人也只是在极其边缘的位置上感受着喜怒哀乐和离合悲欢。孤寂感也是一种恐惧力量,一种异己力量。格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讲述了一个类似“游戏”的故事,这个游戏的题目是:敌人是否存在?敌人到底是谁?格非把“敌人”作为一个虚无概念的象征,“敌人”并不曾真实存在过,而是具有神秘性、荒诞性的色彩。赵少忠心理的恐惧,从对敌人的仇恨变成了心理的扭曲,这种恐惧又无处不在,赵龙、赵虎、梅梅、柳柳等人也都受到了这种恐惧的感染,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恐惧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当人处于这种状态中,人与世界之间就会分裂,个体既失去了一切可以依附的东西,又被异己的力量所包围。”[2]因此,个人就会完全地排除在外,孤独脆弱的感受在内心相应地产生。
2.历史和现实中的孤寂
(1)历史的回忆。展现隐秘的历史是格非喜好表达的题材,许多故事也都被格非放置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写革命者张季元与少女陆秀米之间的爱情的《人面桃花》,赵少忠一家每个人内心心理纠葛的《敌人》,还是姚佩佩与谭功达之间命运契合的《山河入梦》,都是在一个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人物命运的流转,都是远离格非自己所在年代的一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格非从未亲身经历过这些漂泊的寻梦过程。但是格非通过远离现实的“猜谜游戏”表达他对历史时光的想象,对人类集体精神的回忆,而“革命”也是格非对历史事实最常态的表现,在格非看来,革命无疑不是对人性孤寂、迷乱的一种展示。
中篇小说《迷舟》用一个绝对的“历史实录”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在小说的最开始有一段背景描写:“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兰江两岸……萧旅长的失踪使数天后在雨季开始的战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3]18格非喜欢用明确而细致的历史叙事方式把故事赋予真实的史实性,而在叙述展开的过程中解构其真实性,构筑叙事的迷宫。萧和他以前暗恋过的远房表妹杏、杏的丈夫三顺、萧的母亲、哥哥、警卫还有那一把手枪,他们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又不可预测,萧没有办法把握自己不可捉摸的命运和归宿,个人在历史中的处境如此无奈和荒谬。“当萧朦朦胧胧地想到了这一切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在夜幕中消失了。”[3]33当萧最后被冠以叛变的罪名并被警卫开枪打死时,他与母亲矮小的身影互相凝望,却再没有办法拥抱她。人生结局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可捉摸和无奈是孤寂生存的一种展示,还有一种是个人在历史中漂泊不定的人生命运。《风琴》书写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通过冯金山、王标,特别是读书人赵瑶在面对日本人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表现,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漂泊。“在这个文本中,格非像对待他其他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一样,把带有公共性的历史故事和带有私人性的个体生命体验故事并置,使它们互相交叉重叠,前者往往被后者侵扰甚至遮蔽,两相对峙中,个体的生命体验总是占上风。”[4]赵瑶在日本人到来之时,仍然固执地留守那个落寞的庭院,他内心焦灼和悲凉的情绪通过悠扬的风琴声,永远飘在历史的时空里。这两篇小说是格非将故事放置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代表作,历史不是现实,但格非把眼光对准整体上的人们,透过集体对历史的回忆来追忆生存在历史时空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漂泊命运。
(2)现实的欲望。如果说再现和回忆是格非揭开历史迷雾的方式,那么《欲望的旗帜》《不过是垃圾》等小说则是格非描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最为熟悉的现实的作品。故事主要发生在高校校园,在这里格非感同身受地将知识分子的自身困惑和精神危机进行展示和书写。在看似单纯、美好的象牙塔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欲望的诱惑:爱情的欲望之于张末,理想的欲望之于宋子衿,名利的欲望之于老秦,等等。“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欲望的描写,我们要抵达的仍然是对自身困惑于矛盾的思考,对人存在意义的探索,这是文学的终极目标”[5]。格非持续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也是他把眼光投向现实的表现。知识的能量并没有给他们带去生活的希望和内心的宁静,而是更加无力、尴尬。他们始终被命运所主宰而不是去主宰自己的命运。《欲望的旗帜》里,宋子衿是一位对理想执著追求的知识分子,他永远像一个孩子在追求着遥不可及且并不真实的梦:导师的情妇、怀孕的女研究生、身上烙斑的叙述,都无法让他触碰到梦想。他的梦中有他的妹妹,当真实的妹妹到来时,他的梦却彻底碎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现实和理想对立的困扰,最终走向了肉体的毁灭。与宋子衿不同,张末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的一生追求着爱,又在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的矛盾之中痛苦。书中多次提到张末那幅憧憬的画面“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她走来说‘我们回家’——一副充满纯真与美好的画面,这个画面缠绕了张末的一生并指引着她寻找归宿。”药剂师引发了她最初对爱情的渴望,曾山给了他安定的婚姻,邹元标给了她生命原始的欲望,但最后她都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自己忍受着思念的痛苦。格非通过张末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来表达他对于生活在现代性中被异化的人的揭露和反思,格非自己曾解释说:“这部小说外表的讽喻特征也许掩盖了我写作时的基本动机,事实上,它只是一把刻度尺。我想用它来衡量一下废墟的规模,看看它溃败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们为了与之对抗而建筑的种种壁垒,比如说爱情,是否能够进行有效地防御。”[6]格非以高校为缩影来窥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为精神理想坍塌的孤独封闭的现代人寻找精神的出口。
二、对生活破碎处的展示
在格非所有的小说中,无不展现了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下,在灰色、边缘的生活破碎处,人们的挣扎、寻找、希望和超越现状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们,如何勇敢地面对和超越现实,无论是神秘的“花家舍”还是格非心中的“乌托邦”,都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它的直面。
1.乡 村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人的影响很大,更何况是对一位小说家,乡村的记忆对格非来说尤其重要。在格非的笔下,对乡村景象的不倦描绘说明了他把乡村和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当成他的回忆和想象力的延伸。在乡村这片充斥着神秘、隐晦、温情和永远说不尽的风俗和历史内涵的土地上,格非书写了人类最孤寂、最困惑的生存境况。一个叫“麦村”的村庄是格非许多小说中同时出现的一个村子,在《追忆乌攸先生》《青黄》《边缘》中都出现过,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的描述大致想象出它的样子。一个位于江南的村庄,阴雨连绵,寂寞安静,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里的宁静,这也许是格非对儿时生活环境的难忘记忆。在这些记忆基础上,格非写出了这里的欲望、虚无、血腥和暴力。“梅雨”是他小说中的乡村经常出现的天气。首先,雨水、雾气很容易让人产生心绪烦躁、原先预定的生活被完全打乱的感觉,因此,人们在这种天气之下常常出错。《雨季的感觉》中,正是在梅雨天气里写错请柬的褚少良的失误,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和猜忌。格非也采用了错乱的叙述方式和结构讲述这个故事,增添了神秘和悬念色彩。其次,“梅雨”本身会让人联想到生命形式本身,雨水是欲望的滋生条件,外界的一切在连绵不断的雨线中辨不清真伪,探究虚实的欲望会随着雨水的流淌产生。雨过天晴后,一切恢复平静,所有的躁动偃旗息鼓,人们的内心欲望也随着晴朗的阳光消失在背后。只有雨季和雨水天气,村庄才会露出它本来的面目。这里不仅有格非个人的童年记忆,同时包含了人类隐约的童年记忆,“……如鲁迅和他笔下的‘鲁镇’、沈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这些地方因为经过作家的审美把握和情感烛照,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在它的肌理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人性内涵。换句话说,这样的地方已由日常意义上的生活具象上升为积淀着个体生命创建的艺术意象,……有着强大的象征符指和意义结构功能。”[7]这些乡村无疑是荒诞又愚昧的,本身的边缘性和孤立性致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异常孤寂的生存空间。
提到格非在小说中描写的乡村的边缘人物,就不得不提乌攸先生,生活在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村子里的一位知识分子。这个村子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噩梦,毫无生机、死气沉沉,只有一位叫杏儿的姑娘能够激起他心中的涟漪和对生活的期待。偏偏最后的希望又被打碎,杏儿被强奸,罪名却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要为这莫须有的罪名承担死刑的惩罚。对于他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所以他无需辩白,但是将这种亵渎的方式强加在他和杏儿的关系上是他所承受不了的。显然在蒙昧的村子里,乌攸先生的学识和医术是不被认可的,他的含冤而死甚至也不能激起人们的同情,相反族长所代表的暴力、野蛮却是令全村人生畏的。乌攸先生在乡村中的落寞和孤独的生活状态没有办法得到解救,命运注定是悲哀至极的。“具有强烈活命意识的乡村对于精神层次具有本能的漠视,没有任何关于生存意义的质疑与否定,乡村不再是精神田园,而是以一个封闭、愚昧、永世轮回的孤独地域形象出现。”[8]乌攸先生在冷漠的乡村中找不到同类,泯灭了生活的希望。内心充满痛苦的乌攸先生与村子中极有威望但浑身充满暴力、荒诞的族长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2.城 市
如果说乡村依然拥有温情、宁静的一面,那么城市很显然是异常冰冷、绝望的地带,城市中的欲望是显现的、直露的,同时也是麻木的。“现代化”结果带来的异化,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困惑更加断裂。《欲望的旗帜》中的大学校园是城市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某高校。格非恰恰把与城市、金钱、商业最无关的学科哲学当做揭露对象。哲学本应该独立地徘徊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但是格非让我们看到的是哲学系的教授、讲师、大学生、研究生各种人物面对金钱、理想、爱情时的焦躁不安。小说里,贯穿始终的现象是举办学术会议,在一次会议中牵扯出一系列的人和事,但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会议的成果仿佛是浓重的烟雾弹,我们始终无法得知;相反,与严肃的会议毫无关系的吃喝玩乐、婚姻、欲望等一些内容却一次次地被曝光,学术会议完全变成了荒诞无聊的滑稽戏。在“欲望”这面旗帜下,是绝望的爱情、消逝的理想、永无止境的名利追求,而张末最后对自己一遍一遍地追问“怎么会这样?”也道出了格非的内心所思,不同的是张末在感受到荒诞的命运后是绝望和孤寂的,但格非在绝望的境况中依然在努力思考寻找希望的天空。
城市是被现代化“异化”较彻底的地方,城市中的人们在异化过程中渐渐产生精神危机,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也如此。《去罕达之路》中“我”和妻子荒诞的婚姻,说它荒诞因为这种婚姻不是单纯的爱情、责任的丧失,而是两人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封闭和隔阂,是一人对另一人彻底地责任推卸和心存戒备。在“异化”中,婚姻的困惑和情感的丢弃显得再平常不过。“城市的婚姻是变幻的,充满着太多不确定因素,它与急剧变化的城市社会形态相吻合。城市现代性观念中对于理性、平等、自由的渴望使每一个现代人失去了传统的感性、亲情、稳定与眷顾,个人在守护自我、追求自在存在的境界时,他人的存在对自我构成了威胁。”[8]可见,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异化的城市中变得荡然无存,这相对于人们在迷茫的城市中所面临的困境和迷惑来说,是更加可悲的。
三、对“花家舍”的眷恋
对生活破碎处的描写是格非经常在小说中展现的,同时他的小说中也有对于美好的生存环境和梦想的特定描绘,“花家舍”就是格非笔下缔造的一个梦境,在两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都有他对“花家舍”的复杂情感注入。“花家舍”如同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如同人类精神的“乌托邦”,那里是人们逃脱孤寂感的港湾,但却不应该是人们精神追寻的终点站。
格非把他对生存困境的复杂感受注入到《人面桃花》的主人公陆秀米的身上,《人面桃花》描绘了一个面若桃花的女子的传奇经历,也描绘出了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秀米面对父亲的出走,母亲的抛弃,被花家舍的强盗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又面对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死亡,她虽有过不安但更多的是勇敢的面对和承担。回到普济后,秀米的革命、办学都是在不清不楚的状态下开始的,就像书中写道的“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革命,没错,但他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时的秀米就像被命运推着,自己没有改变方向的能力,她等来了六指却早已失去了希望,她被自己的苦难遭遇刺痛了,流血了,她拒绝所有来客,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折磨和惩罚自己。最终她鼓足了勇气,赶了七八天的路前往改变她一生的花家舍岛,这时的她只想掌握自己的一切,而不是被未知的命运掌握。但直到最后也没能面对她一直追寻的历史和不忍触摸的那段往事,她还是离开了,“她知道,此刻,她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过路的船队,而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9]
秀米的人生和命运的苍凉漂泊,无不体现了格非心中孤寂的生存意识,他把秀米心中藏得很深很深的苍凉和孤寂给“挖”了出来。离开花家舍时她回忆起自己和韩六在窗边说话的场景,仿佛听见了韩六在她耳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其实,秀米一直在正视和直面生活及命运,心中有着理想化的“乌托邦”式冲动,即使失败,即使最后的转身也不是逃避的表现,而是她明白无论如何也始终无法把握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王观澄的大同梦想、张季元的革命、父亲的宝图实际上是一体的,那是秀米的“桃花源”,是她的梦想。“格非以一本张季元遗留的日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欲望化的主题和人生难以摆脱的‘围困’,而在文本之外,格非妄图把握历史,通过距离感制造神秘的渴望,对于世纪初中国文坛的现状而言,也确然不失为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诗意行为。”[10]秀米对于花家舍的眷恋并不是因为那里如梦幻般美好,而是因花家舍是她追寻理想和命运这一冲动和激情的象征,试过后才知道:现实会成为过往,而梦终究还是梦。
格非就是在这样矛盾的情绪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花家舍的结局,因此他没有使秀米停止追寻,使秀米的生命在《山河入梦》的谭功达身上得以延续,同时格非也开始了新的思考与追寻。
[1]格非.写作的恩惠[M]∥塞壬的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02.
[2]向仕艳.论格非90年代长篇小说的思想意蕴[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2):7.
[3]格非.戒指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4]许瑶.论格非中篇小说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认识[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11.
[5]余中华,格非.我也是这样一个冥想者:格非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8(6):46.
[6]格非.序跋六种[M]∥格非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224.
[7]董学武.欲望的幻想:格非小说中的乡村意象[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5(2):22.
[8]吴妍妍.格非的城市批判及其困境[J].当代文坛,2007(4):34.
[9]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276.
[10]张立群.论格非小说的“神秘性倾向”[J].泰山学院学报,200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