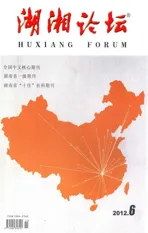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2012-04-12邓名瑛
邓名瑛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邓名瑛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最近一些年来已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学者着眼于中国当代政治伦理学的体系建构;有的学者从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当代的政治伦理问题;也有学者回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资源,力图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建构提供借鉴;还有的学者专注于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比较,力图通过比较促成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会通。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政治伦理理论的完善、丰富与深入以及政治伦理学学科的繁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笔者以为,在努力探索当下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固然十分重要,而与此同时,探索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使政治伦理从观念层面转化为现实层面,或许是一个更为重要因而也是更为有意义的课题。
一、儒家德治主义传统及其特征
“德治”是与君主专制的“人治”政治模式紧密联系并与法家的“法治”相对的范畴。概括而言,包括如下两项内容:第一,由有德者治理天下。所谓“修德配命”“敬德配天”“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以道德教化天下。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的德治具有三个典型特点:
第一,以德配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在追问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时,总是把它与“德”联系在一起,按照中国传统儒家的看法,就是“德位统一”,有德的人才配享有位。如果说,在汉语系统中,“王”是人间权力的最高拥有者,那么“王”字的词型结构恰好体现了“以德配位”、“德位统一”的权力观。“王”字的三横象征天地人三才并立,中间一竖象征对天地人的贯通,这种贯通是道德上的贯通,这就是说,权力首先来源于天,天把某种美好的品德赋予了每一个人,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把上天赋予我们的美好德性展示出来,这种人就可以称王。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德的人不一定有位,但是有位的人按照理论来讲,必然是有德的。在“德”与“位”的关系上,讲究以德为先,以德取位,德位一致。《中庸》道:“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这说明与地位相匹配的功名利禄等东西都是以德为基础的。
儒家“以德配位”的思想又是与“民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儒家的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德,关键是看他是否能体恤民情,贴近民心,顺乎民意。至于为什么把这种人看做是有德之人,最根本的还是“天道”,因为至高无上的“天”正是以民为本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可以说,儒家“以德配位”的思想逻辑地包含着“立君为民”的价值诉求。
第二,德化天下:治理国家的方针是德主刑辅。德治主义主张治理国家的基本也是主要的方式是对天下之人进行道德教化,法律的强制是次要的,这就是“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汉书》云:“道之以德教者,德教5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汉书》卷四十七)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春秋繁露》)朱熹也说,“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第三,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主才次。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有才的人如果没有德,是万万不能作为人才的。当德和才两者发生矛盾时,是选择有德的人而不是有才的人。这与法家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儒家主张以德为主,以才为辅,“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才是为德服务的。“是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资治通鉴》)可看出儒家选拔人才的明确标准是重德轻才。
从实践层面上看,德治乃是一个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互动过程,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德治就不光是对形于外的人群、阶级阶层、社会以及家庭和国家、民族的治理,也是对隐于内的个体的心理意识的治理,而且,从德治主义的立场上看,后一方面显得更为重要。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在儒家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后来唐代的韩愈所概括的儒家“道统”:“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原道》)。儒家认为,政治权力的存在依据就在于它能否切实地承载这一道统的延续,若能够便是合理合法的“政统”或“正统”,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二、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
上述对儒家德治主义思想的分析大体上涵盖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应,儒家还建构了把这套政治伦理付诸实践的路径。大体说来,这一系统的实践路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方面;一是个体行为方面。
从制度设计方面来说,权力的获得是“君权神授”。儒家特别推崇尧舜禹三代以上的禅让传说。这种禅让传说详细描述了尧舜禹三代以上的帝王谱系以及由这一谱系所表征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政治权威的确立过程,尽管不同的典籍对帝王谱系和权力转移以及权威确立过程的描述有出入,[1]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政治权威的确立都是以权力接受者的德行为依据的。如尧舜禹都是因为贤德而被他们的前任选作接班人的,每个被选中的人在位时都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因而也是受民爱戴的。被选中者不仅仅是他的前任认为其有良好的德行,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在实际生活中切实表现出自己的良好德行。
与禅让相关联的政治权力的转移方式是“革命论”,对此,儒家判断这种权力转移是否合法有效,仍然是以权力的获得者是否具有良好的德行、是否顺从民意、是否以民为本为依据的。例如,历史上的汤武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在汉景帝时代辕固生和黄生就有激烈的争论,黄生认为,汤武推翻桀纣的统治而获取权力是“非受命,乃弑也”,实际上是犯上作乱,其权力的来源不具有合法性,但辕固生认为:“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2]P122-123可见,儒家认为,当权力的拥有者丧失自己的德行时,也就丧失了继续拥有权力的资格,因而那些有德之人推翻其统治,夺取其权力,乃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具有其合法性依据的。
制度方面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礼制的创设。按照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理解,“礼”是用来辨等级、正名份的。不同的等级意味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严守自己的等级和名份,即严守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严守自己的等级和名份,享受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的权利,同时也尽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的义务,那么,整个社会就能达到和谐的状态,“礼之用,和为贵”。“礼”之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其依据仍然是不同人的德行的差异,所以,在儒家那里,人的差异是德性的差异,君子与小人、圣贤与愚不肖的区别皆导源于此。当然,这种等级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结构,而是可以变化、可以流动的。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同时又提倡弟子“学而优则仕”,两者合观之,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地位较低的人通过接受教育并培养自己良好的德性,也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
制度方面的第三个重要内容乃是人才的选拔问题。在先秦时代,政治运作的人才除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君权神授”外,其他层次的人才则有分封制和世袭制两种。分封和世袭与“以德配位”的政治理念存在着可能的冲突,例如,就分封制来说,最高权力拥有者具备相应的德行,但与其相关的亲属或亲戚就不一定具备相应的德行,因而也不一定具备拥有某种权力的资格。世袭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先辈具备的德行后辈不一定具有,同样也不具备拥有某种权力的资格。若要把“以德配位”的政治价值理念贯彻到底,则必然有相应的制度作为补充。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较为严格地限制了人才流动外,汉代的乡举里选以及自隋以后产生并逐渐发展的科举取士制度都是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特别是科举制的兴起后,世袭制逐渐走上衰亡。
从个人行为方面说,既然德治主义的政治伦理强调“以德配位”、“德主刑辅”、“徳主才次”,那么,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不断养成自己良好的德行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一方面,既有的权力拥有者要继续保有相应的权力,需要持之以恒第具备相应的德行;另一方面,非权力拥有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自己的“小人”、“愚不肖”的身份,甚至成为儒家所说的那种“人”,也必须不断进德修业,去培养自己的良好德行,于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
应该指出,由于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的过程,而儒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理解总体上过于理想化,因此其所设计的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也是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儒家所构造的政治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而在利益博弈中更有效率的法家政治伦理倒是事实上压倒了儒家政治理想,“阳儒阴法”一直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生活史的真实写照。“阳儒阴法”、“儒法夹杂”的政治运转模式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上所说,儒家的政治伦理及其实践路径对当下中国的政治伦理的建构是否还有借鉴意义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去发掘,怎样去创造性转化。
三、儒家政治伦理实践途径的启示
笔者以为,当今中国政治伦理的理论建设固然应该从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吸取积极的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认真思考其论证问题的方式,包括经验与教训。
众所周知,从伦理实践的角度看,一套伦理价值体系对社会现实生活究竟能发生多大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受这套价值系统所规范和约束的社会成员的认同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受这套价值系统规范和约束的社会成员对这套价值系统的敬畏。这种敬畏或者是生发于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对这套价值系统的信念;或者是生发于某种外部强制力量。而无论是内在的信念还是外在的强制,都与这套价值系统本身的一个特点相关,这就是,这一价值系统本身必须具有神圣性的目标指向。没有这种神圣性,外在的强制就缺乏理由;没有这种神圣性,内在的信念就缺乏基础。
以此观之,儒家伦理包括儒家政治伦理在其源头和目的指向性上都具有神圣化的特点。从源头来说,儒家把伦理道德的源头奠定在超越性的“天理”或“天道”上,认为“天理”或“天道”乃是伦理道德的终极性源头,而“天理”或“天道”又内在于人从而也是作为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终极性依据。在这样一种思想架构中,人的本真性存在乃是作为“天理”或“天道”的承载者而呈现出来的,人对伦理道德的恪守就既是“天理”或“天道”的实现,也是人自身真实存在的实现。
与这种终极性源头相适应的儒家伦理包括政治伦理,其目的指向性也具有神圣性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儒家对公私、义利、理欲等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在公私关系上,儒家强调重公轻私,克己奉公;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在理欲关系上,儒家强调以理制欲,以理导欲。这就是说,公、义、理才是行为的目的之所在,私、利、欲不过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上述思想的简练而精当的表述。
正是因为“天理”或“天道”这种终极性源头所赋予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目的指向性上的神圣性,才使得儒家伦理两千多年来或是借助于人们对内在“天理”本性的自觉而形成的信念,或者借助天理的外在形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而形成畏惧之心,从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作用。儒家伦理能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干,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决不是偶然的,其终极性源头和目的指向的神圣性实在是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在政治活动领域利益的角逐更为鲜明和直接,因而效用直接、效果明显的法家思想经常对儒家的政治伦理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但睿智的统治者却始终把儒家政治伦理放在首位。当然,儒家伦理包括儒家的政治伦理在追求超越的同时,又具有世俗化色彩。儒家对私、利、欲的轻视并不等于排除甚至剿灭,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其现实合理性。这种思想架构既体现了儒家在人的理解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同时也为神圣化的目的追求与世俗功利化的目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儒家,“德”与“位”紧密相联,而相关的“礼”则又把“位”与“禄”相联,“位”乃获得某种“禄”的资格和条件,以此类推,“德”就可能成为获取“禄”的手段和工具。于是,现实生活的情形可能恰好与儒家的价值诉求发生颠倒性错位,即人们培养相应的德行仅仅是为了某种功利性追求,这一点从汉魏至晋至南北朝的人物品第的评定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所证明,形式和内容的脱节使伦理道德成为虚伪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对于这样的冲突,尽管儒家提出了“下学而上达”的解决方式,即既不排斥功利又超越功利的方式,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
儒家在政治伦理上的上述致思路径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首先,重谈伦理道德的终极性源头和目的性指向的神圣性乃是使伦理道德发挥其作用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研究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其次,处理好伦理道德的神圣性、超越性与世俗性、功利性之间的关系,避免使道德沦为手段和工具,同样也是十分紧迫的课题。从世界历史看,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对人的理解也片面化为理性经济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成了理性算计的动物,讲伦理道德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在世俗功利的追求中,道德的神圣性丧失殆尽。这种状况使得重建伦理道德的神圣性显得更为迫切。
在儒家所建构的政治伦理的实践途径中,个体的德性修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建设也是非常重要,传统儒家不仅有完整的修养理论,还有完整的修养方法,今天,在政治伦理建设中,修养方法比起修养理论来说也许更为重要,而儒家能给我们提供的积极借鉴也在于此。当然,个体修养和环境的改善是并重的。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由于过分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社会环境的批判,导致把世俗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归因于个体自身不努力改造和完善自己的结果,这一点乃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1]见《庄子·胠箧》、上博简《容成氏》、班固《汉书古今人年表》.
[2]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