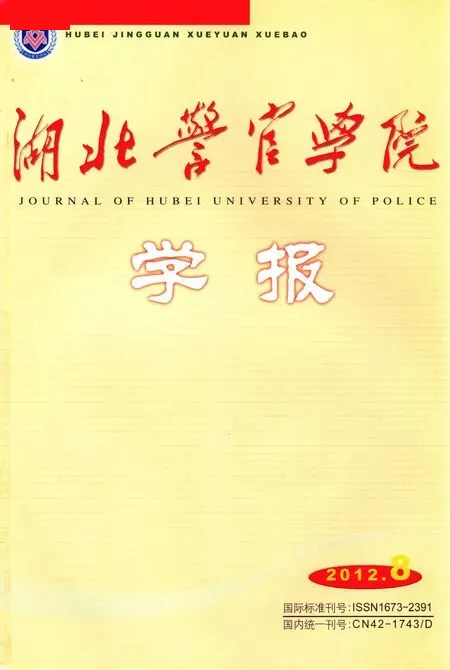论侦查中逆向思维的运用
2012-04-12杨静
杨 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论侦查中逆向思维的运用
杨 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侦查主体思维素质的核心是侦查思维的创造性。创造性侦查思维是一种发散思维,而在发散思维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逆向思维去分析问题,故逆向思维是侦查主体思维素质的重要体现。面对形形色色高智商的刑事犯罪,特别是在信息化背景下,逆向思维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换位思考以突破瓶颈、颠倒方式以为我所用、移挪作用以化弊为利、翻转观点以重构思路。
侦查;逆向思维;顺向思维
思维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以知识经验为中介而实现的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应。[1]简单地理解,它就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大脑活动过程。侦查思维,就是侦查人员在侦查办案中的思维活动。它是思考侦查问题的手段、工具和技能,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根据相关证据线索,对案件中的人、事、物、时、空以及有关信息进行思考,以发现案件真相。
侦查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破案效率。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侦查机关侦查办案的格局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然而,技术层面的发展并不意味思维层面也在随之进步。由于人类思维的强大惯性和隐蔽性,侦查思维与一切显露于外的技术相比,总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滞后性。
这种滞后表现在我们思考问题时易倾向于单方向的思维模式,即从一个方向去看事物,而不会从无数个方面、多个角度去看问题。如在运用侦查手段和措施时,往往只抓住单个问题,遵循某种固定的思维,确立单一的目标;往往不善于在对立统一、多样性统一中思维,而是拘泥于两极的绝对对立之中,习惯于在非此即彼、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2]侦查工作的实践要求我们的侦查员要在侦查过程中善于运用逆向思维,在侦查过程中把握住对立统一。
逆向思维是发散思维常用的方法。逆向思维是一种对立的多向思维,其客观根据是事物内部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顺向思维是指顺着常识去想,或顺着客观事物的某种顺序去想。逆向思维则是相对于顺向思维而言的,它将顺向思维颠倒过来,朝相反的方向去想问题,以达到豁然开通的目的。
下面列举几个具体案例,阐述如何在侦查中运用逆向思维。
一、换位思考,突破瓶颈
换位思考,即交换位置,从行为人的角度去揣测行为人在当时情境下会做出何种行为,或做出行为是出于何故,从而解疑释惑,走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这里的行为人不仅仅指犯罪行为人,还包括受害人、证人等。
(一)把握情境
换位思考是一种“情境再现”,即将自己置于同样情境中会有什么行为。这一过程中,对情境的把握至关重要。这里的情境即是犯罪现场的各种现场环境情况,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如当地的文化习俗、行为人的智力、思维水平。例如,某地发生一起凶杀案,饭店女老板郭某被杀死在酒店大厅。饭店卷闸门上卷,玻璃门自然关闭。死者全身赤裸,仰卧大厅中央,嘴被布裤头塞住,双手被长筒尼龙袜反绑于身后,双脚用一白底红花上衣捆绑。死者胸腹腔被剖开,心脏被挖出扔在头部前方,肠子外露,双乳及臀部组织置于前方的两个木凳上。现场有数枚鞋印,但无翻动痕迹,无财物丢失。
在这个案例里,令侦查员疑惑不解的是凶手为什么在死者死后将其解剖,并将其器官置于木凳上。这是不是某种宗教仪式?侦查员根据对当地民俗风俗的理解,宗教仪式的可能性不大,迷信倒更有可能。结合当地迷信的观点,凶杀可能认为,人死后捆住双脚鬼就不会附身,而把解剖后死者的双乳、臀部放在比身体高的地方仍能保持死者身体的完整。据此,认为凶手应是极度迷信的人。根据这一特征,侦查员展开排查并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二)代入思维
代入思维,即在已经把握情境的前提下,将自己想象成行为人。如果我是他,我会想什么,我会怎么做。代入思维在追逃工作中是最有效的。
在近期开展的清网行动中,某地公安机关仅凭20多条短信就劝服潜逃19年的嫌疑人张某自首。在掌握嫌疑人家庭现状(家中有幼子,父亲身患绝症)后,侦查员认为嫌疑人并未丧失本性。如果侦查员是嫌疑人,家庭有如此情境,又有中肯的规劝,肯定会主动投案自首的。于是,侦查员根据掌握到嫌疑人的手机号码,连发20多条短信。如“小张:劝你立即投案自首,理由很简单……放下心中的‘石头’别再太累,为自己好好活着,自首吧!”“小张:我们知道你的经历,这十年你都在赎罪,都在刻意做一些好事,救过人,抓过小偷,维护过正义……早点投案自首。我们等你!”“小张:看看你可怜的孩子,在等待着叫声爸爸……看看你老婆,时刻在呼唤着你的名字……看看你残疾的父母,无刻不在盼望着团圆……还有你自己不争气的身体,要再逃跑到何时……自首吧!等你。”最终,嫌疑人在这几条短信的感染下投案自首。
二、颠倒方式,为我所用
颠倒方式,是指就事物起作用的方式从相反的方向思考,以引发创意。事物都有自己起作用的方式,它同事物本身的性质、特点等密切联系。如果从某种需要出发,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某事物起作用的方式发生颠倒,那就有可能引起该事物的性质、特点、作用相应地发生改变。基于这种客观联系,侦查主体可以将事物起作用的方式倒过来进行考虑,使一些被动因素为我所用。
颠倒方式在审讯中运用得最为普遍,例如“囚徒困境”。这虽然是个博弈论的经典模型,但也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运用。这个模型讲述了这样一个侦查过程:某富人家中被盗,本人也被杀死在家中。侦查员锁定了两名小偷,并从其住处找到赃物。但两人只承认盗窃而否认杀人行为。两人口供一致,似乎结成攻守同盟。侦查员将两人分开关押并分别进行讯问,并告诉两人:“你们的盗窃罪证据充分,所以你们都坦白交代,可以判你们8年。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罪行,我可以判你无罪,立即释放,但你的同伙要被判9年。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将被判刑9年,他无罪释放。”但实际上,根据现有的证据,他们如果都不坦白杀人和盗窃的话,最多被判一年。
我们先暂不论这是否符合法律法理规定,就单纯对侦查员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这两人如果都不坦白的话,那么也就是他们的最好结果,即最多判一年。但侦查员为什么不担心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因为侦查员考虑到他们两人结成攻守同盟的根本原因,即利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在于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会顾及对方的利益,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对方或者指望对方具备合作精神。这种利益的作用方式本来会让他们结成看似稳固的同盟,但实际上只要被侦查员反利用,将这种驱动结合的方式变成瓦解同盟的方式。最终两人同时选择了交代杀人和盗窃。
三、移挪作用,化弊为利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对于人、事,我们不光要看到它的弊端,也要看到利处,要尽可能地促使其原有的弊端变为利端。在侦查活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利用违法犯罪人员侦控同类违法犯罪分子,包括刑事特情的运用,以及“控而不抓”、“放长线钓大鱼”等。这是逆向思维中颠倒、移挪作用的最好见证。
某县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外地青年女子常常出现在汽车站附近,经常在汽车站进出口处向行人发放名片。经查,该女子散发的名片上写有“办理证件、出售发票”以及联系方式等字样。后根据各方面收集到的证据证明,该女子就是本地某贩卖假发票团伙的重要犯罪嫌疑人。随即进行布控,但未发现有人与她接头。该女子登上去省城的客车,警方为稳住对方,没有采取相关措施。
没几天,警方获悉该女子返回该地,便迅速进行跟踪,发现该女子仅与一名中年男子接头碰面。为不打草惊蛇,民警再次放弃抓捕,继续监控。后来,该女子又突然前往省城。这次民警没有脱梢,在省城警方的配合下发现该女子与一名50多岁的男子会面,但没有进行相关交易,警方再次放弃了抓捕。
此后十多天里,该女子与50岁男子在当地汽车站附近碰面。这次不仅是见面,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在他们交易时,民警从天而降,缴获大量假发票。面对大量现实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了犯罪事实。随后,警方根据嫌疑人提供的线索,乘胜追击,来到嫌疑人在省城的租住屋,当场缴获各类假发票1700份、手机短信群发器3个、手机卡10多个以及大量的伪造身份证、印章和假证件。通过长线侦查,公安机关捣毁一个假发票储藏窝点、三个传播涉税违法信息窝点,缴获假发票6800份,涉案金额达126万元。
在该案中,警方已有证据证明该女子是犯罪嫌疑人,具备了抓捕的法律许可。但是如果将其抓捕了,不利因素还是很多的。如赃物较难起获,其他同伙无法掌控,组织难以破坏。如何化弊为利,变被动为主动,这是面对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在本案中,侦查主体运用逆向思维颠倒作用,利用嫌疑人一定会与其上线交易这个客观事实,放长线钓大鱼,在控制嫌疑人的过程中,顺藤摸瓜,逐一打击,最终一网打尽。
四、翻转观点,重构思路
人们的思维在发展,犯罪人的思维也在发展。犯罪人越来越了解侦查员的思维方式。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施用各种伎俩,试图把侦查员的视线引入到完全相反的地方去。这个时候,需要侦查员仔细观察,在发现可疑线索时,能够运用逆向思维,彻底翻转一般观点,重新构建破案思路。
2003年郑州一案犯绑架一名小男孩后,给其父母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息,上面写着“不药用保经来下的雄门港处来结电生活费的雄们汉美那到前不向看于司望破的局面你孩子一定安全”。仔细一读,才知其意为“不要用报警来吓弟兄们,刚出来,借点生活费。弟兄们还没拿到钱,不想看鱼死网破的局面,你孩子一定安全”。
对于这封短信,侦查员分析认为,案犯是个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因为43个字中有一半是错别字。按照这个思路,侦查人员圈定了排查范围,但是无果。
侦查员于是重构思路。如果案犯文化水平低,还会用发短信的方式暴露自己的特点吗?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直接打电话。在整句话中,除了把“还”(音 hái)误读作“汉”(音 hàn)之外,其余拼音全部正确,除此之外还用了“鱼死网破”、“局面”等词语,从中不难看出案犯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较强的拼音能力和伪装能力。因此,案犯绝不是一个文化层次很低的人。案犯之所以采取这个伎俩,就是伪装自己,迷惑侦查员。这说明,案犯的文化水平还是相当之高,还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按照这个思路,侦查员重新确定了排查范围,通过一系列的技侦手段,锁定了犯罪行为人。
认识事物可以倒过来想,对作为客观事物反映的思想观点也可以倒过来思考。本案中,案犯使用错字连篇的短信,为侦查员下了套,企图使侦查工作误入歧途。但侦查员及时调整思路,颠倒了“犯罪行为人文化素质低”的观点,重新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这就是逆向思维中颠倒的运用。
总之,随着犯罪活动和犯罪手段的不断复杂化、智能化,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刑事侦查工作实践中,在运用侦查思维去进行逻辑推理和逻辑判断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在顺向思维遇到瓶颈时,应当尝试使用逆向思维来理清线索,重新建构思路,为侦查破案服务。
[1]刘黎明.侦查思维[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3
[2]芦鹏.试论侦查思维中的误区及其矫正[J].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9(6):54.
D631.2
A
1673―2391(2012)08―0012―03
2012—05—30
杨静,男,安徽含山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责任编校:边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