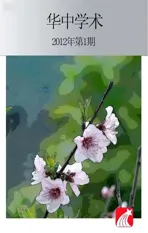新旧冲突中无所适从者的悲剧
——也谈《大雷雨》主题及卡捷琳娜、卡巴诺娃形象
2012-04-12曾思艺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俄罗斯文学研究
新旧冲突中无所适从者的悲剧
——也谈《大雷雨》主题及卡捷琳娜、卡巴诺娃形象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大雷雨》的主题是新旧事物的冲突以及女主人公在这一冲突中的无所适从导致的悲剧。卡捷琳娜的性格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具有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充满幻想,富于诗意,过于天真、单纯、浪漫,对现实生活的严酷、生活风习的残忍缺乏应有的准备与深刻的认识;又相当刚烈、十分冲动,且相当诚实,有深刻道德情感。而当时正处在妇女追求解放、恋爱自由的新潮思想与传统守旧观念激烈冲突的年代,因此必然导致悲剧。卡巴诺娃的性格也具有双重性:对外人颇为仁善,真心爱子女;却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人物和封建家长,是旧传统和习俗的保护者,不自觉地充当了用温情脉脉来杀人的角色。
《大雷雨》 主题 卡捷琳娜 卡巴诺娃
1860年《大雷雨》剧本公开发表,马上获得了俄国科学院的乌瓦洛夫奖金。接着,早已对奥氏此前戏剧发表过论文《黑暗的王国》的著名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就《大雷雨》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并且在当时俄国的文坛引发了争论。在这篇文章中,杜勃罗留波夫继续发挥了《黑暗的王国》的观点,认为奥氏戏剧中的一切矛盾和灾难,都是由于两个集团——老一代和年青一代、富人和穷人、一意孤行的人和逆来顺受的人之间冲突的结果,这是俄国整个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揭露了俄国社会专横顽固的完整体系和在家庭与社会事务中普遍存在的尔虞我诈,以及家里人自发地暗中反抗一家之长和封建专制,看到了在专制统治下逆来顺受的无辜牺牲者个性的毁灭,指出卡捷琳娜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她用自杀表明了自己的反抗,她的死带来了新的生机。甚至进而提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对俄国家庭中长辈的压迫和专断反抗到底,就应该充满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应该敢于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1]。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一度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权威观点,至今还是中国所有俄国文学史和涉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国文学史公认、通用的观点,如“专制统治思想与民主思潮的对抗性矛盾是人民要求改革现存制度而展开的斗争地反映……深刻地揭露了俄国黑暗现实,歌颂了人民的坚贞不屈的反抗力量”[2];“剧作家在《大雷雨》中提出了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妇女如何摆脱封建家庭中的奴役地位从而获得解放。剧本的基本冲突是新风尚与旧传统、被压迫者要求自由生活的权利与压迫者维护宗教法制秩序之间的斗争”[3]。
这一观点尽管有某种片面的合理性,但它遮盖了作品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用政治的解读垄断了其他种种可能的解读。作品的主题不只是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对此,与杜氏同时的两位著名文学批评家在当时都发表了与此不同的看法。一位是皮萨列夫(1840—1868)。他在《俄国戏剧的主题》中反驳了杜氏的观点。他认为,卡捷琳娜并非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并非一个完美的、积极的、与“黑暗王国”对立的性格,而实际上属于“矮子和长不大的孩子”那一类人,属于空想家,属于愚昧无知的群众,他们“从未尝到过思考的乐趣”[4]。另一位是格里戈里耶夫。他认为该剧的内容不能仅仅归结为对专横的揭露。他承认杜氏在论述“黑暗的王国”的文章中,“正确地看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所反映的一个生活方面”,并具体谈到:“《大雷雨》的问世,表明这一理论完全站不住脚。这个戏剧的某些方面似乎证实《黑暗的王国》作者的聪明思想是对的,但是,用以分析另一些方面时,文章提出的理论就根本不知所措了:用这种理论的狭窄的框框无法去套它们,它们所说明的完全不是这个理论所谈到的。”[5]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皮萨列夫稍嫌偏激),只是后来因为苏联把别、车、杜抬高到垄断一切的地步,以致我们至今还只能看到杜氏的观点。在细读原著后我认为悲剧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富于诗意、富于浪漫情怀与美丽幻想的女性,一方面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和宗教的熏陶,另一方面又由于爱情的燃烧、新潮思想的支持与帮助,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在两者间无法找到平衡点,不知何去何从,最后终于走向毁灭。这是只要有人类社会、有新与旧的交替就会产生的一种悲剧(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苔丝),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因而,戏剧的主题就是新旧事物的冲突,以及女主人公在这种冲突中的无所适从所导致的悲剧。对作品主题的正确理解,与对卡捷琳娜和卡巴诺娃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关系。
第一幕一开场,就是作家对于新事物的初步展现。登台的人物纷纷表示对当地死守陈规的“无教养”、“无知”乃至“残忍”的风俗不满:“我们这座城市里的风俗是残忍的……太残忍了!在小市民中间……除了蛮不讲理和赤裸裸的贫困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些人物中,有试图发明永动机造福民众的库利金,有决意报复老板的办事员库德里亚什(“可惜他家的闺女都还是黄毛丫头,没有一个大姑娘……我可是追求大姑娘的好手”),尤其还有根本不懂本地风俗、唯一不穿“俄式服装”、认为当地人太野蛮的鲍里斯,他们都透露了与当地唯利是图、一切只为个人打算、因循守旧不同的新思潮新信息。新思潮的根本点,就是追求独立自由,“用自己的头脑生活”(库利金语),尤其是追求妇女的解放、恋爱的自由。因为“在《大雷雨》问世的时代,俄国出版物上曾经大量地谈论‘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新的家庭生活方式’、‘恋爱自由’等等,不仅写写而已。在出版物所讨论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妇女解放也在以独特的‘家庭生活方式’实行着。六十年代及稍后,妇女解放现象按照某种规律性不断出现,表现为不担负夫妇义务,甚至不担负母亲义务,妇女有完全的自由”[6],而偏僻的小城只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潮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季洪的妹妹瓦尔瓦拉:一方面她大胆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背着母亲与情人不断幽会,最后甚至跟恋人库德里亚什私奔了;另一方面她竟然完全背弃竭力维护自己家庭安全的传统,一再鼓励甚至帮助自己的亲嫂嫂去背叛亲哥哥,和外人幽会——活活地把嫂嫂往外人怀里推。她这样做,就是因为按新潮观念,她认为母亲压迫嫂嫂,而哥哥也不能给嫂嫂幸福,嫂嫂在此没有自由和幸福,而一个妇女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尤其是恋爱方面的自由和幸福,所以她要帮嫂嫂。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又是死水一潭,循规蹈矩,一切按习俗办,照规矩办,驯顺地服从长辈的一切安排,以至外来人都感到“你们城里还是王道乐土,安居乐业”,“办任何事都有条不紊,平稳妥当”。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小城是整个俄国的象征。奥氏曾在散文中这样写道:“在莫斯科河南岸,人们很少自己思考,什么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和习俗,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莫斯科河南区不信任智慧,只尊重传统……那里对科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科学只是为了某种实际目的而对某事物进行的研究。”[7]莫斯科如此,伏尔加河上的小城也是如此,说明这个小城就是整个俄罗斯的象征,旧的规矩和习俗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新的思想已经出现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远不如旧的东西强大。卡捷琳娜一开始就置身于两种力量激烈冲突的环境之中。
对卡捷琳娜的形象,至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是从正面充分肯定的。“卡捷琳娜是全剧的中心形象。《大雷雨》的成功与不朽,与这个形象的创造是分不开的。她显示出的不只是诚实而智慧、温柔而刚毅、美丽而善良等令人崇敬的品质,而更在于她具有那种坚韧、顽强的性格,向反动势力抗争的、宁死不屈的精神。”[8]“她感情丰富、性格倔强,是俄国文学中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反抗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的勇敢、刚毅的性格。”[9]“她在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长大,从小就很有个性,富于幻想,对生活充满美妙的憧憬。她感情真挚、热烈,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她笃信宗教,具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感。”[10]其实,在此新旧交替的时期,卡捷琳娜的性格必然具有双重性。卡捷琳娜是在旧的传统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必然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她有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早在童年时代,她就经常和母亲一起去教堂,而且家里经常住满了女香客和朝圣的女人。这样,宗教观念在她心中就扎下了根。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追求女性自由的观念影响很大,其化身就是瓦尔瓦拉,她一再鼓励她追求自由,无视习俗和传统:“你先别急,等哥哥明天一走,咱们再想想办法;也许你们能够见面的。”“你这么单相思有什么用!哪怕你愁死了,难道会有人可怜你吗!别犯傻啦。何必自讨苦吃呢!”“依我看,你就放手干吧,只要不露马脚就行。”并且还帮她住到花园里的亭子内,给她钥匙,叫来鲍里斯,让他们相会。这些行为以致卡捷琳娜都觉得惊恐,感到瓦尔瓦拉是“疯子,真是疯子!这会毁了我的!”卡捷琳娜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环境里。旧的东西力量强大,但已开始让年轻人不太信服;新的东西摇动人心,但又没有为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真正的指导思想,人们因此无所适从,不知应该怎么办。像卡捷琳娜这样背着丈夫与别人私通,“过去是要把人弄死的”,其实这样,倒也让她高兴:“如果干脆把我扔进伏尔加河,我该多么快活啊!”可是现在,人们好像有点进步,不把人弄死了,但反而更残酷:“他们说‘要是把你弄死,那么,你的罪孽就会解除,你得活下去,让你的罪孽折磨你’。”
卡捷琳娜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充满幻想,富于诗意,过于天真、单纯、浪漫,对现实生活的严酷、生活风习的残忍缺乏应有的准备与深刻的认识。她生长于较为自然的单纯环境中,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在家庭的疼爱和美妙的幻想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不是浇花、织绣、听香客讲故事,就是到教堂去;她能够深深理解大自然的美,热爱俄罗斯歌曲,并善于为自己创造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她说:“人为什么不会像鸟那样飞?你听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我像只小鸟。站在山上的时候,真想插翅高飞。就这么跑呀跑呀,举起胳膊,飞起来。”甚至在教堂里,她也富于浪漫幻想:“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教堂的圆屋顶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柱,这光柱里烟雾缭绕,犹如云彩在飘拂,我看到,仿佛常常有天使在这道光柱里飞翔和唱歌。”睡着了的时候,她也尽做美梦:“我做过多么美的梦呀……不是金碧辉煌的神殿,就是异常美丽的花园,总有看不见身影的人在歌唱,松柏散发出清香,这里的山和草木都跟平常的不同,就像圣像上画的似的。要不然呀,我就好像在飞,在空中飞翔。”然而,出嫁以后,森严的家规、严酷的现实,使她失去了少女时代的自由和幸福,再加上在爱情方面也无所指望——丈夫是个唯命是从、软弱无能的人,一切都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敢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因而,这自由的、浪漫的灵魂,深感自己被残酷的习俗和平庸的生活拘禁了:“我待在家里觉得很闷,闷得我真想逃走。我常常这样想,要是由着我呀,这会儿我真想驾一叶扁舟,唱着歌,在伏尔加河上遨游,要不然呀,就彼此拥抱着,坐在一辆漂亮的三套马车上……” 在某种程度上,她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孩子,因此她特别喜欢小孩子,甚至说:“我最喜欢跟孩子们说话了——要知道,这都是些小天使啊。要是我小时候死了就好啦。那么我就可以从天上遥望人间,兴高采烈地欣赏一切。要不然,我就飞得无影无踪,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要飞到旷野,像蝴蝶似的乘风飞翔,从这棵矢车菊飞到那棵矢车菊。”即便是死,她也比哈姆雷特想得更有诗意。哈姆雷特害怕那死后不知有什么而且十分黑暗的王国,卡捷琳娜则富有诗意:“还是在坟墓里好……一棵小树下面有座小坟……多好啊!阳光温暖着它,雨水滋润着它……春天,坟上会长出青草,那么细软细软的……鸟儿会飞到树上,它们将唱歌,生儿育女,鲜花盛开:有黄的、红的、蓝的……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静悄悄的,太好啦!”
卡捷琳娜在娘家是掌上明珠,父母对她实在太好,这就形成了她这种浪漫、幻想、诗意的性格:“过去,我就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无忧无虑。妈妈疼得我什么似的,把我打扮得跟布娃娃一样。她从来不勉强我干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总是一早起来;如果是夏天,我就到泉边去洗脸,还顺便挑点水回来,把家里所有、所有的花儿都浇上一遍。……然后我就跟妈妈一起到教堂去,大家都去,香客们也去,我们家老是住满了香客和朝圣的女人。我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就坐下来干活,多半是用金线在天鹅绒上绣花儿,那些香客就开始讲她们到过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讲圣徒们的各种故事,或者唱赞美诗。就这样一直到吃午饭。接着那些老婆婆就去睡午觉,我就在花园里散步。然后我们又去做晚祷,晚上呢,我们又是讲故事,唱歌儿。”结婚后,丈夫虽然爱她,但自身都被母亲管得毫无自由,甚至出门远行前,妻子拥抱他,也要受到母亲的指责:“你搂搂抱抱的干什么,真没羞没臊!又不是跟姘头告别!他是你丈夫——一家之主!难道这点规矩都不懂啊?跪下磕头!”因此季洪对她的感情不敢太外露,也不可能太热烈,甚至有点自私。比如说他要到莫斯科去,妻子求他别去或者把自己也带去,他居然说:“过着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哪怕你老婆再漂亮也会逃走的!……有两星期,我头上再没有人来打雷下雨,脚上也不戴镣铐,我哪管得了什么老婆不老婆。”而婆婆对一切都管得很严,使她感到:“这儿的一切好像都是被迫的。” “她太让我伤心啦……因为她,我讨厌透了这个家;甚至瞧着这四堵墙都讨厌。”
与此同时,卡捷琳娜性格又是相当刚烈、十分冲动的。她说过:“我还在五六岁的时候,不会更大,就干了这样一桩事!家里人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惹恼了,这事发生在傍晚,天已经黑了,我跑到伏尔加河上,坐上一只小船,就离了岸。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好容易才在十几俄里以外的地方找到我!”所以,面对各种拘禁、规矩、压迫,她必然无法驯服地听从,必然会反抗,她曾宣称:“要是我在这里感到深恶痛绝的话,任何力量也拦不住我。我会跳窗,跳伏尔加河。我不想在这儿住下去,哪怕把我宰了,我也不干!”她最大的反抗,就是克服了心中沉重的负罪感,大胆地与鲍里斯幽会了十个晚上。从上面的情节可看出,她是一个富于激情的人,十分容易冲动。正是在无法克制的冲动中,她不加思考地当众忏悔,最后,她在见了爱人最后一面后,又毅然冲动地投身伏尔加河自尽。
然而,宗教和传统又使她刚烈的性格中有着软弱的因素,这表现为强烈的罪孽感或者说负罪感。她像传统习俗和宗教观念那样,认为自己的婚外恋是沉重的罪孽,她甚至对鲍里斯说:“这罪孽是十恶不赦的,永远也没法求得宽恕。要知道,它会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心上。”丈夫回来后,她更是深感有罪,“浑身哆嗦,像打摆子似的;脸色煞白,在屋里走来走去,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两只眼睛像疯子一样!刚才,上午前她还哭过,简直是嚎啕大哭。……她都不敢抬起眼睛瞧丈夫。”同时,她又相当诚实,不会撒谎,不会伪装,不会过一般人过的那种双重生活,有深刻道德情感,在新潮人物把隐秘的幽会当做新道德的时候,她却在进行道德的自我审判。这些更使得她加强了负罪感,进而导致了她的坦白和自杀。然而,这一形象的独特意义,也正在这里。她的自我道德审判,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对妇女形象道德义务感的优良传统(如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因此,“卡捷琳娜的悲剧与其说是在于‘破裂的爱情’,在于和不喜爱的丈夫及威严的婆婆一起过‘令人厌恶的’生活,不如说是在于当她发现不可能在‘新道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发现未来没有出路时内心感到的渺茫”[11]。
卡巴诺娃的性格也具有双重性。但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其依旧是众口一词,彻底否定。“卡巴诺娃是旧制度、遗风故习的坚决维护者。她性格、意志的中心是维护专制势力。她要一切人遵守陈旧的传统,敌视任何独立性与新事物。……但是卡巴诺娃与提郭意表面上有所不同,即在于她的伪善。她虔信宗教,宣讲古老的遗训、原则,施舍叫花子,大养香客,作礼拜不缺席……都是美化她的残暴的外衣……她在依照陈旧规则作恶时,反而认为自己是在‘行善’。这样就把一切暴虐解释成美德了。”[12]“卡巴诺娃是‘黑暗王国’中宗法制生活秩序和一切旧传统的维护者。她不但专横、无知、守旧,而且狠毒、伪善。”[13]“卡巴诺娃是‘黑暗王国’的另一种代表。她不仅专横、无知、守旧,而且狠毒、伪善。”[14]
人们对她早已有两种评价:一方面她对外人还是仁善的,对穷人、叫花子、过路香客,她总是“慷慨布施”;对野蛮成性、总是大骂家里人的季科伊,她也有好心的劝说:“你一辈子老爱跟老娘们干仗,也不见得有多大光彩”,甚至说:“我对你真感到纳闷:你家里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满意吗?”“你干吗让自己发这么大火呢?我说,大兄弟,这可不好。”并且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你要是看到有人想来找你要钱什么的,你就存心对你家里的什么人破口大骂,大动肝火;因为你知道,你发起火来,也就没人敢接近你了。”另一方面,她对子女却极端严厉,要求他们必须循规蹈矩,以致于外人对她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库德里亚什说她“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库里金宣称:“她是个假善人……对叫花子可以慷慨布施,可是对家里人却心狠手毒。”但受惠于她的女香客费克卢莎,则称她“品德高尚,为家门增光添彩”。
卡巴诺娃并不像过去人们评价的那么穷凶极恶。她对子女是爱的,像所有母亲一样的爱。她说:“要知道,做父母的有时也对你们严厉,是出于爱子之心,就是骂你们,也是出于爱,总想教你们学好。”“谁让我是你妈呢?为了你们我心都操碎了。”就连瓦尔瓦拉在给季洪送行后谈到母亲时,也这样说:“她心中十分难受,因为哥哥现在没有人管了。”她对乞丐、香客也是尽力帮助的,这是她仁善的一面,她与敛财成性、成天骂人的季科伊是不同的,那完全是个异化了的东西,而她还是有好的一面的。她的问题在于,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人物,一个封建家长,一切都要按规矩办,决不允许越雷池半步,她是旧传统和习俗的保护者,尤其是家里的一切都要随她这个家长的指挥运转,从而不自觉地充当了用温情脉脉来杀人的角色。“卡巴诺娃坚信,她应该,她有责任教导青年人,她是为他们好。这是治家之道,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祖辈一直是这样生活的”,她“竭力维护宗教虔诚和旧道德”[15]。因此,她特别强调儿女们一切都得听母亲的,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甚至惧怕丈夫进而服从婆婆:“连你都不怕,就不用提服我了。咱们这个家还有什么规矩?”她认为,季洪当着妹妹的面说只要妻子爱他就行,不必怕他这种话,会把妹妹也教坏,引起她未来丈夫的不满。即便在季洪要出门两个星期这件事上,她也要讲规矩,母子怎样告别(叮咛、嘱咐,还要儿子跪下磕头),兄妹怎样告别,临行前丈夫应该吩咐妻子注意些什么,她都要维护传统,甚至指责媳妇没有按老一套规矩办:“你老是自吹自擂,说你非常爱丈夫;我现在算是看见你有多么爱他了。人家的媳妇送丈夫出门,躺在台阶上一哭就是个把钟头;可你呀,跟没事人似的。”她最注重的就是规矩,就是传统的东西,她一再感叹:“年轻人就是不懂规矩!瞧着她们都觉得可笑!要不是自己的孩子,我不笑掉大牙才怪。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规矩都不懂。连个像模像样的告别都不会。幸亏家里还有长辈管着,他们在世的时候,这个家还有人支撑着。可是这帮糊涂蛋还想由着自己去胡作非为,真要这样,岂不乱了套,让人戳着脊梁骨笑话。……自古以来的老规矩就这么给废啦。……要是老人们死绝了,怎么办?这世道又该怎么样呢?”因而,她认为新思潮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唉,可是如今不喜欢这样。做儿女的逢人便说她妈唠叨个没完,说什么她妈跟他们过不去,恨不得把他们逼死才好。哎呀,上帝保佑,只要一句话没有讨得儿媳妇的喜欢,就会有人说长道短,说什么婆婆差点没把她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她对子女看管得更紧了,以致子女们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儿子巴不得快点外出,媳妇恨不得远走高飞,女儿最后离家出走。当然,在卡巴诺娃的感情中,还有点寡母对媳妇的嫉妒:“我早就看出来,你对老婆比对妈亲。自从你成亲以后,我就看出来你对我没有从前那么孝顺。” “你没有成家的时候,兴许你是爱妈的。现在你哪里顾得上我呀:你有年轻的媳妇嘛。”当季洪辩白说“这是两码事,互相并不妨碍。媳妇是一回事,孝顺母亲是另一回事”时,她甚至公开提出来:“那你肯把媳妇换母亲吗?”
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复杂因素,使得卡巴诺娃不自觉地成为了温情脉脉的杀人凶手,一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母亲,和现实生活中宋朝陆游的母亲。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大雷雨”是卡捷琳娜觉醒的象征、反抗的象征。细读原著,我们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可靠的。女主人公一再宣称害怕“大雷雨”,并且“可怕的倒不是雷会把你打死,而是你冷不防突然死去,像现在这样,带着你的一切罪孽,带着一切大逆不道的想法。死,我倒不觉得可怕,可是我想,在这次谈话后,我突然出现在上帝面前,就像这儿我跟你在一起一样,那才可怕呢”。本来已有“大雷雨”的恐惧,心上人鲍里斯突然又走了出来,再加上贵妇人的惊吓,跪到墙边,又看到火焰地狱图,卡捷琳娜终于再也忍受不了啦,当众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且主动供出了“同犯”:“我的心已被撕得粉碎!我再也受不了啦!妈!季洪!我在上帝和你们面前都是有罪的!……在头一天夜里我就从家里跑出去啦……这十天夜里我都去玩儿了……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史坦因指出:“在剧本的结构当中,第一幕和第四幕的雷雨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次雷雨是个警号,第二次则是那等待着卡捷琳娜的惩罚的征兆。”[16]著名演员毕沙勒夫(1844—1906)曾经指出:“天国的大雷雨只在此地才和道德的大雷雨相共鸣起来,而显得更加可怕。婆婆——是大雷雨,斗争——是大雷雨,对于罪行的意识——是大雷雨。所有这一切,都非常骚乱地影响了卡捷琳娜,即使不是那样,她也已经是个够幻想和迷恋的人物了。而在这一切之上,又加上了天国的大雷雨。卡捷琳娜听到一个消息,说大雷雨并不是徒然来临的,于是她觉得大雷雨会把她打死,因为在她的心灵里重新出现了老贵妇人所指出的那种原本的罪:‘你干吗躲藏起来?躲藏起来有什么用!看起来,你害怕,你不想死?你想活!怎么会不想活呢!带着你的美丽投到深渊里去吧!是的,赶快去,赶快去!’当画在墙壁上的恐怖的审判图投进卡捷琳娜的眼帘时,她更加忍受不了那个和天国的大雷雨及老贵妇人的可怕的迷信与险恶的话语相伴而来的内心的大雷雨,良心的大雷雨:她高声地承招出,说她和鲍里斯在一起整整地逛了十夜。她早年在书本中所受的那种狂喜的幻想的教育,当时她每分钟都在期待着:一旦雷响起来就会打死什么罪人,现在都正反映在她这种骚乱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之下,很明显地,她既看不见她周围的人,也听不见他们的话,假如她承招了自己的罪的话,那大概是她在狂乱的情况中承招出来的。”[17]
注释:
[1] 详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244—462页;第二卷,第331—440页。
[2] 易漱泉等著:《俄国文学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24页。
[3]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4]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2页。
[5]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6]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7]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
[8] 易漱泉等著:《俄国文学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9] 李兆林、徐玉琴编著:《简明俄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3—194页。
[10] 任光宣主编:《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11]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12] 易漱泉等著:《俄国文学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27—428页。
[13] 李兆林、徐玉琴编著:《简明俄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14]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15] [俄]洛巴诺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朱铁声、章若男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16] [俄]史坦因:《奥斯特罗夫斯基评传》,蒋路译,北京:时代出版社,1954年,第60页。
[17] 戈宝权、林陵合编:《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北京: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第19—20页。
【主持人语】本期发表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三篇,它们的选题、论点与论证方式,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皆有新意且有突破。曾思艺教授的《新旧冲突中无所适从者的悲剧——也谈“大雷雨”主题及卡捷琳娜、卡巴诺娃形象》,紧扣奥氏剧作文本故事情节与人物话语之细节,从两个主要女性形象的双重性格出发,认为它是一出新旧事物的冲突以及女主人公在这一冲突中的无所适从导致的悲剧,这样的见解对于重新理解作品主题有很大帮助。王树福副教授的《双头鹰与十字钟摆:俄国审美现代性的多重面向》,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俄国现代化进程坎坷波折,其原因是它不断受到东西方文化因素的诱惑与影响,所以它的现代性选择一直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左右摇摆,这正导致其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和悖谬在文学思想中的渐次展开,在历史上形成了坚守民族性的斯拉夫派、认同现代性的西欧派以及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欧亚主义、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等审美形态。作者视野开阔,条分缕析,比喻深刻。刘涛副教授在《“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形象》中提出了另类“作者”概念,并认为诗作里始终存在着一位神采飞扬且忧国忧民的“作者”形象,正是他的立场、观念与感情让长诗产生了特有的思想与艺术魅力:一方面他身上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他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强烈地谴责当时王公贵族们因内讧而造成的分裂倾向的基础上,作者对建立统一罗斯民族国家寄予深切的希望。因此,研究“作者”形象的存在与原因,对于重新评价此诗具有重要意义。(邹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