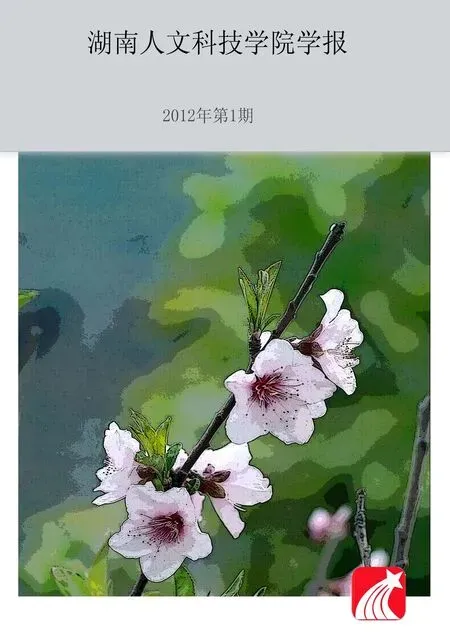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质疑
2012-04-08胡美玲
胡美玲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上海 200042)
见危不救的现象此前在中国一直属于道德的调控范围,根据传统的价值取向,当别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以积极救助他人的生命。但2007年“彭宇案”的出现却动摇了这种价值取向,后又出现了2009 年8月重庆那个惨死在闹市的“女村官”、10月荆州长江边上2名少年落水中渔船拒施以便救捞尸赚钱、2011年10月“小悦悦事件”等一系列悲剧。故此有人面对中国社会这种漠视生命的情形,提出刑法应当增设见危不救罪,以纠正这种道德沦陷的现象。但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只要不是出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免受更大侵害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国家就不能运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剥夺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1]。笔者认为见危不救的现象尚不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一 见危不救行为的界定
见危不救,在我国泛指见到别人有危险而不去实施救助的行为。而国外的刑法体例中,的确如美国、俄罗斯、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国家都设立了见危不救罪,具体指“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2]。相比较于国外的见危不救,我们的概念至少有以下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对“别人”范围的界定,是指除行为人以外的任何人还是仅限于行为人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其次,“危险”程度的要求,不是一切危险都有转化为死亡的可能性,客观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本身没有导致生命的危险在客观因素的刺激下最终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那么此时的危险是否属于不救助的危险范围;最后,见危不救的范围是否应该扩大,具体而言,当行为人有救助能力却不实施救助行为无疑属于见危不救,但如果行为人看见他人有危险时没有救助能力,是否应该要求行为人实施一些诸如拨打110、寻求附近的第三人帮助等协助行为。基于以上关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种种问题,笔者拟对见危不救行为作出全面的界定,同时对刑法规制的范围作出合理界定。
(一)“别人”的范围界定
见危不救的“别人”至少不包括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因为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不实施救助的行为另有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名规制。但是这个“别人”的范围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只有当某人见到别人有危险并且明确意识到该人正处于危险的状态时,其才有救助的义务,否则会使打击面过大。
(二)“危险”的程度要求
从国外刑法见危不救的立法来看,其中的“危险”多指威胁生命的危险。但实际上见危不救中的“危险”不应该仅限于有直接转化为生命危险的情形,应该说,凡具有转化为生命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都属于需要实施救助的范围。之所以如此界定:一方面,有利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鼓励大家面对别人的任何危险都积极实施救助行为;另一方面也对救助人提出更高层面的要求,当面对一些没有直接转化为威胁生命的危险时,有人可能抱着我不救自有他人救的心理而放任不管,由于现实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没有直接威胁生命的危险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完全有可能威胁生命,因此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此时行为人能够实施救助行为。
(三)见危不救的范围问题
从国外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概念来看,只规定不给予救助的行为属于见危不救。但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另外提出:见危不救罪,也被称为疏于救助罪,是指对因年幼、年老、疾病或其他原因致使生命危险而不能自救的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不予救助或放弃救助的行为[3]。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唤起救助”的字眼。具体而言,即行为人自身没有救助能力时,是否有义务去寻求第三方的帮助来实施救助。从道德的层面看,这种规定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有利于社会和谐;但从法律层面看,不应该对行为人提出这个层次的要求,因为法律以社会为依托,不能将一般人不会实施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规制。因此,这里的见危不救应仅包括不实施救助的行为。此外,从一般人的角度,实施救助行为还必须对救助人不造成现实的危险,至于对他人是否会有危险,我们认为也不应该有,因为法律上的人是平等的,所要求的救助行为也只能不造成任何危险。
综上所述,我们对见危不救行为可以作如下界定: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明知他人处于有转化为生命危险的危险状态中,有能力实施救助行为并且给予救助不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时却不实施救助的行为。
二 见危不救犯罪化质疑的理由
下面,笔者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刑法谦抑性理念和司法实践操作的可能性三个角度对见危不救犯罪化提出质疑。
(一)没有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危不救行为如果纳入犯罪规制的话,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理论,要成立不作为犯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二是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三是作为义务之不履行与危害结果之发生具有因果关系[4]。笔者认为见危不救罪的设立不符合第一个条件。
我国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一般分为四类: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二是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三是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在见危不救的情形中,首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目前的刑法尚没有将救助义务规定为法定的义务;然后由于要求实施救助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因此不可能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最后见危不救多发生在行为人偶然路过的场合,不可能有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因此自然也不存在这两者所引起的作为义务。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见危不救犯罪化在现行刑法中缺乏救助义务的来源基础。但有学者指出我国国内刑法界以往对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探讨局限于形式,并未深入实质,进而提出“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也是不作为犯罪中特定义务的根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可取,我们的刑罚权不能随便扩张,应该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因此,在见危不救的情形中,由于没有刑法条文明文规定的救助义务,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就不应该对不实施救助的个人予以定罪量刑。
(二)违背刑法谦抑性理念
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但概括起来无非包括以下层面的内容:一是刑法的经济性,二是刑法的最后性,三是刑法的有限性,四是刑法的宽容性[5]。笔者认为若将见危不救犯罪化,至少不能实现刑法的经济性、最后性和宽容性。
刑法的经济性,是指国家在动用刑法手段调控社会生活时,必须以最小量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刑法效益。见危不救行为多发生在公共场所,涉及的人数往往很多。如果设立见危不救罪,即意味着对每一个应该实施救助行为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侦查机关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举证。再来看看打击这种行为的刑法后果,见危不救行为相对于一般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显然没有那么大,因此对其判处的刑罚多以短期自由刑或罚金刑为主。如果判处短期自由刑,由于见危不救涉及的主体很广,无疑会给我们的监狱造成很大的压力,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监狱管理,而且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形成的心理来看,见到危险不实施救助的行为很少会给行为人造成犯杀人、盗窃等罪后的罪过心理,从而不会有悔罪的表现。如果判处罚金刑,由于从实际效果看,罚金刑和行政处罚中的罚款在实质上并无差别,对受罚的当事人来说,两种处罚都同样的是剥夺合法财产,在数额上也并无多少之区别[6]。但刑法作为社会生活最后的调控手段,既然行政处罚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了。总之,从刑法经济性的角度,运用刑法对见危不救行为加以调控也是不适当的。
刑法的最后性,是指刑法必须是所有法律体系中最后介入的制裁手段。从刑法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出,刑法经历了从介入国民生活各个角落的全面法到调整一定范围社会关系的部门法再到作为其他部门法实施后盾的保障法这样一个演变轨迹[7]。现在,刑法即是作为其他部门法的后盾而存在。再反观见危不救现象,笔者认为还没有到非刑法不可规制的地步,因为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部门法对见危不救现象加以规定,因此刑法的后盾作用不能直接发挥。其实,见危不救现象此前一直是道德范畴的问题,道德鼓励个人在别人需要救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大家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滑坡现象比较严重,因此有人提出将此问题纳入刑法的规制,以强制人们去救助他人。这种提法是不合理的,舆论谴责、社会倡导、治安管理处罚等措施完全可以及时制止道德滑坡的现象。
刑法的宽容性,是指刑法介入社会生活,介入人类行为领域时,应当有尊重、保护、扩大公民自由、权利的极大同情心、自觉性和责任心,对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发展和解放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以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具体包括刑法发动的善意性、刑法调控范围的现实性和刑法调控手段的人道性[8]。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过程中,是把每个人面对别人遇见危险时都设想为一个善人的角色,但关于人性善恶论的争议几千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面对别人处于危险境地都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况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人因为救助别人最后反成为被告、或者因为救助别人最后自己陷入生活的困境等情形出现。因此,从刑法宽容性的角度,刑法应对人性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见危不救是否入罪也要慎重考虑。
(三)司法实践难以操作
要设立见危不救罪,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必然存在一个举证问题,即侦查机关需要证明哪些人见到危险没有实施救助行为。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来看,需要救助的危险多发生在公共场合,谁不实施救助行为也多是通过公共场所的摄像头来判断的,个人很难成为见危不救罪的证明主体,因为当一个人能够证明别人见到危险不实施救助行为时,说明他自己也看到这种危险的发生,其本身即有一个救助的义务,法律不可能期待个人通过说出自己的犯罪来证明别人的犯罪。因此,见危不救罪的证据完全集中在摄像头了。但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差异,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有摄像头,也不是所有摄像头都能清晰地拍下公共场所的一切状况。此时,犯罪的打击面即取决于摄像头的数量和质量,这时极可能出现一种情形:甲和乙在两个发展程度差异很大的城市,面对别人处于危险的情形都没有实施救助行为,最终甲却被定为见危不救罪,而乙无罪。这显然违背刑法的平等性原则。因此,从举证这个层面上,见危不救行为也不应纳入犯罪的规制范围。
此外,若设立见危不救罪,司法成本过大。举证程序就需要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因为见危不救的范围涉及的主体往往很广,例如“小悦悦事件”中就有18个路人,要一一证明其见危不救行为,无疑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况且有些案件中涉及的主体远大于18人,成本上更是不可不考量。基于有限的司法资源,我们也不应该从刑法上打击见危不救行为。同时,行为人要成立见危不救罪还要求其明知别人处于危险需要救助的情形,这里对行为人明知的举证也很困难。有时行为人虽然经过需要给予救助人的身边,但需要救助的人可能不能言语,表面上看起来与正常人无异,以至于行为人当时无从判断,最终没有实施救助行为,如果对行为人定见危不救罪显然不合理。
三 结语
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即是道德义务的刑法化。见危不救行为属于道德调控的范畴,我们期望通过舆论谴责、社会倡导等一系列手段纠正这种道德滑坡的现象,不能由于某些人失“德”就认为失法。刑法作为社会生活的第二道防线,它是其他部门法的实施后盾,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个理念。当前,无论是从刑法理论层面,还是从司法成本、法律的可操作性角度,我们都不应该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
参考文献:
[1]陈忠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2]王启富,陶髦.法律辞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21.
[3]安翱.增设见危不救罪相关问题探讨[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2(5):23-25.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7-248.
[5]熊永明,胡祥福.刑法谦抑性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65.
[6]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55.
[7]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97.
[8]陈正云.刑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