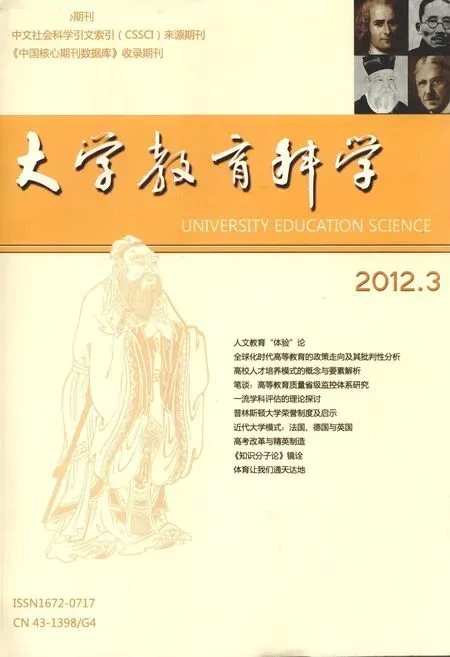人文教育“体验”论
2012-04-03张祥云
□ 张祥云 陈 莉
人文教育“体验”论
□ 张祥云 陈 莉
“活着”就得体验,体验才算“活着”。人文教育是教人如何“活得好”的教育。因此,体验对人文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体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教育“方法”,是与人的目的、价值合一的“方法”,体验既是方法也是目的。为了区别于科学的“工具性方法”,我们将体验称之为“本体性‘功夫’”。我们不仅要从方法论视域更要从本体论境界去整体理解体验。从本体论境界看,体验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文教育的过程是生命体验的过程,生命体验的过程是学生成为自己的过程;从方法论视域看,体验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方法,人文教育的体验方式包括:诚敬、专注、参与、理解、反思。
人文教育;体验;本体性;功夫
体验必须是“活着”,“活着”却未必在体验。植物人的“活着”,就没有体验。没有体验,仅是“肉体性地活着”,不是“精神性地活着”,这样的“活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活着”。没有体验的人,除了植物人,还包括睡不醒又没有梦的人。肉身存活基础上的“精神地活着”,必须是体验的。体验是人自我确认、自我见证自己活着的基本方式。自我“活着”的丰富性、质量及其意义和价值全靠自我的体验,那些不懂得体验的人,被指称为“木头人”和“行尸走肉”,是有道理的。体验的能力,是自己“活”给自己“看”的能力。人文教育是教人如何更好地“活着”的教育。如果“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那么,人文教育就应该既是“体验地”又是“体验的”。既要“教人去体验”又要“体验去教人”。体验在人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基础性的。
一、体验的生命:人文教育本体境界
人文教育的实质是人性的教育,是让学生“成人”的教育,是对“心”的教育。人文教育的影响只有通过学生自己去体验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在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体验对人文教育来说具有本体论意义。
(一)体验是人的存在方式
体验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的文献中。据说出自黑格尔的一封信,后来因为在传记文学中频频使用而被广泛传播。在德语中,体验(Er leb en)有经受、经历等含义,蕴含了主体主动积极地去感受生活、体验生命及其价值的意思。正因为这样,一些英译者经常把德文Er leben一词翻译成Ex per ience of life(生命体验)。《现代汉语大词典》则将体验一词解释为:(1)动词,亲身经历;实地领会。(2)名词,通过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经验。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我们倾向于把体验当做工具性手段来定义。这个解释似乎还没有揭示体验在生命意义上的本体论意蕴。
最先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本体论范畴提出来的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曾对体验做过许多规定,但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体验指的是“特殊个人发见其此在的那种方式和途径”[1],即体验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领会和发现自身存在的方式和途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狄尔泰认为生命正是在体验中完全实现它自身,并由此观察生命,从而把握它的全部内涵。他视体验为生命的基础,所以强调生命表达在体验中。叔本华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的世界”[2]。狄尔泰也认为,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物理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一个只有对有灵魂的人才敞开的、由生活体验所构成的生活世界。世界的本体不是理性、不是实证主义那种客观外在的实在,而是活生生的、有心灵的感性生命。而生命处于变化之中,是不断生成的,人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只能依据内在的体验和感觉加以把握。那些经过抽象的东西,也只能通过体验才能得到具体的说明。由此可见,生命体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体验,而是体验者在体验中存在,体验使体验者存在,体验与体验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只要人存在,人就总是要体验着的。因此,体验是人存在的方式。
(二)人文教育的过程是生命体验的过程
受传统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常常把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于是将主体和客体,目的和手段相分离。在教育领域,人文教育把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客观化,用处理人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来处理人与人文知识的关系,用了解物质世界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精神世界,用改变外部世界的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心灵世界。如果没有足够了解人文知识的特性和人文教育的特点及其关系,就容易将人文教育变成“数学式”的、“工程式”的教育[3]。人文教育往往只是使学生增加了人文知识,人文教育由此而被对象化、工具化、技术化,变成纯粹传递知识的“工具”。一旦把知识当成目的,生命本身反而就成为了手段,人文教育的本体论意义就此消解殆尽。结果,在人文教育中,学生的个体世界被“外在”的知识片段所“堆放”,“头脑”“塞满”了各种“被客观化”处理过的人文知识,“心灵”却无法体验到自我和感受到幸福。人文教育的真正使命是要唤醒学生的精神生命和意义生命,在追寻自我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人文教育应该始终关注学生的生命主题。
生命是体验,而不是知识和理论。人们常常认为生命是一个谜,而且会有一些答案,他们必须解答“它”,于是寻找解释、理论和学说。过分强调“生命是一个问题”的假设,把人们引向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为了找到答案,他们努力学习并制造各种知识和理论。但生命问题的解决却不能仅仅依靠于这种头脑上的知识和理论。我们不仅要从知识层面去解答“它”,更要在本体层次上进入“它”,去生活并感受,与“它”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对生命的理解来自我们的整体,不仅需要“脑”的思考,更加需要“心”的体悟。在“脑力”基础上提升到“心力”的境界,才能真正进入生命堂奥。人文教育所引领的生命理解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使整个生命成了你,使整个你成了生命。在这样的境界里,我们与生命的关系就超越了工具性的“我—它”关系,而变为本体性的“我—你”关系——用“我”“你”“它”来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布伯的经典表达。我们不能“死于”布伯所谓的“我—它”公式而不悟,虽然没有“它”,我们不能“生活”,但仅仅靠‘它’来“生活”,这样的所谓“生活”,其实只是处于糟糕而“困难”的“生存”状态而已。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否则,那些关于生命的确定性知识、理论、结论就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而还会束缚我们,让我们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就如百足蜈蚣的故事一样:
蜈蚣是用成百条细足蠕动前行的。青蛙见了蜈蚣,久久地注视着,心里很纳闷:四条腿走路都那么困难,可蜈蚣居然有成百条腿,它是怎么行走的呢?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蜈蚣有成百条腿,它是怎么决定先迈哪条腿,然后动哪条腿,接着再动哪条腿呢?于是青蛙拦住了蜈蚣,问道:“我被你弄糊涂了,有个问题我解答不了。你是怎么用这么多条腿走路的?这简直不可能!”蜈蚣说:“我一直就这么走的,可谁想过呢?现在既然你问了,那我得想一想才能回答你。”这个念头第一次进入了蜈蚣的意识。事实上,青蛙是对的,该先动哪条腿呢?蜈蚣站立了几分钟,动弹不得,蹒跚了几步,终于趴下了。它对青蛙说:“请你再也别问其他蜈蚣这个问题了,我一直都在走路,这根本不成问题,现在你把我害苦了!我动不了了,成百条腿要移动,我该怎么办呢?”[4](P166-167)
我们的学生有时就像青蛙一样,对生活、生命充满了疑惑,并带着他们的知识性回答试图征服生活,带着他们所学理论试图操纵生活。他们以为,只要知道了这些知识和理论,他们就成为了主人。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生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记住各种知识和理论。正是这些未进入学生内心的杂乱知识和繁多理论使他们忽视了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去回味生活中的感动。海德格尔曾说:“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关于人有这么多的并且如此杂乱的知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地成了问题。[5]”知识越多,人们疲于用脑,心被掩盖了。人文和生命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验才能化为自己的内在。头脑包涵不了“心”,是“心”包涵、滋养并超越了头脑,“心”更具生命的整体性。头脑只是制造确定性的知识和干枯的理论,当我们用“心”去体验时,我们才进入到生命的整体,我们才成了生命本身。生命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它是动名词,生命只有通过生命才能得到彰显。正是如此,狄尔泰才说“精神科学的基本方向就是从生命去认识生命,从生命去解决生命问题。[6]”我们的学生越是变得理论化,他们就活得越少。他们可以思考爱,却从来不会爱,他们想有关神的事情,却从来不会变得神圣。他们只是不断地谈论,将时间都花费在记忆文字、理论和学说之中,没有一刻进入生命和生活。人文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不仅需要记忆更需要学生将它融入生命整体。学生不仅要“知道”更要“体道”、“悟道”和“行道”。人文教育不是要教导学生占有多少死寂般的知识、了解多少木乃伊般的理论和学说,而是要让学生在人文知识的指引下进入心灵的探索,引导学生走入生命、生活,并与其融为一体。人文教育应该超越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不应停留在对人文知识头脑层面的理解和记忆,而是要进入到心灵乃至肉身层面的实践。因此,在人文教育的过程中特别要唤醒学生的体验,以体验的方式让学生进入人文知识,以体验的方式让人文知识进入学生的生命,激发学生用生命去体验人文知识,并且让学生在自身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开出智慧之花,使人文教育真正成为“人心”的教育。因此,人文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
(三)生命体验的过程是学生成为自己的过程
在茫茫宇宙中,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如卢梭所说的,上帝把我们造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属于我们的模子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都是身外之物,每个人都可以求得,但没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感受人生。从学生角度看,人文教育中生命体验的过程就是让学生成为他们自己的过程。
1.让他们接受自己
让学生成为他们自己首先要让他们接受自己。人文教育就是帮助每个学生成长,让他们从自身生命出发,变得更完善。而让自身更完善的前提是接受自己,否则学生就会失去依托。接受是我们与生命友好相处的原则。学生的诸多迷惑常常因为他们一直在排斥自己,责备自己,而不是接受自己。于是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内心骚乱和苦恼。我们的教育总告诉学生他们哪里不好,过分强调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需要改正。学生从小一路走来,就是在这种害怕犯错,避免犯错的状态下度过。我们为了让学生变得优秀,就必须先把他们身上某些本真的品质抹杀掉,然后教给他们在我们看来最好的东西。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成为好学生。其实,犯错和“缺点”宛如“黑暗”,黑暗不是一种“存在”,只是一种“不在”,它只是“光亮”“不在”。只要“点亮”“灯火”,黑暗就消失了。所以,人文教育要做的就是点亮“心灯”,用生命的智慧照亮他们领悟到生命大大不同于非生命的玄机,驱赶掉用理解非生命物质的习惯规则去理解自身生命的“黑暗”,赢得理解生命的“时间性智慧”。生命性即是过程性,成长性,个体性。生命不是一步到位,生命不是即刻定型,生命不是一劳永逸,生命不是外在创构。让学生领悟生命的奥妙暗示我们要从容地接受、享受、肯定自己成长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阶段。让学生既接受自己成熟的一刻,也接受自己羞涩的一刻。不要让学生只是在思想上把生命当对象,把生活当成“一个谜”,站在这个人生的“谜语”之外,对象化地“驻足”于思想地“猜谜”,因为生命不是身外之谜,它必须总是在被经历,而不能等到“解答”之后才去经历,就像我们不会等到我们解答了什么是爱之后才去爱。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总是沉迷于制造太多的“应该”。学生一直被教导那么多“应该”的知识,那么多“应该”的观点,教育始终寻求“应该”,于是,直接的“是”被羞于对待了。就像他们看着一朵鲜花,他们马上开始想的是这花应该是怎样的,它可以更大一点,它可以更红一点,可以注射化学物让它变得更大,可以画它,它将变得更红。他们不能接受它原来的样子,小或者大,红或者不那么红。生命的智慧却会发问:为什么不在这一刻享受它?为什么要先把它弄得更红,把它弄得更大,然后才享受它?教育的智慧也会问:为什么我们非要让学生个个都变得成绩优秀才觉得那是最好的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自我肯定地成长呢?我们是否会发现,我们把整个生命都浪费在了“应该”上,却看不见那个已经存在着的美丽的“就是”。人文教育必须让学生找到一条从他们生命被驯化的模式中“出走”,并进入自然生命流动的途径。从生命的视角看,学生的存在不是为了实现任何其他人的期望,其他人的规则,其他人的蓝图,尽管他们无法脱离被期望,被规约,被谋划,而且这些期望、规约、谋划在“应该”的意义上说都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合法的。但作为生命的而非机械的个体,学生在这里却是无可替代地要身体力行地去实现他们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规则是学生必须生搬硬套的,他们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很可能与公共的规则完全一样,但从根本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不是被赋予的。
2.让他们“放下”规则去领悟
人文教育中,要让学生体验生命,成为自己,就是要让他们放下规则去领悟。人文教育通过人文知识来教育,但人文知识不能成为捆绑学生的教条,变成冷冰冰的规则。规则是死的,它将成为一种禁锢,而领悟是活的,它将给学生无垠的天空。因此人文教育应该靠体验的方式将人文知识和人文理论—规则沁入学生的心脾,让其散发出生命的芬芳,使学生领悟到生命的真谛。然而我们却常常用处理外部世界知识的方法来对付心灵和精神这些内部世界的知识,心灵负担着太多未消化、未融通的规则。宗教精神最后纷纷变成教规,基督和佛陀的生活成为每一个人遵从的规则,但是没有其他人是释迦摩尼,没有其他人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唯规则是从,我们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修饰过的复印的副本,我们将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自己。在人文教育中,如果我们只是将规则硬塞给学生,最后他们就会像下面故事里的传教士一样。
这是个犹太教的故事。一个所谓的聪明人,几乎是一个犹太教的法学家,他从附近的村庄回家。他看见一个人带了一只美丽的鸟。他买下了鸟,开始想着:这只鸟如此美丽,回家后我要吃了它。忽然鸟儿说:“不要想这样的念头!”教士吓了一跳,他说:“什么,我听见你说话?”鸟儿说:“是的,我不是一只普通的鸟。我在鸟的世界里也几乎是个法学专家。我可以给你三条忠告,如果你答应放我并让我自由。”法学家自言自语地说:“这只鸟会说话,它一定是有学问的。”法学家说:“好,你给我三条忠告我就放了你。”鸟儿说:“第一条忠告:永远不要相信谬论,无论谁在说它。他可能是个伟人,闻名于世,有威望、权力和权威,但如果他在说谬论就不要相信它。”教士说:“对!”鸟儿说:“我的第二条忠告是:无论你做什么,永远不要尝试不可能,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失败。所以始终了解你的局限,一个了解自己局限的人是聪明的,一个试图超出自身局限的人会变成傻瓜。”法学家点头说:“对!”鸟儿说:“我的第三条忠告是:如果你做什么好事,不要忏悔,只有做了坏事才需要忏悔。”忠告是精妙的,于是那只鸟被放了。法学家开始高兴地往家里走,他脑子里想着:布道的好材料,在我下星期的集会演讲里,我会给出这三条忠告。我将把它们写在我房间的墙上和桌子上,这样我就能记住它们。这三条准则能够改变一个人。正在那时,突然,他看见那只鸟坐在一棵树上,鸟儿开始放声大笑。法学家说:“怎么回事?”鸟儿说:“你这个傻瓜,在我肚子里有一颗非常珍贵的钻石,如果你杀了我,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法学家心里后悔:我真愚蠢。我干了什么,我居然相信了这只鸟。他扔掉他带着的书本开始爬树。他是个老人,他一生中从未爬过树。他爬得越高,鸟儿就飞向另一条更高的树枝。最后鸟儿飞到了树顶,老法学家也爬到树顶。正当他要抓住鸟儿的那一刻,它飞走了。他失脚从树上摔下来,血流了出来,两条腿断裂了,他濒临死亡。那只鸟又来到一条稍低的树枝上说:“看,首先你相信了我,一只鸟的肚子里怎么会有珍贵的钻石?你这傻瓜!你听说过这种谬论吗?随后你尝试了不可能。你从没有爬过树。当一只鸟儿自由时,你怎么能空手抓住它,你这傻瓜!你在心里后悔,当你做了一件好事却感到做错了什么,你使一只鸟儿自由了!现在回家去写下你的准则,下星期到集会上去传播它们吧。”[4](P159-161)
这就是所有的传教士在做的,也是我们学生在做的。他们只带着准则,缺少的是领悟和体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特别明显。学生把道德知识当作世界的真理去记忆、掌握,最后以为在考试中取得了高分就是获得了“道德”。学生掌握了一定的道德知识,具备一定的道德认知和判断能力,但他们只是按照秩序机械行动,而不能够充分享受和体验道德生活、实践道德生活。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智慧,而是枯萎的语言符号和知识气泡。所以不要强记规则,只是试着“放下”规则去领悟和体验。“放下”并不等于抛弃,放下规则是为了让规则融入学生的心灵,就如身体里被移植的器官一样,最后与身体融为一体。如果老师只是将规则强加于学生,学生也不会变得明智,他们的内在将仍然无知。这样的学生看起来就像被刷得雪白的坟墓,外在看似美丽和清洁,内在却是死的。人文教育中,老师要让学生去领悟,将规则融解在他们心里,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遵循规则,以至于最后忘记规则的存在,而实际上他们却正在遵循着这些规则。
3.让他们平凡而独特地活在当下
最后,要让学生进入体验,成为自己,在态度上就要让他们学会平凡而独特得活在当下。
法国思想家蒙田在四百多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到,我们人类从不安于现状,总是追求未来,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使我们感觉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而对未来的乃至我们已经不在的未来的事却尤感兴趣[7]。人是具有时间意识的生灵,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人,因为有了时间意识,当下的生命状态就会与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当过去和未来全然地聚集在“当下”时,“当下”的空间反而被过去和未来占领了、覆盖了。因此,我们经常为过去或未来而活着,反而疏忽了“当下”的意义。事实上,“当下”才是构成生命的确切现实。“当下”是未来的过去,是过去的未来。“活好”“当下”才能拥有一个无悔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可现实的教育生活中,我们普遍得了浓重的“未来焦虑症”,学校教导学生要为了未来而学习,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为此,“你必须出类拔萃”,“你必须班上第一”,等等。为了未来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学生很可能为了某一点优势的获得而陷入不顾其余的洞穴思维之中。为了使自己有这种能力,学生要忍受暂时的痛苦,要放弃自我的个性去应付标准化、模式化的考试,甚至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来换取未来的所谓幸福人生。为了未来,当下被彻底当成工具献祭出去了。
把当下彻底出让给未来的人,也就把自己仅仅当成了工具和用途。可是一个人不只是一种用途,不仅仅在于要去证明什么。一朵玫瑰开花,不仅仅是为了过路人,不仅仅是为了将会看见或闻到其芳香的人。可是,我们的教育总是教人把自己当成一件东西,要在“商店”的“橱窗”里展示,总是等着有人来利用“他”的出众之处。当学生被教育成仅仅为了他人而存在的时候,他们就像呆在一个陈列柜里,被贴上商标,标了价,分了类,做了广告。托尔斯泰曾经指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于安排他人的生活”,而“人越不满足于自己和自己的内心生活,他就越是要在外在的、公众的生活中显示自己。[8]”其实在所有人忙于安排他人生活的同时,几乎每一个人也都在他人的控制和安排之下。学生被教育为他人活着,为未来活着,惟独不为自己当下的心灵活着。
生命因独特而产生价值,人文教育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变得千人一面。人文教育不是“流水线”的作业,把学生按照规定的模式进行塑造。要尊重学生自己的体验才能凸显生命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所以,人文教育要教会学生放下一切展览、表现,做回他们自己,平凡而独特地活在此时此刻,珍惜此时此刻的存在。这是不可替代的生命的事情,学生的生命要靠他们自己去体验和完成。老师是一种闪光的火焰,学生只是来汲取并点燃自己内在的火焰,最后那将成为学生内在的光芒,为他们指出生命体验的道路。
“人文教育是教人入‘道’的教育,而道却往往‘道隐无名’,‘大象无形’,且‘道可道,非常道’[9]”。即使我们的学生用头脑占领了人文知识这一疆域,他们依旧无法开启人文世界的城门,永远在“道”外徘徊。人文教育只有通过体验的方式让人文知识进入学生的心灵方可使他们“入道”乃至“道成肉身”。因此,与其说体验是人文教育的“方法”,还不如说体验是人文教育的“本体”。
二、生命的体验:人文教育方法视域
(一)体验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方法
人文教育是有关“心灵”(con sc iou sness)的教育,但科学知识的爆炸式发展不断刺激我们认识事物的欲望,我们常常以科学的方式去接触事物,于是,人文教育往往变成关于“头脑”的教育,即把“心灵”看作是“心智”(mind)。虽然心智似乎可以包括很多心理活动,但其中理性思维最具决定性,处于权威地位。理性之外的其他心理活动被忽视或轻视,完整的心灵中有一大片心田被荒芜了。把心灵简化为只关心知识的理性导致了我们的教育对学生精神、情感生活——“心事”(hear t)的忽视。于是在人文教育中,我们的学生常常用“科学”的眼光去看人文的世界,他们看到的世界只是按照“铁的规律”运作的一架宏大机器,而不是处处涌动着创造性、随意性、偶然性的生灵之舟;我们的教师也像科学家一样给学生分析人文知识,他们给了学生关于事实的知识,却没有带领学生进入人文的世界——一个丰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和教师就如下面这个故事中的科学家一样,把本来散发着“诗意的光辉”的人文世界变得单调乏味。
哲学家缪斯特堡要求科学家说一说海水。科学家提来一桶海水,说:“这是一桶海水。海水里还有盐分。它的水分含有氢和氧,并且每一滴水里都有亿万个分子。”缪斯特堡问科学家说这些盐啊、氧啊、分子啊是什么用意。他说:“我说的是关于海水的事实,并解释了这个事实。你若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他如何证明呢?缪斯特堡站在一旁看着他。他先取一桶水,并加以蒸发,把剩余的盐分当作结果指给缪斯特堡看;再取一桶海水并接通电流,把水分分解成氢和氧,用这些气体充起了大气球;他又把水置于高压之下,并改变温度,使其显示某种变化,证明每一滴海水由无数多的分子构成。科学家让缪斯特堡尝了尝结晶的盐粒,并让他看被氧气和氢气充得膨胀起来的气球和蒙蒙的蒸汽,然后说:“看到了吧,相信了吧!”只见缪斯特堡极为愤怒地面对着科学家,像受了戏弄,他说:“我认为你所作的这些证明并没有说明当初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我们所要了解的是海水,你却想尽办法粗暴地把它变成别的东西。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你任意地使海水被蒸发,被电解,像是在给它上酷刑。你让我看到了盐粒、看到了氢气球,看到了水蒸气。可是,海水呢?我们想要了解的海水呢?却被你弄得不见了!”[10]
为了清晰、准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宏观物体的微观结构都被科学的犀利目光透视得清清楚楚。科学就这样把大海拆解再划归为某种普遍概念,大海变成了盐分、水分、分子、蓝色,而不再是大海。可是在人文的世界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不能说明什么。例如蓝色,大海、天空、甚至衣服和书包都可以是蓝色的,它与大海没有直接的关系。人文教育中,我们不能把各种独特的蓝色抽取出来冠以同一个“蓝色”概念。这样一个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概念,不可能使学生对大海、天空等具体事物本身有真切的了解。科学重视用逻辑论证和证明、科学分析和证实等来产生知识,而人文则更重视体悟和体验,强调隐喻的、默会的和“迂回”的话语来进入情感。所以,理解人文世界的方法多是感悟性的、体验性的,尽管它并不绝对地排斥理性分析和推理计算,但在它那带有诗意般感性光辉的世界中,绝不能“滥用”科学的方法。当我们全身心地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诗一般的语句所激励时,就绝不能用科学的理性将其深厚的内容“分析”为“太阳每天都换一些新的氢离子进行核聚变”。如果这样,本可以让我们体味无穷的东西就变得索然无味。
体验使我们与事物融为一体,我们所看到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件事物都是独特的、唯一的,都是自身完满的,就如我们自己一样,具有了生命和个性。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一种天地,是一种“诗意”的理解。诗,需要用语言传达,而语言是概念化的,但是诗用它所表达的不是“概念”定义下的事物。也就是说,诗表达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言外之意”、“境生象外”,即诗的意义不在有明确定义的语言,画的意境也不局限在具体的形象。透过语言,诗重新救活了被概念封死的事物,在诗中,事物与心灵直接相遇。诗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愉悦和震撼正是来源于心灵与事物、心灵与心灵的这种无间关系。以体验的方式理解人文世界,就是不拘泥于任何知识和观念,像诗一般超越常识地去听、去看。它不是用概念抹去事物的一切感性存在之后的抽象推理,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对象之中的“精神漫游”。比起用科学的方法得来的那些公式、原理和定律,用感悟、体验的方法感受到的东西告诉给我们的似乎更多。它们的“信息量”可以为零,因为不包含按科学标准确证的内容,也可以为“无穷大”,因为其中有着我们体味不完的内涵。由此看来,理解人文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体验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即使它包含有理性的思索,也是以感性体悟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情感理性”(蒙培元的范畴)。因此,体验是理解人文世界的重要方式。对于人文教育,我们应该根据其知识性质、理解方式的不同而采用有别于科学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否定和排斥实证、逻辑等普遍运用于科学教育中的方法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是要强调更适合人文教育的方法——体验。没有体验,人文知识就成为干瘪的符号;没有体验,学生就无法走进精神和价值的世界;没有体验,我们的“心事”就变成“荒地”。脱离了体验的人文教育因失其“根本”而会变成人文的“木乃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验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方法。
(二)人文教育的体验方式
人文教育不仅是知识和方法的教育,更是心灵和精神的教育。它给予学生的,不仅是方法,更是思想——动名词意义的思想。从方法的角度看,体验的过程是参与、理解、反思和内化的过程,而诚敬和专注是我们对待知识和学问应有的态度。所以,人文教育特别注重体验过程中的诚敬、专注、参与、理解、反思和内化。
1.诚敬
在一个知识成几何速度倍增、凡事求新的时代,具有历史沉淀的人文知识和理论犹如历经沧桑的老人逐渐被我们所忽视和遗忘。我们的学生往往不愿花时间和耐心真正走进“他们”。常常只是看了几眼“他们”的“外貌”,就对其“指手画脚”,妄下判断。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创新并具有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建立在深刻了解批判对象之上的。对于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内容我们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就连具有大智大慧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都说:“我年轻的时候,知道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什么都知道。然后我变得成熟了一点,我开始感到我知道的不多,实际上,很少。当我变得非常非常老的时候我恍然大悟。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知道。[11]”妄说、妄断不是学生做人和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中国古人云“格物亦须积累涵养”,所以他们都十分强调在格物致知之中贯以诚敬。北宋哲学家邵雍说:“先天之学主乎诚,至诚可以神通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12](P33)”程颖、程颐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12](P37)”朱熹也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诚以致敬,说这事不妨胡乱做了,做不成又付之无可奈何,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的是一样,背后又是一样;外面做的事,内心却不然;这个皆不诚也。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13]”可见,他们都将“诚敬”视为治己、治学的重要方法。面对具有深厚内涵的人文知识、理论和传统文化,学生应该带着“诚敬”的心去深入研习。
2.专注
在这个日新月异、求变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对待知识和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急躁和匆忙,沉不下心去做事。有一个关于悟禅的故事大概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带来一点提示。有一位弟子问大珠慧海禅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大师回答了四个字:吃饭睡觉。那位弟子很不解。大师说:“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弟子当下就开悟了。我们现在的学生之所以不“悟”,就在于该吃饭时不吃饭,千般须索;该睡觉时不睡觉,百般计较。吃饭的时候想睡觉,睡觉的时候想做事,做事的时候想吃饭,做什么事情都不专心。结果就是饭吃不香,觉睡不甜,事做不好。据说一只蜜蜂必须飞上好几千里,停在5000朵花上才能采到一勺蜂蜜。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记住一件事: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要全然地在那里,否则他们将停在了花上,却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带上蜂蜜。当他们停在一朵花上的时候,就要真正的停留,要忘记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花。在那一刻,没有其他的花存在。仅仅作为一只蜜蜂嗡嗡地、快乐地享受那朵花。这样他们才会积累生命的蜂蜜。无论是学习和做事,学生都应该有一种专注的精神。这种专注是一种单纯的心境,精神集中而且心境宁和,这种专注是一种心无旁骛的执着。惟有如此,学生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所要完成的事情当中,不受其他事情干扰,才可以取得较大进步,才可以有所造诣。就如佛经言“心系一处,杂念俱无,方可大进。”[14]这大概也是一种定而得慧的卓越境界。
3.参与
参与的意思就是亲身参加、亲自去做。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的“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的古训。《荀子•儒效》里说:“学至于行之而至矣”。扬雄在《法言•学行》中也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可见,古代先哲们早已告诉我们为学之道旨在参与。可是在现实的教育中,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常常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在教室里“静听”、“静坐”,接受既定的一切,甚至很少问为什么。学生的身体来到了学校,可他们的心灵却游离在校外。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否则就会造成他们身心和知情的分离。参与的过程是获得经验的过程。学生通过活动和实践等途径参与到教育活动中获得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通过心灵的参与从书本或他人那里获得间接经验。所谓心灵的参与就是心灵体验,即以自己原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移情、想象等方式将自己融入到对象中,然后去感受、领会和参悟其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参与的过程是各种活动、观念和知识与学生个体建立意义联系的过程。只有当知识与学生自身有关系、有意义时才能被学生吸收。杜威也指出,关于“怎样做”的知识是最能令人不忘的知识。正是通过“做”,知识与个体之间建立起了关联,知识才会永久不忘。参与使知识与学生的精神形成意义关联,使知识真正地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而缺少个体主动参与获得的知识,就是“无源之水”。只有通过参与所获得的一切,才是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正如华盛顿儿童博物馆的墙壁上的格言:“I hea r,I forget;I see, I remem ber;I do,I understand.(听到的,过眼云烟;看见的,铭记在心;做过的,沦肌侠髓。)”在参与过程中,学生投入进去的并非仅是智力和技能,而是所有的一切,包括躯体、情感、精神、心灵等等。因此在参与过程中,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加和智力的提高,更是身心的发展和精神状态的更新。此时,学生就不再是教育的“旁观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了。
4.理解
对自然我们可以解释,而对“人”我们只能理解。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就在于它关涉到情感,它渗透着体验和感受。学生拥有了丰富、充实而深刻的体会和感受,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文本”(课程和教材)的深处,去领略其中的精髓和精妙的生命意味。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就是把学生个体将自己的视域向“文本”对象的视域开放,两者互相交流和接纳,实现视域的融合,并在融合中生成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学生总是在自己的当下情境中带着自己的思想痕迹进行学习的,在参与“文本”世界过程中投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理解,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理解,获得生命意义的生成。也正如《理解与教育》一书中所说:“理解带来的视野融合,也就是新的地平线新的意义的获得。这种融合的过程不断地发生着,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有价值的意义世界,构成绵延不断的历史和生活,构成了不断生长的经验。理解者的视野处在运动中的开放过程,它不断地变化着、扩展着、运动着,这都是通过理解而实现的。理解者通过理解,把地平线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在理解中,他不断地构成新的视野,不断地获得新的世界经验,他生活的地平线就不断地变化扩展。[15](P29-30)”
5.反思
反思就是反省和思考。只有不断地对所学的东西进行反思,才能把握知识各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否则获得的知识犹如一堆没有经过消化的负担。杜威也认为“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是偶然得到的知识,才能具有逻辑的使用价值。[16]”其实,中国古人也是十分重视反思和内化的,所以他们强调学与思互相结合,读书与体察互相结合。特别是朱熹,在《朱子语类》里关于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例如:“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便思量这事合如何,学字甚大,学效他圣贤做事。”(卷二十四)、“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卷十一)、“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卷十一)。其实“思”、“反求诸身”、“虚心涵泳”和“切记体察”这些都是强调个人在学习和读书时应该在反思的基础上将知识内化。知识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常常是静态的,它需要学生去感悟和体验方可被激活。现实教育里,学生往往死记硬背一些没有活力的概念。这种“知识”没有被学生吸收、消化,没有被学生内化为自身的经验,没有转化为学生的智慧,它游离在学生的生命和体验之外。明代的王守仁就曾经提出,学生依其不同的为学方法可获得三种知识:“记得的知识”、“晓得的知识”与“明得的知识”。“晓得的知识”是指学生对知识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这种知识仍然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而“明得的知识”则是一种内在的知识,是一种经过长期的实践体验与思考后获得的知识,它既是对内在良知本体的明了,也能自觉地外化为行为。[15](P31)反思和内化是将知识个性化,在整体上予以领悟和把握,从而发现新的启示和意义。学生认知的目的不是获得关于事物“是什么”的客观知识,而是要将这种知识内化到主体自身的情感中,成为学生自身价值、信念和态度的知识。停留在学生情感和个性之外的知识,对他们来说都只是表面的知识,还未进入他们的心灵。只有在反思和内化过程中,通过感悟、移情和想象,才能使相对静止的知识在学生的心灵中被激活,从而产生新意义。此时的外在知识便成为了与学生自身血肉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明得的知识”。
三、“体验的人”与“人的体验”:功夫与本体合一
体验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其运用并非易事。在人文领域,每一种教育方法的使用都具有鲜明的“本体性”,“他”不可能被做成科学实验室里的仪器,可以复制性地简单操控。为了使人文方法区别于科学方法,我们将人文方法称为“本体性功夫”。科学方法就好比是“武器”,它的应用只需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来操练(比如扣动扳机)便可,而人文方法却是“武功”,它作用的发挥不是靠外在的“工具”,它需要我们身心一体的投入,身体本身(挥拳踢脚)便似“武器”。教育方法不同于科技操作,它无法实现内在傻瓜化和外在智能化,它需要内化于主体自身方可见效。正是为了区别于外在主导型的工具性方法,我们将体验这样一种本体性的方法——用中国所谓的“功夫”来表达!拳头打人是本体性功夫,手枪打人是工具性方法。作为“功夫”涵义的体验意味着“修行”。提到“修行”,似乎涉及宗教的领域,但修行并非宗教所独专。古代中国儒道思想强调知行合一,尤其重视“体”认、笃“行”,所谓修身、修心、修德必须落实为身心整体的切己体认与自觉修持,这实际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质的修行。作为教育方法的体验,它必须由外在的方法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自觉,成为与自身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一过程就是“修行”。无论我们对体验这一方法了解得多么透彻,如果不践履和内化,它永远都如别人口袋的钱,到不了自己腰包。正如惟有“用锤子”而不是“看锤子”才能真正把握锤子一样,只有运用体验的方法才能使其转为内在功夫。其道理就如同真正的打字方法不是体现在打字者聪明的头脑里,而是手到心会地体现在将手和键盘“合在一起”的打字者的动作中那样。“方法”是一种认知,而“功夫”是一种体验,体验涵蕴认知,认知未及体验,体验是“实践性智慧”而非“知识性智慧”。“功夫”是“做”和“练”出来的,不是“说”和“看”出来的。古人王坤说“君子之为学,所贵乎知要,而尤在乎体验”(《继志斋集》,卷七《观澜亭记》),朱熹说“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朱子语类》卷十)[17]。因此,作为“功夫”的体验需要我们去体验,它不是一味静观枯想的“冥思”,而是充满创造活力和坚持不懈的“践行”。它不仅依赖于“心”的静中知道、了解、领悟,还要将这种“知”和“悟”融入到形躯之身的活动和展现中,成为动中的“体”、“会”。只有“体之于身”才算“会”得根本,“心”之“思”必须落实为“身”之“能”才能受用,静中之“知”必须落实为动中之“会”,才成其为彻知、真知。从“知”不“知”的“心”官“思”虑,归于“会”不“会”的“身”心一“体”,就是从“方法”到“功夫”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是从理论到实践,更是身心境界拓展与提升——“修行”的过程。体验这样的“功夫”,“是在我们肉身里培植和练就出来的精神和‘道行’[18]”。体验成就境界,它是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教育“方法”,是与人的目的、价值合一的“方法”。也就是说,体验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功夫,也是本体。
[1]安延明.狄尔泰的体验概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5):49.
[2][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李建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9.
[3]张祥云.人文知识视野中的教育探询[J].复旦教育论坛,2004(6):19.
[4]思勤.奥修故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166—167.
[5][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00—101.
[6]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9.
[7][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卷(M).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第4次印刷):12.
[8]徐建顺.托尔斯泰:怀疑,还是疯狂[EB/OL]h ttp:// book.sohu.com/2004/07/06/10/ar ticle220871070. sh tm l 2004—7—6.
[9]张祥云.走出人文教育的思维困境[J].高等教育研究,2003(3):25-29.
[10]舒可文.美是幸福的时刻[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26.
[11][印度]奥修.春来草自青[M].虞莉,顾瑞荣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176.
[12]转引自孟耕合.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9:33,37.
[13]陈敏.朱子论诚敬[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19-121.
[14]转引自刘为开.专注的境界[J].湖北招生考试,20 09(252):19.
[15]转引自赵联.体验与教育——体验的教育学意蕴初探[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4:29—30.
[16][美]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1.
[17]张再林.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8(4):100-111.
[18]张祥云,罗绍武.对话的意蕴——基于教育立场的多维理解[J].高等教育研究,2011(7):32-39.
(责任编辑 陈剑光)
Experience:Humanites Education On to logy
ZHANG Xiang-yun CHEN Li
It is necessary to experience while being alive, and being alive can be con firmed on ly by experience. Humanistic education is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teaches people how to live well. Therefore, experience has significant value to humanistic education. Experience is the educational method with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And it is the unity of purpose and value. Experience is both method and purpose. In order to distinguishit from scientific instrumental method, we call experience as on tological kungfu. We should understand experience wholly, not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but alsofrom ont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experience is one way of being, the proces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process of life experience is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becoming them selves. From the point of methodology, experience is the basic method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way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clude being sincere and absorbed, particip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humanistic education; experience; on tology; kung fu
book=3,ebook=26
G40-02
A
1672-0717(2012)03-0003-10
2012-2-18
张祥云(1964-)江西太余县人,教育学博士,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人文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