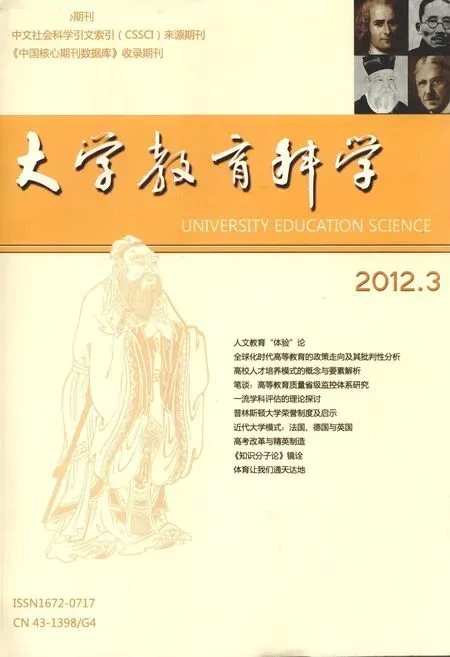高考改革与精英制造
2012-04-03彭拥军
□ 彭拥军
高考改革与精英制造
□ 彭拥军
高考一旦成为分配教育机会和社会机会的工具,它就不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促使个体进入不同社会职业岗位、充当不同社会角色从而拥有不同社会地位并享有有差别的权力和义务的作用,而且使高层次教育成为获得权力、财富和身份的最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客观依据,并带有炫耀性意味。高等教育大众化则使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人们必要的生活准备,甚至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泛泛而谈的高等教育逐步不再具有卓越含义。大众化背景下的高考,不仅要关注卓越,也要关注学生与专业之间的合适性。
高考;高考改革;精英制造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指出的,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1]。它实际上表明了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太学)是国家养贤之所、制造精英的机构。在当今中国,高考一头连着基础教育,另一头连着高等教育;一头连着个体的出路与命运,另一头隐含着社会职业继替和社会阶层生产与再生产。高考制度作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分割和利益共谋的制度安排,它把个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国家对政治控制的需求统一起来[2]。因此,高考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努力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寻找满足大众需求与实现精英筛选之间的平衡点。
一、恢复高考:文化资本成为精英识别符号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压力和激励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在我国最具号召力和革命性的字眼。如何看待社会改革与转型情境中的教育改革与转型,不妨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表明我的立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侯,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改革与转型[3]。特定的教育转型往往与特定观念、特定需要相关联,并且因为原有教育体系无法直接满足发展导引的新需要从而引发了教育改革。
1977年恢复了考试取人的高考制度,当年招生27万人;1978年增至40万人,录取比例分别为4.7%和6.8%[4]。因为当时适龄人口中初中、高中入学率都较低,能上大学的人在同龄人中小于百分之一,难怪当时人们使用“天之骄子”来指称大学生,以此来表明大学生的稀缺性和精英性。恢复高考使知识人获得了地位和声望,它实际上恢复了知识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再一次回归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个人对教育机会和社会机会的享用具有排他性,高考实际上也成为众多利益相关者利益争夺的工具。对青年学生而言,它把知识改变命运由头脑中的信条转变成客观事实,从而对他们产生强烈的社会动员作用;对家庭而言,高考成功可以使社会中上层家庭的阶层地位得以保持或提升,至少免于沦落,中下层家庭则对高考寄托着向上社会流动的希望;对基础教育而言,高考使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的使命明确甚至神圣起来,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行为具有强烈的导向和制约作用;对社会而言,高考传递了社会流动的依据由先赋因素向自致因素转变的信号;对国家而言,高考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选纳贤良的机制。
高考一旦成为分配教育机会和社会机会的工具,它会使知识变成一种资本,对不同人群产生区隔。尽管个人在高考上的成功往往是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高考包含了许多为人们所认同的自致因素,并且先赋因素必须通过个人自身努力才能较好地实现,所以在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手段来替代高考制度时,它不失为一种最具可操作性的选纳贤良的工具。
由于高考在我国的特殊意义,高考成功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资源的利用和社会地位的占有上成为优势群体。这种优势,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和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可以提高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它就像科举制度盛行时期的所谓“科班出身”那样,是获得权力、财富和身份的最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客观依据,并带有炫耀性意味。正如凡勃伦所宣称的,这是荣誉准则、竞争本能在起作用,就像人们为了在社会上获得地位与声望,只有通过消费商品(或服务)—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以达到与他人的歧视性对比的目的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炫耀性消费。所谓炫耀性消费,又可称为“显眼的消费”、“ 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即富裕者总是要通过购买一些昂贵奢侈品或大讲排场疯狂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优胜者可以保护或者提高他们的尊严。
有必要指出的是,高考制度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形成不同个体对文化资本实际占领机会和占用能力的差异。因为高考实际上把获得文化资本的机会当成一种完全原始性的财产赋予给高考成功者,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5]。当高考制度充当成圣仪式时,文化资本自然就获得了走向精英的合法性基础。文化资本与物质层面享用能力的低层次、低门槛以及产生社会区隔的低持久性不同的是,文化层面的享用能力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和专门性。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享用能力之间的差别就如喝茶和品茶的差异,喝茶能力几乎与生俱来,而品茶能力就需要天赋加习得。正因为这样,文化资本不但具有很强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而且像一种身份标签,可以帮助实现固有秩序和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保证现有秩序的合法化和自然化。恢复高考重建了高等教育制造精英的合法性,使知识的社会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开始出现有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所指出的:未来社会中“成就原则战胜归属原则(归属原则指通过社会继承或分配取得个人地位)……社会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权力和知识的结合程度……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按照他的‘智商和努力程度’来决定的”[6]。
二、恢复高考:高等教育制造政治精英
恢复高考,实际上是与社会的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相呼应的,这些制度性变革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并波及文化和观念等其他诸多层面。作为社会变革组成部分的高考,实际上成为了观察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
首先,高考恢复与社会分层格局变化相呼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形成了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和资源控制格局。国家控制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而资源的实际分配权力又掌握在各级各类干部手中。因此,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既是社会权力“合法性”的风向标,也影响不同出身者的实际命运。高考存废是影响知识人命运的制度性手段,影响着知识人的命运起伏。在政治分层的社会格局下,反映新中国知识与权力结合状况的重要尺度就是干部录用标准。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曾提出过“任人唯贤”的路线,即“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7]。此后在1964年,毛主席还提出过选拔接班人的5个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必须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8]。这些标准实际上没有明确提出技术的、业务的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要求。所以,新中国的官员在一段时间内,文化水准不高(到1987年,官员中大学毕业程度者也仅为13.5%),这实际上也给知识分子进入政界预留了巨大空间。
高考恢复后,知识逐步成为通向权力的康庄大道(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状态突变到大学生天之骄子的高尚地位,确实引人注目),因为国家一步步强化了从大中专生中吸收干部的作法(即“大学生包当干部”)。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9](P37-39)的口号,并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9](P286);中组部则于1983年制定了《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下称《要点》),明确规定现具有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年龄在50岁以下的干部到1990年要基本达到高中和中专水平(《中国大百科全书》相关条目)。从此时起,文凭牵动了千万中国官员的心,人们称之为“文凭热”的现象急剧升温。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1988年的10年间,官员获得大专学历的有151.8万人次,获得中专学历的达97万人次,高中学历的达100多万人次。到1991年底,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已占干部总数的71%①干部专业化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要有从事管理活动的比较固定的程序和规章;第二,专职或兼职官员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行政管理上;第三,它需要专门训练以保证办事效率和权威性;第四,需要有合理的官员选拔制度来保证官员更替的有序性和有效性。。
其次,高考改革与国家权力占有格局变化相适应。客观地说,“文革”让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城里的孩子还要上山下乡(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现的政策性引导的大规模逆向社会流动)。当然,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忘记学习(这些人大都成为了高考恢复后的受益者),尽管当时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氛围也远远不够。恢复高考意味着用人制度从注重出身转向注重知识和能力以及个体自身努力,也就是从注重先赋因素转向注重自致因素,虽然接班顶替等制度一度仍在推行,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确实拓宽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强调干部“四化”的要求。由于干部四化中的知识化和专业化与高考的知识取人走向完全一致,加之国家明确提出并实施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高考除了分配高等教育机会外,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使命就是选拔潜在干部。事实上,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一度确实成为政务性干部的重要来源;技术性干部也主要来自大学生群体(他们具有干部身份的主要标志是他们由人事部门进行身份管理,从而制度性地区别于工人)。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一方面使大学生更加顺利地进入技术领域和干部队伍,并具有了制度赋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优先性,另一方面使干部继替有了明确的知识和技术标准,有利于干部队伍走向专业化②新华社1993年5月9日电。。可以肯定,恢复高考实际上使高等教育系统成为新中国文官制度的支持系统甚至就是文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安排使高考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并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特殊的政治生态。
简而言之,随着干部文化层次的大幅度提高,文凭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尽管不是决定性的)通向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学历慢慢地向政治(其核心是权力)靠近,知识和人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根据蔡禾等人1983年对职业声望的研究,专业人员的声望评价首次超过了官员层而居于第一位[10]。
三、恢复高考所代表的教育改革:理顺精英替代的社会秩序
一般而言,教育具有社会化和社会筛选两大基本功能。简而言之,社会化功能就是使人通过教育成为特定社会的合格参与者和建设者;筛选功能则是使个体进入不同社会职业岗位,从而充当不同社会角色,拥有不同社会地位,并享有差别性的权力与义务。
首先,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会引起人们地位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产生。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尽管有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但实际上存在三个基本集团,即职业官僚、民间精英和普通民众三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其中职业官僚掌握社会运行,发挥社会向标作用。而以教育内容为主要选拔依据的科举制度成为我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支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理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的依据越来越呈现出由先赋因素向自致因素转变的趋势。高考成功往往是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包含了许多为人们所认同的自致因素,并且先赋因素必须通过个人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在公正的考试制度下,权力、财富等因素难以直接发挥作用。高考制度确实不失为一种最具操作性的社会筛选工具,有利于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流动。
其次,高考充当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的功能。从考试实践看,公正的选拔性考试都具有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的功能。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其考试标准比较严格和客观,也比较制度化。科举制度本身基本上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把学问这种成就性因素作为官员录用的基本标准甚至首要标准,它确实起到了提高官员素质、改变官员构成背景,从而优化社会政治精英结构的作用,为家天下的政治制度增添了许多活力。因为学问不能世袭,即使是身世较为显赫的家族,如果其家族成员不努力或缺乏天分,也会家道中落。
可以肯定,高考制度在相当一段时期客观上造成了个人的合理社会流动,从而缓解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也模糊了社会阶层边界,促进了不同阶层间的交流。高考或其他社会选拔性考试制度必然近乎天然地充当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从反面看,国际经验和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都表明,缺乏合理的教育筛选制度,不但容易遗漏社会英才,而且容易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动乱的制造者或积极参与者[11]。
再次,高考除了分配教育机会和预演分配社会机会和社会身份地位外,还再生产社会结构和形成新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认为的那样,教育体制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的制度基础。他将一场细腻的、微观的除魅放在现代教育制度背景中展开:教育场域和权力场域的等级同型性使得强势社会地位的人可能利用文化资源,尤其是知识分类、资格差别和招生过程来维护其政治和社会权力地位。于是,教育代替门庭、宗教和直接的政治、经济背景,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机制实际上既可能抹平社会不平等,也可能生产或复制社会不平等[12]。
四、新一轮高考改革:应对大众化时代的新挑战
1999年触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人们必要的生活准备,甚至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泛泛而谈的高等教育逐步不再具有卓越含义。诚然,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不能单纯关注卓越,也要关注学生与专业之间的合适性。与此相应,高考改革要使高考既能够反映考生的生理心理素质、知识能力结构差异,从而既为高校选择合适新生,也为考生选择合适高校与合适专业提供依据。高考在充当为国家、社会或高校挑选合适新生的手段时,也要成为促进人的发展之目的的重要手段。
首先,高考改革要凸显为大众服务的功能。当今,高等教育出现了以下变化:第一,高等教育边界逐步模糊。正如加塞特所言,大众化和普及化容易把校园的边界演变成国家的边界,将内部同外部分开的界线就变得相当模糊[13](P17)。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使高等教育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走向社会中心。由此,高等教育与国家、社会有了更加密切的互动,出现了把校园带进国家或者把国家带进了校园的新局面。第二,高等教育服务内容前所未有的扩张。克拉克•克尔对大学的特殊职能做过一个简洁的评述:大学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上的所有高等学校中间,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13](P29)。克尔实际上用另一种方式阐明了大学的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知识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第三,高等教育服务对象范围扩大。从高等教育服务对象看,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也是高等教育服务对象扩张的过程。大学最初是为社会精英服务的,而后又为中产阶级服务,现在则为所有人服务,不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13](P64)。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使高等教育服务对象在数量上大大扩张,服务层次和类型更加丰富。高等教育由单纯培养职业准入者进入更加广阔的领域,将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在注重培养毕业生找到职业技能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培养毕业生塑造职业素质;高等教育为初次从业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职业转换者提供职业转换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还要考虑终身学习与培训方面的社会需要,不仅面向即将走向职业岗位和需要转换职业的人群,还要考虑范围更大的人群,比如高等教育将成为老年人圆大学梦的场所和更好享用晚年的方式。
其次,高考改革要为精英高等教育的繁荣服务。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中,由于大学生数量的绝对增长导致了高等教育机构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际上也出现了教学和科研赖以生存的环境性质的变化[14](P1-21)。对学者而言,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充足时间思考研究项目或者从事学术工作和科研而不受干扰,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学者要有独立的时间,需要远离办公室和研究中心而较多地呆在家中,但这种做法又容易削弱学术团体,并可能对大学管理、学生训练和社会化产生负面影响;对高等教育系而言,会进一步增强它对政府的经济依赖,使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味道;对学生而言,上层和中层子女的入学率会大大高于工人和农民子女的入学率,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反而可能因为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突出,并且使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发生变化,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含义发生变化。
尽管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相伴随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容易遮蔽高等教育制造精英的职能,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指出,把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本来就是一种人为抽象。事实上,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在大众型高校中培养精英的功能仍继续起作用[14](P1-21)。制造精英与普惠大众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难以摆脱的魔咒。并且,以杰出为特点的精英本来就是一个意义丰富或者说含义模糊的概念,在很多场合里,精英都被狭义地视为统治精英。而广义的精英,可以指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取得成功并在职业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少部分人。诚然,社会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权力、财富和声望等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人们倾向于让精英来掌握更多社会资源,以更好地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因此,精英生产和精英循环的制造机制十分重要。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就指出,如果我们使美国100名最有权的人、100名最有钱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远离他们现有的地位,远离人际关系和金钱,远离目前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大众传媒,那么,这些人将变得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声望。因此,权力并非属于个人、财富也不会集中在富有者身上,声望并不是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15]。托夫勒则对制度化精英生产做了更为简明的注脚,他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其中基本的权力资源不外三种:暴力、金钱、知识[16]。
人们如何才能拥有这些权力资源并使之具有人们认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制度设计(比如高考或其他制度)来保障甚至放大权力。在中国,把教育视为精英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化手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传统中国,权力与知识的结盟是因为知识可以为权力所用,可以增强权力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权力可以保证知识产生更大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社会资源[17]。
[1]孟宪成.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40.
[2]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摘要[D].博士论文.
[3][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南京:世纪出版集团,2006:178.
[4]黄抗生,等.大学圆梦——从27万到600万[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0-15(01).
[5]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6]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42.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9:515.
[8]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28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蔡禾,等.社会分层研究: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价值[J].管理世界,1995(4):191-197.
[1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44-46.
[12]彭拥军.论高考的功能[J].湖北招生考试,2006(16):42-45
[13][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4][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
[15][美]米尔斯.权力精英[M].王崑,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16][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刘红,等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
[17]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责任编辑 黄建新)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lites-Made
PENG Yong-jun
Onc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orks as akind of mechanic to distribute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opportunity, it will not only inevitably promote individuals to enter in to different social occupations, to play different social roles, to have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and enjoy differen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role, but also make the higher education become a kind of tool to get power, wealth and status with a conspicuous means. In the procession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necessary preparation for life, even a kind of right and obligation. Higher education by itself gradually no longer means excell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mak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excellence, but also to the suitability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s.
collegeen 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lite-made
book=98,ebook=49
G 649.21
A
1672-0717(2012)03-0098-06
2012-04-15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研究”。
彭拥军(1969-),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