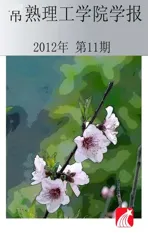港岛奇葩——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诗歌卷》
2012-04-02计红芳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翻开厚厚一本400多页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诗歌卷》[1](以下简称《诗歌卷》),作家数量之多、作品题材之丰富、语言风格之多样、创作手法之千姿百态,令人为之惊叹震撼!在高度商业化、快节奏生活的香港,从事文学工作是非要有西绪福斯的勇气不可的。诗歌是文学中的小众,坚守诗歌理想、追求自由的艺术王国,那更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当我们看到出现在面前的这本厚重之作时,谁能否认这是港岛的一朵奇葩呢?
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当代诗歌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期间的发展变化及成绩有目共睹,基本上呈现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多元并存,并以现代主义为主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在左右对峙严重的50年代已经初具雏形。
50年代,避难至此的难民诗人如力匡、徐訏、徐速、赵滋蕃等人给香港诗坛带来了“怀乡”的浪漫主义诗作。同时,马朗、王无邪、叶维廉等南来诗人避开左右对峙,开始“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他们创办《文艺新潮》、《诗朵》等刊物,试图从艺术上建立理想的乐园。除此之外,还有老诗人舒巷城等发出的映照香港本土的现实主义声音。
这三种类型的诗作在往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都有更为年青的一代继承发扬。重在情感抒发和心灵表现的浪漫主义诗歌在本土诗人钟晓阳、80后诗人吕永佳等的诗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钟晓阳的《绝色》:“他的下半生/和她的下半生,加起来/比一生还长久,比永生还永久。”“如同两尊高贵的塑像,/人间绝色。”如果说钟晓阳的爱情诗比较温和唯美,那么吕永佳的爱情诗则比较含蓄凄苦:“你不必知道/有人在这里守候”(《石头》)不管是哪种风格的诗歌,都带有浪漫气息。本土诗人关梦南、邓阿蓝、叶辉、李国盛、卢劲驰等的诗作中则延续着根植于香港和对香港社会各阶层生活的熟悉与关心的现实主义诗风。如邓阿蓝《公厕内》、《野生的清凉》中对香港社会各阶层小人物生活困窘的关切,卢劲驰的《后遗——给健视人士·看不见的城市照相簿》对残障人士生存状态的关注等都是极好的诗作。另外,还有傅天虹、张诗剑、秦岭雪、王一桃、韩牧、原甸等内地南来或者外来诗人①本文所指“南来诗人”特指大陆南下移居香港的诗人,“外来诗人”特指大陆以外移居香港的诗人。对现实主义的一往情深。
现代主义诗作在三者中比重最大,几乎贯穿着整个香港诗坛,而现今的香港诗坛也是以现代主义创作为主。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在经过50年代后期草创阶段的虚无、晦涩,60年代发展阶段对现代诗的检视和审思之后,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自70年代以来,伴随也斯、羁魂、黄国彬、张景熊、王良和、邹文律等香港本土中青年诗人的逐渐成长,再加上戴天、林幸谦、杜家祁等外来的新老现代主义的奉行者,这些充满创造活力和艺术潜质的现代主义探索者构成香港诗人的基本阵营,并把香港现代主义诗歌一直推进到21世纪。他们在意蕴、诗艺、形式、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貌。单从意蕴上来看,有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审视和批判,如饮江的《新填地》;有对自然乡村、渔港之美的书写,如彭砺青的《乡村女孩》、《回到大澳》;有对政治和女性进行隐喻叙事的《男体二章》、《处女》(林幸谦);有对语言、生命、爱情等存在进行哲理探寻的《当我沉默而疲倦》(陈德锦);有对基督教的宽容博爱精神进行形象描绘的《我的咖啡》、《姐妹》(胡燕青)等。从诗的形式上看,羁魂《盘中诗》由四周向中间“盘”字顺时针螺旋形行进的诗行、张景熊《脸》中插入的空白photo等都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表现方式,给你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
现代主义诗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跟诗人们对诗艺的不断探索和对传统的继承有关。早期的诗人主要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当各种手法操练一遍以后,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告别了早期恶性西化的虚无,现代主义诗人们不仅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长处,同时向中国古典诗歌以及五四新诗传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袁可嘉等现代主义诗歌传统汲取营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继承与创新,诗艺基本趋于成熟。胡国贤认为:“从古典、浪漫、写实到现代,香港诗作者既回归传统,又敢于创新;既接受西方,又不忘中国;既忠于自我,投入生活,又呼应时代、关注社会、家国、民族,以至全世界。”[2]
当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马朗、昆南、李英豪等人竭力倡导现代主义诗歌观念之时,就有部分学者对香港的现代诗进行反省、检讨。从50年代末李维陵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学》从诗与现实关系角度切入检讨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得失,到60年代后期《盘古》(戴天、古苍梧主编)杂志社主办的《近年港台现代诗的回顾》座谈会关于“诗的交通”(语言、技巧、观念)和“诗的历史任务”(继承与革新)的讨论,再到《林以亮诗话》[3]等理论著作对“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反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认为现代新诗不仅要向西洋诗借鉴诗歌形式、表现技巧,还应从中国古典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中吸取养料,形成了熔现代与古典一体的现代主义诗学主张,有人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诗学,它对70、80年代甚至90年代至今的诗坛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黄国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诗必须要现代,但又反复申明:“现代不等于西化,亦不等于虚无。这里所谓现代,是指运用活的语言,表现此时此地的经验、感受或生命形态的意思。”[4]3羁魂、何福仁等人也表达了他们熔化古典、锻造现代的诗学主张。总之,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们都认为新诗必须纳入到中国诗传统中去才能实现其现代化。《诗歌卷》中所选诗人蔡炎培、戴天、温健骝、古苍梧、钟玲玲、黄国彬、羁魂、康夫、何福仁、秀实、王良和等的部分作品都比较注重把传统融入现代,即使如蔡炎培、戴天、温健骝等早期深受超现实主义诗风影响的诗人,也很快就在“古典”诗歌传统中找到了“现代”的立身之处。
二
说到香港诗歌,马上会联想到香港本土性,而香港本土性往往与都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所以大部分香港诗歌是以都市生活体验为描写对象,书写诗人对城市独特的心灵观照。由于诗人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个性特点、审美趣味等的不同,他们笔下的城市体验各不相同,对城市的反思与批判也各具特色。香港诗歌的都市性是随着香港国际性大都市的形成一步步显现出来的,主要起始于70年代。而在70年代经济腾飞之前的50、60年代,由于怀乡、西化等众所周知的原因,诗坛基本上是被大陆南来移民诗人和追求真善美艺术理想的现代主义诗人所把持,本土性、香港性的诉求痕迹很难追寻。我们在马朗的《北角之夜》中依稀寻到香港北角的熟悉感觉,但由于其移民身份,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从“溪流”、“春野”等意象中读出他对内地的怀念,感受到他与香港的疏离。选本中的这一首也是第一首的诗歌,就是本土与移民视角的复杂纠缠,这似乎暗示了香港诗坛本土诗与移民诗的相互渗透。《诗歌卷》选入马朗的其它两首《布勒东诗论偶拾》、《岛上的欲望号街车》鲜明地呈现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观以及逐渐弥合了移民与本土的距离而对香港本土的热切关注。古远清认为,香港新诗的发展“是一个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过程,也是‘南来’与‘本土’从对峙逐步走向融洽的过程。”[5]112
翻开选本,很少见到50年代、70、80年代大陆移居到香港的被称作“南来作家”的如力匡、徐訏、徐速、傅天虹、秦岭雪、王一桃等带有比较明显移民心态的诗人,而主要选入的是本土诗人(也斯、叶辉、洛枫、淮远、游静、樊善标、邓小桦、洛谋等),或者是经过时间的洗涤早就融入香港本土的南来或外来诗人(马朗、蔡炎培、戴天、西西、关梦南、杜家祁等),还有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的很难说清楚其身份的诗人(马若、长随、王敏、廖伟棠等)。这些南来或者外来诗人的移民诗与本土诗对于香港诗坛来说显然有差别,但又互相渗透。不同的可能是移民诗歌的语言(普通话)以及面对香港都市繁复影像时的疏离心态和批判的表述,但随着居港时间的长久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融入,很多诗人已经把香港当作自己的栖身之地,客观地书写着都市文明以及它带来的各种问题。当他们融入香港这个社会时,一方面本土诗人的题材、语言、观念等会影响移民诗人,使他们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移民诗人的一些优点与传统也会反过来影响香港诗坛。比如老诗人戴天,他对香港诗坛的影响巨大,“不仅在于他与古苍梧创办诗作坊,培养和扶持了好些有成就的诗人,而且见诸于他开设诗作坊的传统被关梦南等诗人承接下来,至今仍是促进香港诗歌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更见诸他的口语诗启发或影响了诗作坊成员例如钟玲玲和淮远,这两位本土诗人都是用全然的普通话写诗,而且是口语加日常的普通话。”[6]
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移民城市,所以当本土诗人、内地南来诗人、外来诗人抛开一切束缚,让自己的心灵驰骋于辽阔的宇宙时,他们也就弥合了互相之间的界线。就以“九七”后内地移民香港的诗人廖伟棠为例。他说:“香港不是我的家,我不觉得任何地方是我的家”,“即使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者北京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7]现实生活中的他经常在内地、香港以及全世界各地行走,而他的诗歌也主要是对自由生命的书写,不管是《读廖亦武狱中诗集〈古拉格情歌〉》,还是《土豆多好》以及《赞歌》,都充满着对心灵自由的赞许和呼唤。如《土豆多好》,诗人把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与人类做了对比,欣羡自然界中生命存在的自由奔放,而对“没有根茎、花瓣和果实”、“没有幻梦、色彩和声音”的“我们”提出了“向谁奉献我们的存在”的疑问。
说到香港诗歌的本土性,不能不提到也斯。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诗人,而主要是由于他对香港现代化都市的客观审视。费勇认为:“面对大众媒体盛行的香港社会现实,也斯并没有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去抵抗,或者以欣然的态度接纳,而是把这种物质因素化为激发自己创作的源泉,这使得他的诗作带有后现代色彩。”[8]100也斯是一个执着于诗歌艺术探索的诗人。他把自己置身于后现代的平面化的都市社会中,以多样的艺术手段,特别是具有现代科技特征的声光手段,如摄影、舞蹈、电影、音乐、绘画等,形成自己的都市观照的特殊角度和声音,同时寻求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转化与组接。我们来看《诗歌卷》中所选的几首,如《香港历史明信片》,有反思香港文化身份的浓烈意味:“我们如何在往昔俗艳的彩图上/写出此刻的话?如何在它们中间描绘我们?”《静物》采用诗歌与绘画结合的手法进行书写;《异乡的早晨》、《莲叶》、《蔡孓民先生墓前》等,则是作者置身于西方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对东方文化的反思,“从中国古典山水诗和咏物诗中得到的启发,以中国文学的含蓄而富于弹性的特质,写现代都市的情怀”[9]。可以说,也斯的诗是古典、传统、现代、后现代相互交融的产儿。在他的影响下,洛枫、罗贵祥等青年诗人继续着后现代主义诗艺的探索,但遗憾的是,后现代主义在香港没有形成大的声浪,几乎被淹没在现代主义诗歌的洪流之中,有时,两者很难区分。
本土性的书写同样离不开对香港殖民身份的思考。其中游静的诗很有代表性。她的诗中经常提到“西西”,并不仅仅因为她喜欢读西西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她和西西一样对“香港身份”的反思。如她的《港台中飞机诗》,作者采用港台中三地不同的飞机意象的对比写出了“究竟是台湾人、中国人、大陆人、香港人”的身份焦虑,最后明确点出了香港意识,并指出不管历史如何变迁,香港人应该“学习感激与自强”。可以说这是一首非常本土的香港诗。还有《英国航空》,作者通过在英国机场的一次切身体验再次审视了“香港人”这一特殊身份。在他者眼里,香港如同“一件无人看管的行李”,可以被随意处置,甚至毁灭,诗作里面透露着诗人对后殖民主义英国的霸道无礼、趾高气扬的批判锋芒。
三
《诗歌卷》中佳作连连,手法多样,如西西《热水壶》、《蝴蝶轻》、《长着胡子的门神》,黄婉玲《大树》等运用童话手法的精彩诗作;杜家祁《女巫之歌》、《雌鱼》,陈丽娟《女大力士之歌》等女性意识较强的诗作等等。还有像廖伟棠《读廖亦武狱中诗集〈古拉格情歌〉》、谢雪浩《瞬间——致无名的勇者》等正面描写1989年“六四”事件、带有极强批判锋芒的诗作,可以看出编者超越政治的审美眼光,也可见香港不同于内地诗坛的独特性。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从20世纪30年代生作家一直到80年代生作家,涵盖面极其广泛,共收入近80位诗人。30、40年代生的老作家,50、60年代生的中年作家,70、80年代生的青年作家作品选入的比例基本均衡,各占三分之一。作家的身份多种多样,有南来、本土、外来之分。所选的诗歌写作时间从1957到2008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并兼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多样化的创作方法。这些都可以看出编选者的用心之处和独到的眼光。香港作家身份的判断一直以来都是难题,众说纷纭。我们允许存在不同的分类依据,只要合情合理。但是读完整本诗选,略有遗憾。比如孟浪,原是大陆新生代著名诗人,1995年去美国发展,直到2006年才移居香港。为什么他能入选,并且选了三首,其中两首都写于2006年以前。这一类的问题比较明显,如曹捷、长随等,同样让我疑惑不已。如果孟浪能入选,为什么在港居留10多年、对香港诗坛影响深远的余光中的书写香港的诗作没有被选中?编选者本身是内地移居香港的南来诗人,是否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了力避人情嫌疑,而很少选入南来诗人的作品?否则为什么像犁青、王一桃、秦岭雪等相当有成就的南来诗人没有入选?还有像老诗人舒巷城70年代的《都市诗抄》这样的厚重之作也没有出现在选集中。这些都是本诗选在突出“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同时遗留下来的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
[1]黄灿然.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诗歌卷[M].香港: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新加坡青年书局,2011.
[2]胡国贤.香港新诗五十年(代序)[M]//香港现代诗选:1946-1996.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7.
[3]林以亮.林以亮诗话[M].台北:洪范出版社,1976.
[4]黄国彬.文学的欣赏[M].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 6.
[5]古远清.香港新诗六十年[J].江汉论坛,2009(12).
[6]黄粲然.序[M]//黄粲然.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诗歌卷.香港: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2011.
[7]苏更生.廖伟棠:无国界诗人[N/OL].东莞时报,2011-09-04(B08).[2012-09-10].http://dgtime.timedg.com/html/2011-09/04/content_730099.htm.
[8]费勇.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均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2003(5).
[9]也斯.电影和诗,以及一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代序)[M]//梁秉均卷.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