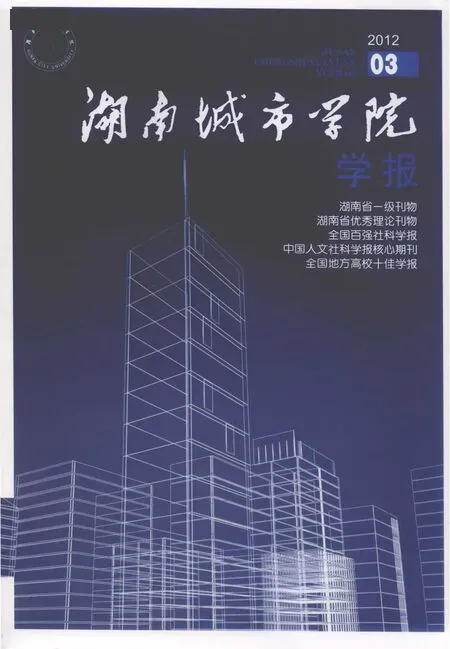围观效应下时评的社会责任
2012-04-02谢国芳
谢国芳
如今,网络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其中受其影响,改变最大的还属新闻传播。在新媒体初起时,热点事件的落脚点与扩散点往往由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占据,其传播路径一般可概括为:传统媒体发端—网络转载—回归传统媒体;而新媒体盛行的现在,特别是彰显出强大媒体属性的微博这一平台风行之后,新媒体所呈现出的时效性强、人人都是新闻源等特点,正悄然改变着新闻热点的传播路径:新媒体引发热点事件—传统媒体落地—网络传载—回归传统媒体。[1]可以看出,后一种传播路径将一个新闻事件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炒了两个回合,这种互动式传播使本来的网络围观现象扩展到传统媒体,产生了影响更大的围观效应。在这一前提下,原有的时评也在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时评是与网络几乎同时兴起的新闻评论文体概念,与原有报纸新闻评论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作者无限制,可以是传统媒体的评论作者,也可以是自由撰稿人,更可以是匿名的网络作者;二是时间无限制,新闻事件报道出来,时评马上就展开评论,不必受传统媒体出版、刊发、播出周期的限制,而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时评还可以跟进做层层深入的评论。现在发表评论的地方非常多,既有报纸上开辟的时评专栏、专版与言论、杂文栏目,又有网络上设置的评论栏目与频道,网络上的新闻事件报道的文末还有“我要评论”窗口,论坛、微博上更可以任意发表评论。不过,本文只就针对新闻事件而发的独立成篇的时评来说事,不包括三言两语的跟帖式评论。
目前的时评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评论者,也是新闻事件围观的参与者。俗话说:“旁观者清”,一旦时评作者也参与到围观队伍中来,其评论要做到公正、客观、科学、准确就更难了。这就要求时评作者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担当,更正确地定位好时评应该担当的角色。
网络围观,是发生重大事件时网民集中关注、发贴、提供信息等的一种现象。现在这种围观一般会延伸到传统媒体,它的名称也相应的应该叫做新闻围观了。新闻围观有3点积极意义:1.对事件的监督作用;2.对正义方的声援作用;3.对非正义方的警戒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既然是围观,许多观众聚集在一起,边看边议,难免有人发一些不冷静、不理智甚至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时就更需要有专家眼光的时评来进行引导,让事件朝妥善处理的方向发展。总之,在围观效应下,时评正当的角色大致是四种:1.本质开掘者;2.是非评判者;3.舆情引导者;4.思想启蒙者。
一、本质开掘者。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形成围观效应的,往往是能够激起人们强烈情感的新闻事件。人们情感激烈的时候,最难冷静,最容易说偏激话,甚至做偏激事,这种时候时评有冷静思考新闻事件本质的义务与责任,千万不能跟着某些过激的人群起哄。就如2011年6月的“郭美美事件”,郭美美微博炫富之后,网友迅速聚集围观,说了许多对郭美美个人、中国红十字会非常不利的话,有的人甚至表现出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现行慈善机制的激愤之情。那么,郭美美事件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呢?本质就在于我们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普通百姓不知道慈善机构的钱是怎么用的,一见到这位小姑娘如此年轻就如此富有,且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就将她的钱往腐败上联想,结果导致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大伤元气。时评作者通过自己的评论,指出事件本质之后,剩下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中国红十字会澄清事实真相,且改革原有管理模式,做到公开、透明就可以平息事件,良性发展。
二、是非评判者。引起围观效应的事件,也许不一定有严格的是与非,也许引发事件的双方都是对的,也许双方都是错的。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有是非可以分的。这时时评就必须站在公正、科学、正确的立场上明明白白地讲出是与非,不能让读者未看时评时弄不清是非,看过时评之后还是一头雾水。近年来,每到农历“七夕”,商家与媒体大都会将它炒作成“中国情人节”。年轻人多以过洋节为时髦,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愚人节、光棍节……都过得不亦乐乎,看准其中商机的商家与媒体除了热炒这些洋节,往往还会让这些洋节中国化,以求获得更大的回报,“七夕”就这样成为的中国情人节。传说中的牛郎与织女是夫妻,他们一年一会的“七夕”过去也叫乞巧节、女儿节。如果“七夕”要成为一个现代人的节日,应该叫“夫妻节”,而不应是情人节。其实,中国古代曾有过一个类似于情人节的节日——三月三,要炒中国情人节可以炒作“三月三”,目前这种炒法炒错了地方。这些年来,过多少次“七夕”就有多少次关于“七夕”的文化围观,不少文化学者对将“七夕”作为中国情人节来炒持否定态度。笔者在2009年也写过一篇《“七夕”不是情人节》的时评同时发在本报与博客上。
三、舆情引导者。能形成围观效应的往往是我们社会的负面新闻、突发事件,这类新闻除了在网上形成群情激奋的局面,还与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相呼应,稍有不慎就会对事件现场气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当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们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当时的抢险工作本就非常艰巨,也存在一定的乱象,媒体记者与网民的情绪都非常激动,而发言人王勇平的这种发言与态度却在火上浇油,让有关部门更加被动。之前时评都还只是冷静地探讨事故原因,而王勇平的发言一出,有不少时评也加入了声讨铁道部的行列,有的甚至指名道姓批评王勇平本人。他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被网民嘲笑为“高铁体”。发言人是事件处理与媒体、网民之间的桥梁,在对舆情的引导作用上与时评人是一致的。这个事件对铁道部、对王勇平本人以及某些时评人都是一个教训。时评往往在追问事件本质的同时对舆情进行引导,力图使当事者、围观者尽快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并促成事件的妥善处理。
四、思想启蒙者。时评也可以视为评论新闻事件的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时评。思想启蒙也是时评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就因为他从现实中体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鲁迅弃医从文后,整理过古籍,写过小说、散文,但最后他选择了杂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就因为他觉得小说与散文的含蓄妨碍了他启迪民智的直接呐喊。
中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没有经历过西方那样的启蒙运动,走向民主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鲁迅那一代人没有完成的任务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力去完成。而且,目前我们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存在着比过去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思想启蒙的任务非常繁重。笔者既是时评版的编辑也是时评作者,我的时评主要评论方向是两个方面—教育与环境,二者都直接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人类文明要持续进步,时评必须在关注事件发生原因的同时,启发、引导人们关注未来、思考未来,克服自己的不良行为。
[1] 窦锋昌, 李华.新媒体时代热点事件传播路径的转变—以韩寒代笔门和三亚宰客门为例[J].新闻战线, 2012(4):40-42.
[2] 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