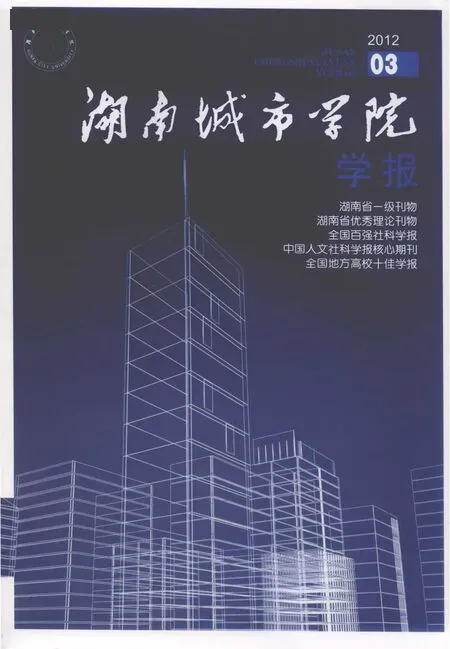自我体认的艰难与超越——龚鹏飞《漂流瓶》的知识分子立场解读
2012-04-02刘新敖
刘新敖
20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社会物质诉求急遽高涨,知识分子的处境日渐尴尬,不得不在坚持知识分子操守与放逐自我间痛苦抉择。因此,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便成为文学家们不可回避的课题,龚鹏飞以其创作实践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的体认,其新作《漂流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的成功和深刻之处正在于,通过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写出了知识分子因理想而叛逆、因自我放逐而无奈何和因追求超越而自我救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漂泊史。
一、叛逆者:自我确认的尴尬
作品描绘的是几个才华横溢、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许上游、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司马佳、玩世不恭却并不甘堕落的杨运仁、中规中矩却有满腔热情的汤亦武和杨彩霞,他们年轻、单纯、向上,在司马佳的号召下,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帮助边缘地区改变教育落后的现状,断然拒绝了大城市的诱惑,带着夺目的政治光环,只身来到了一个只有三条新街、一条老街的边远小城,执教于民族中学,追寻理想的序曲由此铺开。
文学叙事的魅力在于能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可供想象和思考的独特位置和视角,从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的确认来解读作品中的主人公,便不难理解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心理轨迹的把握和描述。司马佳及一同前往民族中学支教的五名大学生,无一例外地,还生活在自我的空间之中,在他们的大学生活中,自我还是完全的自我,自我的认同是完全、彻底的。司马佳以其天才般的口才、极强的政治天赋征服了校园,成为大学校园的风云人员,乃至当其决定带领队伍支教时,便成了政府官员眼中的新星、媒体的宠儿;典型的文学青年许上游生活得更加自我,写诗、对女朋友的无尽思念是其生活的全部。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我之外的任何东西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支配力量。社会的生存法则和游戏规则,让他们明白,做回自我也会如此艰难。
显然,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是尴尬的。这些满腔热情的大学生还来不及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不得不面对社会抛给他们的问题。司马佳因其政治光环及其表现出的领导天赋,成为了民族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并将在一年以后正式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于是,她开始了目标坚定、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年轻的女孩,或者说,作品中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激情飞扬,以出生牛犊之势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她放弃在省城安逸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在她认为大有作为的奋斗之路,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实现她的教育理念。可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哲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遭遇现实分裂。一方面,是主人公们顽强地存留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我确认的努力是带有乌托邦意义的,正如许上游所说:“我这才意识到,此时此刻,大讲苏霍姆林斯基多么地不合时宜。我不好反驳,也无力反驳”;[1]39另一方面,却是主体精神和价值在现实中的失落,自我体认难以为继。这种矛盾和尴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体验中表现出来:司马佳改革步履艰辛,许上游教学改革不被认可,杨运仁玩世不恭、见风使舵。现实社会以其固有的轨迹运转,20世纪末期以来,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的教育体系并不会因某个人而改变,这是中国当前不争的社会事实,这群年轻人以自我理想为目标的诗意生活难以企及。
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诗意关怀在这种矛盾中体现出来,知识分子自我确认的尴尬,源于个体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断裂,源自大学校园与社会的脱节。当这群分子群体在象牙塔之内,在形而上和理想营造的诗意生活空间中发现、确证自我的之后,他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考验:诗意存在在传统固有轨迹和时代经济生活的撞击下,脆如玻璃,不堪一击,要么回归乌托邦,选择虚幻,要么,放弃尊严,痛苦蜕变。
二、挣扎者:自我放逐的无奈
所以,我们能理解这种痛苦和挣扎,当自我的体认与社会整体价值认同达成和谐一致时,选择只有两种:回归或放逐。尽管作者坚定地站在了知识分子守望者的姿态上,但是无可否认,作为社会领域的个体存在,谁也无法逃避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化得存在状态。甚至有学者说“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精神之外构建另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2]因此,作品的主人公们,都只能在挣扎中选择自我放逐,尽管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有着许多无法企及的美好梦想,所有这些,也许都只能在宁静之时细细咀嚼。显然,对这样一个群体来说,对他们的吹毛求疵只能凸显知识分子的自卑,为他们的坚守喝彩,也对他们的放逐给予足够的尊敬,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心声。
作品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人生体验都是注脚。司马佳担任常务副校长、校长,坚持改革,从未妥协。但是,从一开始,她的改革注定是失败的,当改革并不具备所需的所有条件的时候,仅以某一个人的自我理想为力量显然并不足以推动改革的进行,尽管这种理想是进步的。教育改革失败,司马佳却因有省委组织部领导的重视,被调往州城团地位副书记,一条不错的出路。“消息传来,我们无论如何很高兴……两年来,我们的总体还是得到了肯定的。我们宅心仁厚,我们一腔热血,我们满腹才华,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们无愧于这片土地”。[1]102言语间,她仍然豪情,仍能善言,可细细品味,却又不免有许多伤感。试想当年,是什么使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什么使他们叛离传统、迂腐?作为内心的坚守者,作者不愿意直言这种自我的放逐,因为,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来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的渐行渐远,都是一种无可言说却刻骨铭心的痛。接受了政治安排,升官,司马佳在挣扎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背叛了自我。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许上游被始终没有被其所吸引,或击倒。相对于司马佳来说,他的坚守立场并无痛苦和尴尬。他关爱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可以发表诗作的学生,可正如家长们所说,高考不是考试,在全县44个平行班级里,他任教的语文成绩排在倒数第三,他注定无法再现行教育体制下生存。但是,对于政治的权术,他始终是淡然的,当被安排到穷乡僻壤去进行扫描工作时,他仅仅一笑了之,并且深感解脱:“这几年,时空的转换,使我越来越有逃离感,也越来越有新鲜感……这里陌生的一切给了我有种透亮的新鲜。”[1]111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许上游,在一定意义上传达着作者的坚守立场。在农村进行扫盲工作,仍然政治复杂,许上游却仍坚定地做回了自我。在失去爱情之后,在这里,又邂逅了美丽纯洁的村姑;在这里,他读书、写诗,一切如此惬意、自我。这与其说是对于羁绊的逃离,不如说是对于真实自我的回归,诗意栖居之中,是知识分子的寄托和慰藉。但是,这一切都在一次偶然事件之后改变了:与暴发的大学同学的见面及一次偶然的古董买卖,让他见识了金钱的魅力。鬼使神差,他走上了古董生意的道路。一切似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政治力量面前坚如磐石的许上游,在金钱中放逐了自我。自此,诗歌远逝,爱情飘渺,精神虚无,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法则逐渐消散于生意的喧嚣之中。作品中,不难读出作者对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无奈何的淡淡忧伤。
知识分子自我的剥离,这种痛苦的日常生活体验在作品中仍能使人深感痛苦和震撼,然而,却仍是关注知识分子当下生存状态的人们无可回避的话题。如果说司马佳是因政治而放逐自我、许上游因金钱而放逐自我的话,作品的另一人物杨运仁的放逐则没有任何阈限,他本来就是世俗、放逐的,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一个挣扎者,因为他从来没有坚守。他早已经对逐步步入商业社会的社会现实有所洞察,已经有了把握机会、见风使舵的生存法则,他的自我体认方式也不会有身份和道德的重负,所以,他可以游戏人生、调戏同事、玩弄学生,及至开除公职,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板,腰缠万贯。司马佳和许上游的放逐是被动的,他们心有不甘,内心积蓄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虚空和悲伤,可杨运仁的正好相反,他的放逐是主动的,他完整的自我是快意人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人格早已被主动剥离和抛弃。哪种途径才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的、诗意的生存状态呢?作者在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描述中,彰显出了十分深邃的理性思考。
作者以汤亦武和杨彩霞为形象的叙事探索了一种处于上述两种模式中中间状态的可能。汤亦武和杨彩霞大学期间便恋爱,一起支边,工作、结婚、生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既不是叛逆者也不是挣扎者,谈上为政治而背叛自我,也并没有为金钱物质诱惑而沉沦自我,一切都按社会轨迹的固有程式运行,没有痛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选择,也无焦虑和惶恐。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生存模式是社会传统和体制已经预设好的。知识分子更深刻的悲哀或许是对社会给予的预设生存模式毫无所知,或者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甚至在来不及思考是卑微地退却或勇敢挑战之时,便已经丧失了自我确认的意识和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作者对一种自我的被动放逐和主动放逐中间模式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存模式的深刻反思。
三、超越者:自我救赎的期待
从物质诉求的角度来看,主动放逐者和被动放逐者貌似殊途同归了:许上游和杨运仁都成为有钱人,司马佳也调回省城,他们都有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可对于在在骨子里固守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操守的许上游来说,自我放逐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富有,给他带来的却是莫大的空虚和内心的孤寂。在经历理想消解和自我放逐之痛苦之后,渴望冲破时代粗鄙气息的蚕茧,超越自我、社会和时代局限,回归尘封的自我,便成了他的莫大追求和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许上游显然并没有成为一个超越者,如同许上游一般,走上精神的自我救赎之路。
超越身份焦虑,回归自我,作品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商海跌爬滚打多年之后,许上游终于选择了回归。他注销了公司,停止了生意,“我成天在家睡觉,养养身,养养心吧,看看书,喝喝茶,心一天天闲适起来,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千禧年很快就到了,千禧年一道,中国社会的崭新格局就呈现出来,我经常到街上看看,感到日子过得真是优雅而美好。”[1]206知识分子终究无法逃离传统文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种闲适之中直面自我。陶东风曾指出,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处于“道德—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中,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经济要素占据社会的支配力量,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向这种社会过渡),经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俗的与物质的诉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诉求。政治、道德则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态势。于是三者关系又调整为经济—政治—道德。”[3]知识分子自我确认之难,就难在于无法容忍社会经济因素成为扼杀知识道德的魔杖。许上游亦如此。他开始在虚拟的网络寻找心灵栖息之地,显然,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上网、唱歌、洗脚、与朋友喝酒聊天还有相亲的生活,使他觉得生活乏味透顶。于是,需要一种足够自我体认的生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许上游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这样寻找的吗?”没错,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事实上,他也找到了最快适心灵的方式:爬山、阅读、品茶。于是,他又邂逅了美丽的大学生女孩瑛子,爱情一发不可收拾,如此纯洁、深情。在这里,作品展示了最原初、最淳朴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一切现实的庸俗在纯洁的自我面前都显得如此卑微、渺小,作品对于知识分子人文情感的温情关怀彰显无疑。一切从原初的自我开始,又在遭受现实诱惑的异化之后,得以本真回归。作品给了我们更多美好的期待,许上游和瑛子纯洁的爱情给了我们选择美好去向的理由。
如果说许上游的自我救赎是彻底的,司马佳的自我回归则带着些许无奈。调任州城后,平调地区旅游局副局长,后来因赏识她的省委组织部领导调任他职,她的仕途也便再无起色。于是,她来到了省城一家报社任副主编,与一位军人结婚,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假若她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假若她能有美好的政治前程,这个司马佳的人生之路也许不会有转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许上游来说,她的自我超越之路,也有些被动。当然,另外构建评判这一人物的精神尺度是多余的,因为,如同许上游一样,在绕完一个圈子之后,不论如何她都回归了自我。以致当许上游决定给他们追逐自我的起点民族中学捐款时候她欣然应允,并且还希望和许上游一起回那里执教一段时间。虽然她没有成行,但是,再苛求的读者也不会责怪这是人性的虚假。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探索,从走回原点的主人公们不依不傍的精神自律性中得以凸显。
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作品以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书写画了一个完整的圆,从原点起步,经历自我角色的剥离、放逐,再回归自我。“回到原点。我们的原点是什么?……一切美好的价值,我们的社会曾经取得共识的,后来被社会生活颠覆打倒,让我的价值观混淆。回到原点,就是要拨乱反正,回到我们确立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轨道上。”[1]309如何回到原点,也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自我确认之难所在。“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建立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精神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4]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诗性的话语形态,探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流史和自我体认之路,并为我们展示了剥离了喧嚣、浮躁、虚假的对于未来的纯净自然的美好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漂流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1] 龚鹏飞.漂流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2] 邵建.知识分子何为[J].文艺评论, 1996(3):13-19.
[3]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 1999:235.
[4] 张春歌.自我角色认同的尴尬与无奈:析2001年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J].南京社会科学, 2002(8):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