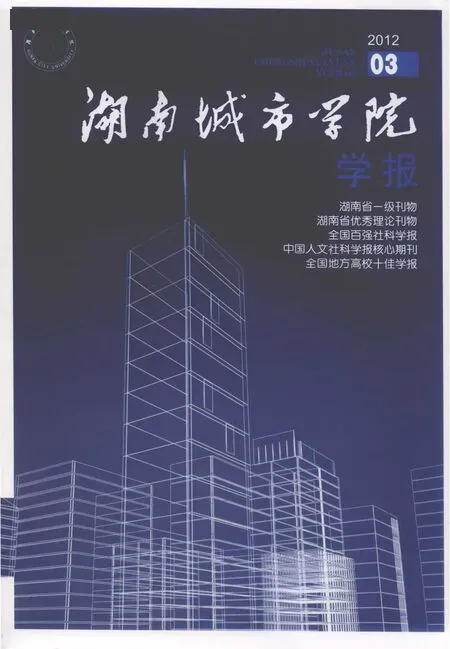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及其形成根源
2012-04-02刘亨让
刘亨让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德国人。1932年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担任中央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同年春天到达大连,1933年10月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在博古的安排下,直接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的军事活动。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由于李德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牺牲了几万红军战士,丢掉了中央根据地,因而被中央撤销了军事顾问职务,对其“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清算。李德作为红军观察员身份,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路,最后到达延安。在延安,李德参加了中央一些军事活动,担任延安军事学院的教官,从事军事理论的教学。1939年10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在那里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李德在华7年,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学术界对他的“左”倾军事路线的表现及危害,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对他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产生,形成的主观因素、客观原因、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还不够。
一
1933年10月,李德从上海一路艰辛到达中央苏区瑞金。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博古对李德予以重用,令其担任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此前,蒋介石曾以数十万兵力,发动了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当时红军只有三四万人,力量悬殊,但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充分依靠群众,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逐步扩大,红军人数增加到十万人,经济建设加快,人心稳定。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虽被机会主义者排挤在中央领导之外。但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入人心,第四次反“围剿”仍取得了胜利。
为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结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采用长驱直入、步步为营的堡垒战,调动了一百万军队到江西,蒋介石坐镇指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去组织反击,战争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李德不顾中国革命实际,实行一条“左”倾军事路线。开始实行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在敌人强大势力进攻下,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实行逃跑主义。由于李德实行以上战略战术,有利于蒋介石堡垒战开展,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军处于被动。广昌是瑞金的门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蒋介石集中七个师进攻这个城市,李德亲自指挥,彭德怀三军团担任守卫任务,根据红军的力量和广昌无险可守的实际情况,彭德怀建议按照作战原则,暂时撤离,并且预言,如果困守,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军会全军覆灭。李德不接受彭的建议,坚持“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由于广昌城无城墙,李德强迫红军修工事,筑堡垒,宣扬说“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对我最危险的道路上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2]强迫红军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这些所谓的永久工事,在敌人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下,几个小时就夷为平地,坚守在堡垒里面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红军伤亡4000多人,最后广昌失守。这就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伤亡惨重的典型战例。战后,张闻天指责说:“不该同敌人死拼”。[1]79彭德怀不满地说:李德完全不懂红军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1]74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势力发生变化,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我们保卫中央苏区。当时,蔡廷楷、蒋光鼐领导的 19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引起蒋介石的恐慌,立即从江西调军队去镇压,这本给红军一个联合反蒋的好机会,可是李德却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未派兵支援,坐失良机,蒋介石在击败19路军后,回过头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由于王明、李德违反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实行错误军事指挥,以致革命战争失利,中央根据地丢失,红军被迫突围,开始长征。事前,未进行战争动员,广大指战员不知道战略意图。未精简机构,把各种文件、印刷机、印钞机、坛坛罐罐,什么都带走,一路拥挤不堪,行军困难。见此情景,彭德怀很气愤:“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1]79长征路上,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处处挨打。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险阻,英勇顽强战斗,好不容易突破了蒋军的三道防线,但为此,付出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特别是渡湘江时,国民党聚集了几十万军队,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在湘江之侧,李德一筹莫展,我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李德只是命令红军硬打硬拼,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渡湘江,损失惨重,8万人从中央苏区出发,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渡湘江后,红军向何处去,李德主张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企图解除压力,可蒋介石早知红军意图,在那里布置了几十万军队,正装开口袋等待红军来钻。根据形势,毛泽东等坚决反对去湘西,主张到敌人的薄弱地区贵阳,李德不同意,后来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说服下,经过几次会议的争论,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红军进军贵阳,从而挽救了红军。
二
李德作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军事顾问,抛弃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拒绝接受几次反“围剿”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顽固地推行一条教条式的军事路线。其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主观因素
1.李德的出身历史和社会背景是错误路线形成的关键。李德出生于20世纪初的德国慕尼黑,年轻时应征入伍,当一名列兵,积极参加左翼社会主义者,以后参加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巴伐利亚的街垒战,也参加了创建巴伐利亚共和国和德国的工人起义,后来被捕入狱,越狱后逃到苏联,参加苏联红军,担任师参谋长。后来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303-304从以上经历可看出:其一,他参加过多次街垒战,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熟悉街垒战。其二,他出生于慕尼黑,这是德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人运动活跃,他参加过工人起义和世界大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其三,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3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军事理论,深受德国教官军事理论的影响。以上经历说明:李德熟悉阵地战、堡垒战,熟悉西方军事理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可是对中国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根本不了解、不熟悉,对中国国情不了解,所以他推行西方的阵地战、街垒战“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就十分自然。这是内在因素决定的。
2.个性自负,听不得不同意见,是他犯错误的另一重要原因。如上所述,他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又参加过战争,这本来有利于指挥作战。即使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红军,只要虚心学习,听取不同意见,还是可以弥补的。关键是他背上了思想包袱,自命不凡,看不起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认为他们是土包子,是“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1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战役前后,或一些重要会议上,或个别交流时,对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多次提出过严肃批评,也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议。李德的态度一般是拒绝,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反而给你扣一顶“游击主义”、“逃跑分子”帽子,让你不敢动弹。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主张集兵力于一方向,其他方向则布置牵制力量,也被李德否定了。1933年10月在一次研究如何粉碎蒋的“围剿”的会上,毛泽东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主张放弃黎川,诱敌深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307李德拒不接受这一正确主张,他们震惊于黎川一城的丧失,认为失去黎川等于打开苏区北门的门户,必须夺回。死守黎川,付出惨重的代价,黎川还是失守了。1934年5月,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重新审查而举行的会议上,李德受到一些与会者的激烈批评,张闻天指责“不该同敌人死拼”。[1]317李德在会上不但不接受意见,不检查自己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几次发言为自己辩护,把一系列战役的失败、大量城市的失守、战士伤亡的原因归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难怪他自命不凡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正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3]
3.缺乏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国情,迷信书本是他执行左倾军事路线重要原因。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交通不发达,生产落后,国民党兵力集中在城市,农村薄弱,中共的根据地分布在边远不发达地区,为白区分割,形势复杂。李德于 1933年 10月才到瑞金,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的特点,不了解苏区形势,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搬到我国,搬到苏区,瞎指挥。毛泽东认为: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域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1]292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既要走路又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路、还是河道,只知道战略图上一画,就限定时间打,很多时候是脱离实际的,毛泽东批评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的,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客观原因
1.王明、博古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提供了土壤,博古的拔高使用,为李德提供了舞台。李德来华是王明、博古要求共产国际派来的,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被排挤在军事领导之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处在顶峰时期,中国大地为“左”倾思想所笼罩。李德与他们的思想相通,臭味相同。王明、博古支持、赞许、推崇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他们配合默契,使李德的错误路线系统化、合法化,助长了它的发展,成为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生存的沃土。王明、博古掌握着中央的军政大权,但他们都年轻,长征时博古只有26岁,既不懂军事,又无经验,更无威望。王明、博古,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李德,赋予其制定军事战略战术,以及红军训练、后勤等工作。在博古支持、纵容下,李德掌握了中央军事大权,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压制不同意见,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太上皇”,为所欲为,动辄训人、处分人。上自司令员,下到一般工作人员,李德无理训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白在苏联学习几年,还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面对敌人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红军闽赣司令员肖劲光为保存有生力量,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撤出了阵地,李德骂他“退却逃跑”,要判他5年刑,还企图枪杀他。[4]48由于毛泽东死命相保,判决才未执行。王明、博古重用李德起了很坏的作用,培养了一些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卫士,成为他们的忠实代言人,进一步取得全党全军统治地位;借洋人压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打击陷害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优秀干部,挫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扫清障碍;助长了李德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极端恶劣作风。王明、博古和李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全面推行“左”倾军事路线,牢牢掌握控制中央的军事大权。伍修权深刻指出:“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大权力交给了他。”李德“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1]292
2.共产国际的威望与支持,中央政治局对军事工作领导不力,有利于“左”倾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央领导人选、重要方针政策、重大行动计划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如临时中央要迁到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从瑞金突围,都是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实施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人们都很尊重他,他制定的军事活动计划、战略战术方针一般都能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军委的批准,给他开绿灯。特别是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纪,是中国在共产国际唯一获得高位的代表。这样显赫的人物,为李德提供了保护伞,王明在共产国际,李德在中央,遥相呼应,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实行违背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错误军事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连连失利。1934年2月14日,聂荣臻等署名向军委提出“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军委未接受,复电称:“必须坚决执行李德那一套打法”,[1]278否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支持了李德的堡垒战、“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压制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战略战术方针。
综上所述,李德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王明、博古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他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批准了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负有重大责任。但责任不能由他个人承担,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人身上。首先是XX同志与华夫同志,把李德同志安排到不适当的地位,超出了军事顾问的职权范围。[1]313也超出了共产国际规定的责权范围,这是中央领导要负责的。周恩来严予律己,他谦虚地说:“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政治局认为:“书纪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责,因为有关重要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书记处批准的。”[1]16虽然政治局担了担子,但李德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李德应负重要责任。
李德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危害极大,但对他不能全盘否定,还属于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好心办了坏事,仍属于革命同志犯错误的问题。在他被撤职受到批判后,仍然服从中央安排,在那么恶劣条件下,仍坚持走完长征路,这种不怕艰苦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走完长征的外国人,只有他1人。到达延安后,担任延安军事学校的教学工作,平易近人,讲课联系实际,为培养军事后备人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6年5月,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在延安访问李德,他羞羞答答地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的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5]247这是李德第一次比较含蓄比较真诚地表明一种认错态度,也是一件好事,历史是最好的教师。
[1] 石志天, 周文琪.李德与中国革命[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1987:20.
[2]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1980:62-63.
[3] 张定, 严如平.胡耀邦传:卷1(1915-1976)[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5.
[4] 于俊道.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5]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回延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