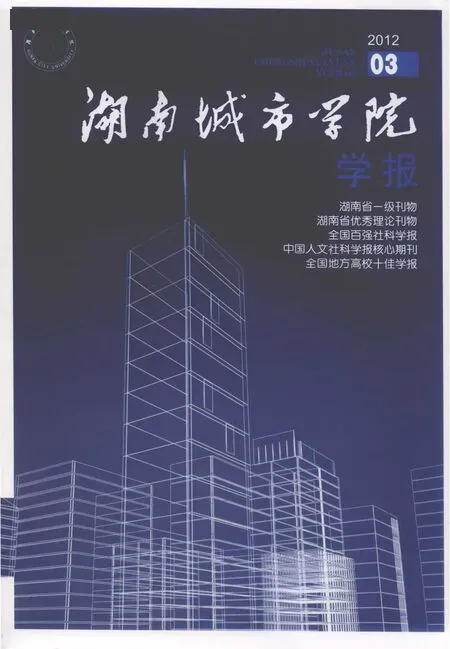从湖南《大公报》看民初长沙拆城事件
2012-04-02庞毅
庞 毅
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拆城运动,长沙也在其中。拆除古城墙是长沙现代市政建设的第一步。长沙拆城,从1917年3月“开始拆毁城墙”,[1]到1923年5月“各方城墙将近拆完”,[2]历时 6年之久。作为民初全国拆城运动的一部分,长沙拆城事件研究相对较少。在已有关于研究长沙的论著中,对此也多是一笔带过,未见有展开探讨者。本文通过当时湖南《大公报》各个时期的报道,考察主张拆城与反对拆城的各种理由,以及拆城前后各方对城砖处理的种种要求,试图反映长沙拆城事件的过程,并对拆城事件背后各方势力的角逐做一简要探讨。
一、拆与不拆之争
关于长沙城墙是否应该被拆除,较早就开始了讨论。光绪末年,湖南咨议局就议论过是否拆除长沙古城墙。[3]民国五年(1916)左右,各界已纷纷议论是否应该拆城。“自民国五年秋,议拆城垣”,[4]“拆城之说,湘人筹议甚久”。[5]最终决定,“关于拆城一案,前经省议会开会讨论者颇多,当经公决以拆城,既成事实,反对无效”。[6]厘清主张拆城与反对拆城的各种理由,有助于揭开长沙拆城事件的第一道面纱。
关于主张拆城的理由,主要从“以利交通,并为改良市政,开辟商场”等方面说明拆毁城墙的必要性。[7]一方面是扩大市场的需要。城垣使“市之范围遂亦以城郭为限”,而“迨及近世,人烟稠密,工商发达,市域之扩张有日新月异之势”,加之商埠的开辟,市区范围扩大已成事实,为顺应世界之潮流,“若仍以旧有及前定之界为限,将来不敷展布,且无以竟市政之宏观”,所以“今之扩充至数倍以上”。另一方面则是便利交通。“铲平城垣”,以达到“除障碍而利交通”的目的。[8]另外,方便商业也是拆城的理由之一。“石头城墙受不起几个开花炮,并且高高低低,湾湾曲曲,商业上交通上诸多碍事,所以谭组安作省长时候,省议会慨然议决将城墙拆了”。[9]
至于反对拆城的理由,主要从城墙涉及水灾兵防、傍城起屋者,拆城会危及附近古坟等方面,而表示异议。王寿慈等人认为“拆城案以与水灾兵防大有妨碍”,[10]拆城还会造成附郭居民傍城起屋者无家可归。另外,“沿途一带古塚甚多”,[11]拆城必然会危及古坟。
对于反对拆城的声音,主管拆城的督军署对其一一进行了驳斥。针对城墙防水一说,认为“湘城淹水系由御沟灌入城垣,并无堤防作用,水灾一项不成问题”,对于兵防,则认为“现时军械日精,非咸同时代可比,作战设防具有一定之区域,与有无城垣无关。瞪之东西各国与广东之拆城事实即可知其有利无害云”。[10]数天之后,又进一步说明傍城起屋的不合法性,“预防水患各条亦仅限于城内一隅之见,无辩明之价值,至附郭居民傍城起屋,本非法律所许,自不能顾此少数居民之便利,城墙之设,当日原为国家军事财产之一部分,不便以国家财产移作地方经费之用”。[12]
如何看待主张拆城和反对拆城双方的理由?首先看反对拆城一方。反对拆城的王寿慈等人通过省议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省议会转据公民王寿慈等对于拆城一事具书请愿,提议并抄送请愿书一纸到署,准此查拆城一事”。[12]从其反对拆城的理由来看,首先是他们认为城墙是长沙水灾兵防的一道防线。结合长沙历史来看,这点考虑不无道理。长沙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饱经战火;同时,长沙水灾频发,城墙有堤防的作用。再看主张拆城一方。督军署对于王寿慈等人的异议进行了回复,从答复内容上看,对于水灾兵防一说,以其作用不大而批驳。但对于傍城起屋者,用“非法律所许,自不能顾此少数居民之便利”,显得有些强词夺理。从后来《大公报》关于傍城起屋者的报道来看,其人数不在少数。“因开辟商埠以及实行拆减沿城所居,小民令饬迁移者约计七千余户”,虽然这七千余户不尽然都是附郭傍城起屋者,但在长沙开埠13年后提出此事,显然他们在其中占了较大比例,“约计数千户之多”。[13]后来市政讨论会筹建勤民区,有弥补附郭傍城住户的作用,但始终未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最后,以“近城房屋,或因有碍马路路线,或因妨碍平城工程”,[14]而强制拆除。对于城墙附近的坟冢作了如下处理:一是“择定陆军义山为安厝古骸之处所”;二是由“本处雇工起迁用□,检骨装置完全妥为安厝,或予若孙,或亲故友朋,择有相当□点”;三是“自愿迁移者,亦听其便,但不得稍涉稽延,致滋障碍”。[15]相对傍城起屋居民的处理要合情一些。
纵观长沙拆城事件的始末,由于长沙市政建设起初并未有具体的规划,即便1921年《长沙市政计划书》出台,也较为粗略,这是主张拆城与反对拆城双方分歧的关键,也是造成后面对于城砖用途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二、拆城各方利益的诉求
在确定拆城之后,对城砖如何处理成为各方讨论的中心。“据商会某君之估计”,当时城砖“可值湘银二百数十余万”,[16]面对如此丰厚的财富,城砖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大公报》来看,首先是商会对城砖用途提出了看法。“昨商会会长左君,拟呈请督军将此项砖石□行变价发卖,约可获现银六七十万金。一俟完全拆净,将环城基址修筑一电车路,即以此项砖石为建筑费”,“此路告成,则沿路内外,必成繁盛商场”。[17]
《大公报》记者对商会的建议给予了声援,并认为应该规定城砖的用途,兴办公益事业。“湘省拆城闻不日即将实行而其对于砖石之用途。尚未确定,窃□卖与商民必可售得钜□。据商会某君之估计,可值湘银二百数十余万,当此财政困难之际,此项财产自应妥为□存,将来□论拨办何种公益事业,必能取得确实效果。倘任其散漫无稽,随意拨用,则各处援例而起,不仅难于应付,而用之何能确得其当。闻长沙商会会长有请拨修环城电车之说,记者以为此种建议用意至善,当道果能采纳,较之不定用途,任意取携者,则获益多多矣”。[16]
面对各种对城砖用途的意见,督军署最后授权营产经理处管理城砖,并部分用作拆城的经费。“省城城墙砖石,前经呈请,定由该处保管价卖,以充拆城经费,无论何项机关不得拨用,业奉督军指令照准在案准咨”。[18]虽然如此,但接下来仍有对城砖用途提出不同意见者。建筑新仓工程处:“建筑新仓工程处委员刘光萃等,请就大西门迤南迤北一带拆取城砖,如须津贴即请酌暂行垫给,随时函示,容当照数拨还归垫营产经理处……前因该新仓工程处需用城砖,自应缴价购买,以符定案。惟事关公用与私人购买不同,兹经从廉酌定,每砖一口收价钱三十文,即由该工程处照数备价,呈缴财政厅转送该处查收,以济要需。”[18]虽然其没有如愿以偿,但按三十文每砖的价钱也不无所得。长沙学董就没有获得如此照顾。“长沙城学董朱剑凡,日昨具呈督军署,拟请拨给城砖以备修造校舍之用,当奉督军公署批示呈悉,现在拆卸环城垛口之砖已拨归陆军工厂及陆军医院之用,尚虞不给。城立国民小学,原就各公庙改设已历有年,虽不免因陋就简之嫌,亦实收事半功倍之效,似不必更张以亏学□。该学董热心教务,素富经验,当不河汉斯言也”。[19]
在各种各样对城砖用途的意见充斥之时,营产经理处将城砖除部分用作拆城经费(包括拆城、迁坟等费)外,主要是变卖“充公”。“据营产经理处处长马吉苻呈称,窃查职处所管各号城砖及麻石、半截砖、碎砖等项,均经呈奉钧署,批准定价,变卖以裕收入,凡各机关及商民取用购买者,概应填给运单,以资稽查,而杜弊混”。[20]但如何分配这项收入不得而知。在拆城的近三年后,仍有对城砖用途提出的申请,新修湘春门关岳庙的负责人便想拨用附近城砖。“北区湘春门之外城门紧接新建关岳庙地段。现该庙正殿落成,四面房殿正在赶建。该外城门砖石既可拨用,且不便于动工,该监修关岳庙委员李春林,呈准当局,将该湘春门外城门一律拆毁,以期两便,年□已实行动工矣”。[21]
从拆城之前,到开始拆城后的第三年,各种对城砖用途的要求层出不穷。城砖即意味着资金,各方的种种要求或多或少都是出于为自身利益考虑。商会建议修筑环城电车路,便利的交通无疑有利于长沙商业的繁荣,而商人从中获益最为直接。建筑新仓工程处、学董以及“关岳庙”等就更加明显。《大公报》记者建议,规定城砖用途,而不要随意取用实为妥当,城砖变卖所得应当用于公益事业,但对于如何规定,用于什么公益事业等没有具体说明。城砖似为公物,建筑新仓工程处本是政府机构,建筑新仓也是政府行为,但“以公济公”仍没有得到首肯,而是变通为廉价出售。从既定规定出发办事,无可厚非,但后面长沙城学董要求拨用城砖,告知以拨给“陆军工厂及陆军医院之用”,则不得不让人怀疑此规定的有效性。近三年后新修关岳庙要求拨用该处城砖,虽然未见是否批准,但推测可知很可能有类似援例可循,所以监修关岳庙人员才会如此行事。由此看来,对城砖如何处理始终没有具体的公文,以致于造成各种意见充斥。
三、拆城事件反思
无论是主张拆城、反对拆城者,还是拆城前后对城砖用途提出不同意见者,他们的背后都代表着各自阶层的利益诉求。主要来说,拆城事件反映了以督军署为首的官方与以商会、学董、“关岳庙”等为代表的民众间的分歧。在反拆城中,站在前列的是平民王寿慈等人,在涉及城砖处理中,商会、学董、“关岳庙”等则直接与官方展开了交涉。拆城直接危及以普通民众为主的附郭居民,为捍卫自身权益,他们诉诸于省议会,而商会、学董、“关岳庙”等主要是想从城砖中分一杯羹。由于没有对市政建设做具体的规划,各方利益争端未能很好解决。
拆城事件反映出督军署的强势与省议会的无力。无论是在处理拆城与否,还是针对城砖如何利用中,都是由督军署决定的。在城砖处理的过程中,将“环城垛口之砖已拨归陆军工厂及陆军医院之用”,也很有可能与督军署有关。在拆城事件中,省议会为民发言,“省议会前据人民请愿提议拆城一案并无结果,兹据北京快函谓谭省长电达政府,详陈□省议会议决”,[7]“省议会对于拆城案以与水灾兵防大有妨碍,特诘问省长”。[10]但显然,省议会并无实权,除把人民请愿呈报省长、督军外,并没有发挥其他作用。
同时,拆城事件也折射出当时湖南督军的大权在握。拆城本属于市政建设范畴,当属行政事务,归省长管辖,但面对议会质疑时,“省长因属军事范围,故移送督署办理在案”。[10]而在反驳反对拆城的意见时,督军署以城墙已无防御功能为由,显然二者互相矛盾。联系当时湖南的社会情况,战火不断,由掌管军事的督军决定,也不难理解。这也是长沙市政建设未能很好规划、省议会无权的现实因素。
在分析与拆城事件有关的各方势力时,以《大公报》为主的舆论力量不可忽视。拆城事件的前前后后,《大公报》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让社会知道了事情的发展动态,对各方提出的要求,对督军署等官方的回应、行动展开报道与评论,这本身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可以说,在长沙拆城事件中,《大公报》在公共舆论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田伏隆.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187.
[2] 西城城基竟出卖耶[N].大公报, 1923-05-14(6).
[3] 黄纲正, 周英, 周翰陶.湘城沧桑之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174.
[4] 吴晦华.长沙一览[M].长沙:开成印刷公司, 1925:4.
[5] 省城实行拆毁城墙[N].大公报, 1917-03-12(7).
[6] 省长不负拆城责任[N].大公报, 1917-05-05(7).
[7] 省议会果已议决拆城耶[N].大公报, 1917-05-03(7).
[8] 长沙市政公所.长沙市政计划书[R].长沙:湖南图书馆藏, 1921:9.
[9] 蒔竹.省城古迹今释(一)[N].大公报, 1925-11-05(9).
[10] 省长答复省议会拆城理由[N].大公报,1917-05-14(7).
[11] 近城坟墓勒令迁移[N].大公报, 1917-05-24(7).
[12] 督军答复拆城理由及城砖所属[N].大公报, 1917-05-18(7).
[13] 市政讨论会筹建勤民区房屋[N].大公报, 1917-08-16(7).
[14] 市政公所强制拆除近城房屋[N].大公报, 1922-09-14(7).
[15] 近城坟墓勒令迁移[N].大公报, 1917-05-24(7).
[16] 静公.处置城垣砖石之末议[N].大公报, 1917-04-05(7).
[17] 拆城改造电车路之建议[N].大公报, 1917-04-01(7).
[18] 拆取城砖建筑新仓[N].大公报, 1917-04-10(7).
[19] 城砖已定用途[N].大公报, 1917-04-16(7).
[20] 规定变卖城砖办法[N].大公报, 1919-03-16(6).
[21] 湘春门外城拆毁[N].大公报, 1920-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