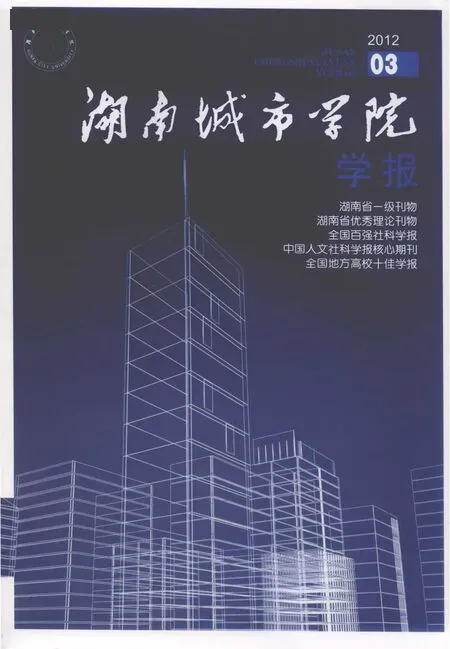中国传统建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2012-04-02胡勤
胡 勤
中国传统建筑注重地域的空间与时间环境,南方北方、各个朝代的建筑风格都略有不同,但是中国传统建筑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伦理文化,传统建筑的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高度统一,表现出了鲜明的传承特点。对于建筑物质材料的不同选择,环境的制约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成为最为重要的选择。但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乏石头这一天然材料,那又为何中国的木构建筑却传承了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呢?在原始社会可以说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了对石头的开采和利用,那么到了文明开化的时代,为何仍然坚持着以土木为材,木构结构呢?这与中国传统建筑伦理思想的“恋土”倾向、“恋木”情结、中正和谐之审美和建筑之术的道德制裁等特色紧密相联。
一、土木之功——生命轮回之观念
梁思成认为,中国传统建筑以土和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有茂密的森林,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而黄土的本质又是适宜于用多种方法(包括经过挖掘的天然土质、晒坯、版筑以及后来烧制的砖、瓦等)建造房屋。”[1]并特别指出“这两种材料之掺合运用对于中国建筑在材料、技术、形式传统之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1]梁思成这一对中国传统建筑材料渊源的深刻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也有一些学者另辟溪径,如学者王振复就从文化成因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结构的建筑特色,他认为这“是出于中华原始初民由原始植取向物采集发展而来的原始植物种植的生产方式,是源于这一原始生产方式的关于大地与植物的生命意识。”[2]这种理解紧紧抓住了中华民族繁衍不息的生命脉搏,具有更大范围的包容性和超越性。所以,中国传统建筑土木结合的建筑方式是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审美取向、伦理政治意识和宗族伦理观念相符的。
(一)“恋土”倾向
《易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朱熹注:“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厚德”即地之德,“顺”是它的根本点。“地势坤”即“地至顺”,即合乎规律而动。这就是古代“坤厚载物”的大地伦理学。这也是中国传统崇天尊地思想的历史来源。《周易》不吝词藻的颂扬了大地作为始祖的巨大贡献与崇高道德,称其为“德合无疆”、“至哉坤元”。如《周易》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也,故日致役乎坤” 颂扬大地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以“万物资生”颂扬大地养育万物的伟大贡献;以“含弘广大,品物咸亨”,“至静而德方’颂扬大地自敛含蓄的修养;以“乃顺承天”,“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歌颂地安于“天”之辅位,克尽妻道臣道的高贵品德。纵观人类历史,对于大地伦理品格的这种歌颂与描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极为少有的。中国这种“坤厚载物”的传统大地伦理观念为现代伦理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
中国传统建筑的雏形源于土与水文化。“土”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水”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象征“土”文化的建筑主要是指穴居式建筑,而象征“水”文化的建筑主要是指干阑式建筑。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具有这两者特点的早期建筑雏形出现了,二者的不断融合开启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之河,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建筑采用土木营构最原初的理由,应是农耕文化下带来的对土地和谷物的崇拜,最典型的就是各地都不乏土地庙,供奉着土地神。作为国家形态,江山社稷是封建帝王的全部依赖,同样,对于平民百姓,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土地和植物就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土地滋润万物生长,春华秋实,夏荣冬枯,绵绵不绝,富有生气和活力,这是华夏民族对土壤孕育出的绿色生命的珍爱意识。这种对土地和植物生命的感悟,逐渐演变成原初先民对山川日月、大地草木等各种自然现象的崇拜意识。古人从这种崇拜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易经·否卦》中记载“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达的就是原始先民将族群的存亡寄托于桑树之荣枯的意识。由此,木材作为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也是原始先民对植物敬畏和崇拜的一种意识的折射。
在古人观念中,土地滋养了万物,虽然她没有生命,但却是生命的来源之本,“他们把一切存在物和客体形态,一切现象都看成是渗透了一种不间断的、与他们在自己身上意识到的那种意志力相像的共同生命……这样一来,一切东西都是与人联系着和彼此联系着的了。”[3]因此,《周易》所谓“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范也。”这种对生命力的尊崇,是中国传统建筑长期进行土木营构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恋土”倾向的一个大地伦理表象。
(二)“恋木”情结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宫殿是传统建筑在形式上、美观上、及工程技术的作法上的典型代表,其始终坚持使用的就是木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来亲近人性、接近自然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贯穿着一个精神,即”人不能离开自然”。[4]
首先,这种坚持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恋木”情结,反映了一种浓厚的农业文化特色。中国自古是土地文化,因木生于土,木与大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建筑匠人主要是指木匠而不是石匠、泥匠、瓦匠。所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行业中,从事木匠行当的人数相当庞大,加之土、木建筑材料的获得相对而言少付出人力物力,且在安排建造的时间、房屋的规模与形制等方面不受限制,就使得方便、灵活、经济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
其次,木材物理属性上的优点为古人的“恋木”情结提供了合理的物质基础。与其他建筑材料相比,木材的弹张性、柔韧性和温和性等物理属性特别突出。所以,中国传统建筑充分利用木材的这些特性,建筑多以木结构为立体构架,由各种梁、柱、檐、椽等构件组成,体现出了在构架拼装等结构方面的优点。木温润的特性与石材的冷冰冰不同,树木复苏能给人以人在自然之中的自由感。所以在审美上,传统建筑中大量木材的使用令建筑形象质感熟软、朴素而自然,充分体同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满足了中华民族崇尚优美的审美情趣。
再次,“远于宗教,近于伦理”是中国古人“恋木”情结的文化成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代宗教是其重要表征之一。中国古代的宫殿、坛庙、宗祠、民居等建筑类型深受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梁漱溟曾指出:“社会秩序之建立,在世界各方一般地说无不从宗教迷信崇拜上开端,中国似乎亦难有例外。但中国人却是世界上唯一淡于宗教,远于宗教,可称‘非宗教的民族’。”[5]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史上,建筑是兼具实用性的功能和伦理教化的功能的。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所论断:“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表征也。”伦理融于建筑和建筑表征伦理,建筑伦理化了,伦理也建筑化了。“远于宗教,近于伦理”的观念在儒家那里就是不信鬼神,而注重人的生命本身,如儒家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等等。道家的正宗也不讲鬼神,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就表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本质,所以应顺其自然,不人为强求,不寄托神灵。因此,中国古代建造的多是宗祠,而不是代表神灵的石筑庙宇和墓塔。
这种对神的“淡泊”在中国传统建筑上明白的表现出来。对此,梁思成分析得非常透彻:“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建筑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6]中国古人从来不把建筑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建筑不必用经久耐用的石材来建造,木料才是最合适的。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来“恋木”的一个文化理由。李约瑟对此曾评说到:“为什么要试图支配后世呢?中国最大的园艺作家计无否说:人造之物诚能保存千年,但人在百年之后谁能生存。创造怡情悦性幽静舒适之境地,卜屋而居,此亦足矣。”[4]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从不依赖物质来追求永恒的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建筑观是不奉神的,只把人的居住放在首位,建筑物所代表的历史与精神才是传之后世的东西。这就是已深入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恋土”倾向、“恋木”情结。所以,在中国传统建筑观中,建筑人对自身非凡创造力的一种欣赏,成为人生当下生存的精神家园。
总之,在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和观念的、审美的等诸多因素中,千百年来深藏于现世生命意识之后的“恋土”与“恋木”情结,是使土木营构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主角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营构,是古代农业文明和生命意识的共同选择。
二、轮廓规制——中正和谐之审美
《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中庸”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古人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正是出于对“中庸”的尊崇,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把最重要的建筑摆在中间,次之建筑环绕两侧。因此,中国的建筑物大多有明析的南北中轴线,齐整的东西对称,形成“中正和谐”之美。这种中正和谐的格局强调的是“中和之美”,是天人和谐之美,具体表现为阴阳乾坤各在其位从而万物生长繁育。更是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等级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和谐之美。所以,甚至于在许多传统建筑物的名称中就包涵 “中”、“和”之字。这些字眼都表现着中国传统建筑观念中的中正和谐之审美倾向。
中国传统建筑基本上是在一个广阔的地面来铺展规划,显得大气而磅薄。这与皇帝坐镇中央统治四方有种内在的联系。周代王城便采用的是“井”字形的格局,宫城位于“井”字的中央。中是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位的交点,是最尊贵的方位。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中商”的记载,表示都城的尊贵地位。《管子·度地篇》也说“天子中而处”,而《吕氏春秋》明确指出“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荀子·大略篇》 则有“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些都说明了“中”这个方位对于帝王的重要意义。所以,王城建设中,宫城是天子所居之所,应位于城市的中央。皇帝的宝座要位于宫殿的中央,这些观念都在建设中得到体现。宫殿中的大朝、佛寺中的大雄殿、四合院中的正房都是居中而建。而单体建筑的当中间(明间)在尺度上都比其他开间要宽。如北京紫禁城太和殿,面阔为九间(不包括两侧廊道),进深为五间,皇帝的宝座在纵横轴线的交叉位置,意喻帝王“九五之尊”、飞龙在天。五是阳数(一、三、五、七、九)的中间数字,具有“中”的特殊意义。太和殿是故宫的中心,周围是庞大的建筑群,外围以天坛、社稷坛、日坛、月坛等拱卫。宫殿建筑是帝国形态的象征。民居也严格地体现着封建家族伦理秩序――家长住上房堂屋,子孙住厢房偏厦。所以,宫殿建筑中蕴含的等级体系与社会思想文化准则完全渗透在了中国古代各类建筑中。礼制同样强调方位,房屋的方位、尊长的坐位都是极度讲究的,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之说对后世帝王影响巨大,所以“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礼记·曲礼下》)为什么必须坐北面南,似乎没有什么说明。不过,孔子所说的“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则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样,民居中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父母或祖父母都必须居于北堂,因为这具有儿孙绕膝的象征意义。这样,坐位便不仅仅一般意义上的象征,而是“天之制”的体现了。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辨人在》所言:“贵者居阳只所盛,贱者当阳之所衰。……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面南,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礼之尚右,非尚阴也,敬老阳而尊成功也。”
在中国古代城市、宫室建筑布局规划中,有一大特点,即有一条中轴线,鲜有体现中轴观念以外的模式。这种规划的具体纲领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天”(《考工记·匠人》)这正是“中立而不倚”的中正和谐观念在传统建筑中的根本体现。由此中轴线路四向相交所构成的网络与直线型的道路,体现着一个严密的政治、伦理模式。这种中轴线模式,多层级纵深,两旁有附属性建筑左右对称摆放,中轴线上的宫室雄伟巍峨、神圣威严、令人仰视,体现着中国政治伦理文化体系中的君臣之序、尊卑长幼,这里有中庸、稳定、内敛与和谐的内在特质。
由此,体现“中正和谐”之美的中轴对称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宫殿、坛庙,还是寺院、民居,中轴对称的特征都非常一致。《周礼·考工记》描述了周王城九里见方、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格局。现存的古都长安(今西安)、北京都是遵守了这样的格局。长安城建于隋代,城市格局十分规整。城市轮廓为方形,宫城居于城市中轴线的北端,“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皆出自《周礼》。平民的居住区采取“坊里制”,与宫城严格地区分开。北京城是明代在元代大内旧址上修建的。宫城(紫禁城)居于内城中心偏南,它的正面东(左)、西(右)两侧布置着太庙和社稷坛,背后是出于风水观念而堆筑的景山。
基于社会制度与建筑类型的同构对应,主从有序的四合院建筑作为主要建筑类型反映的就是“中正和谐”的特点。中国古代其他的一些传统建筑,如宫殿、宗庙、衙署等可视为扩大化的四合院建筑的同构体。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庭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君仁、臣忠、民顺的社会关系影射于家庭建立起了父慈、妇从、子孝的关系,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管理、控制作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四合院就是家庭这种社会稳定器的物质化的延伸。因为四合院不仅具备了居住功能,而且以其主从有序的空间布局,满足了长幼尊卑的政治功能。“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7]就这样,政治组织结构和建筑型制相辅相成,相互地影响和强化,使得中国传统建筑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代相传而无衰竭之迹。
三、建筑之术——道德观念之制裁
建筑在中国古代作为术是一种活动,在我国素称匠学,从事建筑工作的人称之为匠人,通常是社会中下层的人,而非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匠人由于无法注书,口口相传,所以各家匠法不免分歧。为规范建筑活动,从宋代开始,匠学开始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和封建道德观念制裁。所有建筑活动被做出严格的用工用料规定,并形成制度。建筑营造是人为规划、由图纸到施工的有目的的活动。不同时代的建筑理念、建筑文化和建筑者的个体修养等无疑会影响和制约着建筑营造活动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物质载体则不可避免地映射着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或者个人观念的痕迹。
中国传统建筑和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同步发端与发展的,并有着极稳定的系统。中国人一贯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对于建筑是持传统主义和反对改革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古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恪守祖制、尊重祖宗的思想映射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上,就是遵守先前的建筑观念、建筑形式、结构技术和用材取向。所以从秦到清代的两千余年中,我国传统建筑在建筑形式上以台基、柱子加斗拱和大屋顶为主的基本造型从未改变,在平面组合上则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铺展,形成层层相套的院落。与西方建筑史上风格的多变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形成鲜明的对比。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院落式的建筑群,展现广阔空。从两千多年前汉墓砖画上所刻画的院落建筑,及至明清最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都采用的复杂的围合形式。又如,唐代各种斗栱样式已经定型,宋代有了完备的规制,从最简单的不出跳的“把头交颈造”及出一跳的“斗口跳”;最大可以出五跳,达到八铺作的硕大斗栱,再加上昂和上昂的配合,几乎重要的斗栱都出现了。
建筑的营造活动参杂着人的审美意象,同时也交织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反应历史背景,再由建筑这样一个载体,重现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观念中,“士、农、工、商”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从事“匠”这一行业的人的地位。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是“学而优则仕”,而工匠就算技术学到炉火纯青也还是下层的体力劳动者。此外,中国古代建筑匠师和工官制度密切相关。《考工记》称主管建筑工程的官吏为匠人。汉唐称将作大匠,如汉代阳城延,北魏李冲、蒋少游,隋代宇文恺,唐代阎立德等都是著名的将作大匠。宋称将作监、如著名的《营造法式》就是由宋将作监李诫所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名的匠作大师并非现代社会所讲的是建筑类专业出身。他们大多是因为从事工匠久了以后,或是熟能生巧、或是善于钻研、或是久而精通,才胜任职事的。而且中国古代这些著名匠作大师,大多没详细的历史记载,如被后世奉为祖师的鲁班只见于传说,与鲁班自古并称的王尔,所载事迹也是聊聊无几,著名的安济桥的设计者隋匠李春,其原始传记材料基本失传,历代能工巧匠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就更多了。
封建社会这种人才认同制度使得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和风格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了几千年一以贯之的稳定结构。封建社会,建筑之术中“传承”成了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一点,使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总结和理论建设严重滞后于欧美国家。中国关于传统建筑方面的书籍主要有《考工记》、《木经》、元代《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中国古代各王朝制定的建筑法规一类的官书。除了官书,还有一些私人著作,如现已失传的北宋喻皓的建筑学专著《木经》3卷。明中叶南方民间匠师所著的《鲁班营造正式》,万历(1573~1620)时出现的《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明未文震亨的《长物志》,明未计成的造园学专著《园冶》等。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书籍都着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记述,理论升华和探索仍较缺。因此,传统建筑作为一门术,主要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传承,这种方式使匠人之间缺乏技术交流,觉察不到自身的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其狭隘性与局限性显而易见。建筑人才包括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在那个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里都不高,他们没有资格和机会去实现自的创意与想法,没有独立人格尊严,只能惟命是从。作为师傅的往往还要留一手,以防徒弟超越自已,这种保守狭隘的思想不仅教不出好的徒弟,更重要的是使得许多精湛的技艺失传。在这种传统保守的环境下,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实现更新与超越,而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无关痛痒的改进与提高。
总之,中国传统建筑伦理思想来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体现出来的“恋土”倾向、“恋木”情结、中正和谐等基本特点则主要来源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易理与儒释道思想。
[1] 梁思成.建筑历史与理论[M]//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2] 王振复.中华建筑的文化历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M].丁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 4[M].汪受琪, 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5]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6]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