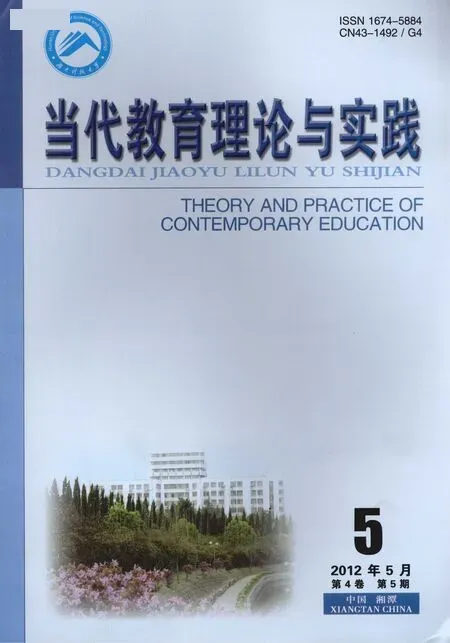以网络民意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思考
2012-04-02谢雄军
谢雄军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以网络民意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思考
谢雄军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网络民意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的意见表达语境、广泛的公共话题和公众舆论、观点表达直接、真实,倾向于权利的保护。网络民意既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应营造良好的网络民意社会环境,促使网络民意成为我国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实现其与法律运行机制的良性互动。
网络民意;法治湖南建设;民主决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网络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网络民意。网络传播民意的方式为公民参与各种各样的事件提供了一个绝对方便、快速、有效的平台,并催生了许多案例的诞生。远的如“孙志刚”事件,近的如“邓玉娇案”等等,都体现了网络民意的强大力量。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切实改变了一些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加入到网民的队伍,开始起了网络问政的新时代。如“微薄问政”、“晒三公”、“加名税”等等,使得网络民意成为当代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经济生活都必须关注的热点。面对网络舆论场的蓬勃发展,湖南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在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将“网络民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和维护健康的互联网生态环境,坚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维护公民权利,促进政府与网络民意积极互动,获得全国网民和社会舆论的认同和肯定。因此,通过网络民意推进法治湖南建设,成为我省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网络民意及其特点
网络民意是基于网络技术而诞生的新型课题。其实,该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是通过网络表达出来的民意,所以,网络民意是在网络这一公共空间,广大网民在此就热点问题、公共事件等公共发表出的意见和见解。网络民意是当代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兴话语表达力量,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网络民意的主题是变化且即时的。相比于以往的报纸等平面媒体,网络上的主题讨论是非常具有即时性的。而且,在表达方式上,平面媒体限于信息量、版面设计、参与程度等限制,民众只能被动的接受和获取信息,甚至更多的时只能通过私下闲聊来表达公共意见和看法。比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如果是平面媒体报道,则顶多是由记者发一则新闻通稿了事,人民对此的关注程度不会很高。然而,由于网络媒体的传播力量大大超过了平面媒体,“我爸是李刚”的话语通过旁听者的转述和网络的迅速传播,广大网民很快就参与到此事件的讨论中来,还有一些网民自发组成“调查团”,调查口出狂言中的“李刚”到底为何许人物,并第一时间将李刚的身份在网上公布,“这样不仅扩大了网络民意表达的单向度影响力,而且互
动性带来的即时反馈也可以反作用于网络民意,如滚雪球般不断放大,直到被相关领域重视并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止。可以说,没有互联网这个广大的信息发布平台,即便通过局域网络形成民意议题,这种小范围的民意也会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很快自我萎缩直至消亡。”[1]没有任何一种媒体能够向网络一样,有那么庞大的记者群体,有那么庞大的参与群体,有那么庞大的评论群体。这里,没有门槛,没有障碍,没有限制,只有观点、意见和交锋,因而也能够引起更多的共鸣和讨论。
第二,网络民意的表达观点直接、真实。以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为载体的媒体都有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效果追求,更多的还有自己的政治定位,强调政治正确。所以,在表达观点和话语时,相对来说比较谨慎,话语比较讲究。而且,这些媒体上的作者或者编辑往往都是实名制的,更有可能为了掩饰或者修辞,对话语表达采用尽可能缓和的方式,甚至对一些问题采用“无可奉告”的表达方式。这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也是对承担责任的回避。但是,网络环境下,这一切都变了。因为“互联网是一种具有虚拟性、超地域性等特性的传播媒介,它以各种虚拟的社区和讨论组而代替了建立在物理空间中的交流空间,网络社群突破了地缘、血缘和、Jk缘的界限,使得公民之问的自由交往和自由联合成为可能。”[2]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人,只要注册一个虚拟的账号就行,他们就更容易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而且,对于现实中发生的较多事件,广大网名都会以自我最聪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和倾向性。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对社会以及社会事件、公共话语表示直接的批判。比如,在“许霆”案中,广大网民就将许霆的行为和贪官的行为进行类比,认为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给国家带来上亿元的损害,都只不过是判十几年有期徒刑;而许霆只不过是因为自动取款机发生了错误而获取了一些好处,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所以网民们觉得“官官相护”。再联系到平日里,我国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颐指气使的神态,银行服务态度不好的真实场景,网民们更倾向于同情许霆。所以,这种通过匿名敢于表达的环境让网络充满了真实与坦率。
第三,网络民意更加倾向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说:“由于每个人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所遵循的普遍的伦理原则,都是从社会中潜在的最小受惠者的角度出发加以考量。”[3]罗尔斯的意思是,在无知之幕下,人们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生活的真实处境,那么就必须选择能够实现正义的原则,所以,每个人都会从自己处于最不利者之时法律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来设置原则。罗尔斯本是通过推论的方式来证成他的正义论。但是,罗尔斯无意中道出了人们的一种心态,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所以,当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言论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会更倾向于充当道德警察,在网络充当打抱不平的英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人们的利益保护并非尽善尽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网名就成为监督的重要力量,“我们应当记得‘辽宁刘涌案’,此案尽管程序上有瑕疵,尽管众多法律专家一再拿美国‘辛普森案’两相对照.但百万网民难以理解和接受“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种理论,更不能忍受这种理论首先应用在一个黑社会头子身上,‘刘涌不死、天理难容’,‘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之语此起彼伏,最后落了个最高院提审、速判、速杀收场。‘许霆案’、‘邓玉娇案’当中,网民出于常识性判断,出于朴素的漠视强者,同情弱者的情感,要求对许霆网开一面,对邓玉娇不适用故意伤害及防卫过当,最后以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邓玉娇恢复人身自由收官。”[4]
当然,整体而言,鉴于民意本身是难以界定的话题,网络民意更难以把握。所以,网络民意还存在非理性因素,容易被少数人给利用,也存在一些网络暴力,也容易造成对一些当事人的权利侵害。这些负面因素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来规制的。我们不能够以网络民意存在缺陷来对此进行打压,而应该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对此表示支持。
二 法治湖南建设重视网络民意的意义
目前我省正处于法治湖南建设关键时期。法治湖南建设一项综合工程,是需要全省人们参与的大事。因此,法治湖南建设要发挥湖南人们的智慧和优势,需要全体湖南人民的参与。此时,将网络民意纳入到法治湖南建设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法治湖南建设引入网络民意可以问计于民,提高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民生决策的参与度。2011年8月2日,《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正式向外公布实施,《纲要》中强调政府决策要“回应社会关切”,并“重视舆论监督”,这意味着法治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将法治建设与民众参与结合起来进行,而网络民意就是其一条重要的途径和力量。网络民意也是一种名义,并且是一种能够更加快捷、方便和迅速直接的民意。重视网络民意,及时掌握网络民意、倾听民声在社会转型期尤为迫切。法治建设要引入网络民意,特别是要引导网络民意朝着积极、健康方向发展,而且也能引导网络民意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比如,在立法之时,就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公布了立法草案文本,向网民征集信息和修改建议。毕竟,网络民意尤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网民建议,是立法与决策十分重要的信息或依据。就网络民意的形成来说,它源自社会现实生活中,并反应现实生活,从中可以找到修正法律的现实性根源,尤其是出台某一项法律法规前后,应当广泛征求民意,最大限度地落实民意。这本身就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必然前提,所以应当合理地保持这一机制的常态化,以实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通过集中与运用网络中的智慧力量,最大可能地扫清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障碍。我们湖南的法治建设,是既承继了法治中国的传统和属性,但是也结合了我们湖南本土的特色和创新,这就更需要发挥湖南人民的智慧。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决策是问计于民,是从湖南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寻计于网络,那么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将更有利的体现出来。
第二,法治湖南建设引入网络民意可以搭建民意平台,扩大百姓话语权,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促进执法公正。传统的信息表达机制都受到了制度的限制和制约,因此,民众的利益很难直接有效地反映到决策层。而且,传统信息传输机制受到传输成本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及时完全。而网络媒体的诞生解决了传统媒体所面临的问题。网络媒体作为民意反映平台,可以及时有效的反映民众的期待和需求,而且这是成本高效益的双向交流机制。这也是最近几年许多地方要员问计于网络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它减少了利益输入的中间环节,有助于实现公众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另一方面,作为沟通公众与政府的桥梁,扩大了政策问题的来源,有效地克服了政府决策的一些“盲区”。法治湖南建设就应该吸收这种低成本的民意反映机制,将民众的诉求和现实的需要添加到利益动因之中,将法治建设的参与度作为反映湖南本土特色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指标。在这样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必然不能信息关门,也不能关门执政,必然将阳光政府建设引入到新的时代当中。而民众也能够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改变传统的单向接收的做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将因为网络这一平台的搭建而变成便捷的路径。现代社会任何权力必须建立在监督和制约基础之上。在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还不尽完善,政府仍然处于强势,公民处于弱势,政府的权威性是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随着网络民意的兴起,公民对于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更加强烈,媒体在行使监督权力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法治湖南建设引入网络民意,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较多社会矛盾之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信息部公开不透明所导致的。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发生之时,网络谣言满天飞,但是政府却一直是关门决策,既没有发布政府对此事的立场和态度,也没有做出有公信力的解释。当观众感觉到自己被“蒙骗”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需要通过一些渠道了发泄。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充分的发挥网络民意的作用,针对网络空间大家提出了的诸多疑问进行有针对性、有公信力的答复,那么许多事件就可以完全被避免。只有让公民知道国家机构中权力运行的内部和外部情况,让百姓参与到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让民众知道政府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实现政治、经济及全部社会管理的公开化、透明化,建设“阳光政府”,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使公民及时、准确、真实地了解国家事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才能在公民之中形成民意,才能真正的引导社会矛盾的和谐化解。
三 合理运用网络民意助推法治湖南建设
尼葛洛庞帝曾说:“我看到同样的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足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5]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权力制衡观念,对法治湖南建设有新的认识。所以,麦克卢汉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6]这也告诉我们,在法治湖南建设中必须合理运用网络民意。
第一,正确认识网络民意,通过制度来引导网络民意为法治湖南建设服务。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控制的不好,就有可能让政府工作陷入非常被动的姿态。但是,舆情问题不能只采取“堵”、“捂”、“拦”、“截”,这样就会造成网络世界乌云重重,民意很难畅通。所以,要建立合理机制,引导网络民意,积极关注民意,实现民众和政府的良性沟通,从而减少行政成本。所以,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合理认识网络民意,不要把网络民意想象成“拦路虎”,更不能想象成见血封喉的“毒药”,这是政府必须树立的思想。
第二,法治湖南建设要建立起网络民意畅通平台。在政府充分认识网络民意的基础上,政府要通过网络延伸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之手”,激活地方尤其是县区基层的所有电子政务平台,合情合理公开政务信息,认真梳理网民诉求与意见,并进行答复与反馈。为了能够有效的实现网络民意畅通,政府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来加强网络民意的实效性。比如,通过绩效评估机制,定期对政府与网民之间的反馈与互动进行考核。特别要鼓励各地政府官员掌握论坛、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的运用,按职能系统注册论坛ID、开通官方机构博客、微博或官员个人博客、微博,发挥博客、微博即时、广泛、互动性强的传播优势,将官员行为纳入到民众监督视野。没有政府官员的参与,光有民众的鼓噪,很难形成一种互动,也很难满足民众对政府事项知情权的渴望。但是,官员通过网络问政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毕竟领导干部的时间有限,很多人基本不上网或者很少上网,因而很容易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在坚持保证民意畅通机制的同时,并不强调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发微薄、建博客,只要能够保证政府信息及时公开,负责官员能够保证公开民众心中想知道的疑问。对官员的发微薄、建博客,每天都上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不需要形式主义,而只需要能够实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度和机制。
第三,法治湖南建设要让网络民意表达有合理的程度保障。网络民意也是一种民意,而且是更新较快、比较及时的民意,我们不能对此粗心大意或者疏忽了事。对于法治湖南建设来讲,我们必须通过程序法治建设来保证网络民意进入决策层视野:首先,要设置网络舆情官员,对于网络上的各种观点及时把握和侦察。舆情官员的职责不是控制舆情,而是协调舆情。即一方面在咨询了各相关政府部门以后,对网络上反映的情况给予反馈;另一方面是对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公共话题进行整理上报;其次,对于网络民意进行排查,特别是注意收集网上提出来的一些非常有见解、对湖南经济建设发展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和报告,形成文件汇报给主要决策者。得到主要领导回应和批示的,应当及时在网上公布通报。最后,对于网络民意,必须采取疏通政策,由此,必须制定网络民意上报办法,为政府决策者注意到网络民意提供法律支持。
[1]马慧茹.论网络民意的形成及其特征[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2]齐 鑫,张慧平.论网络民意的内涵及特点[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
[3]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吕中国.网络民意的法理学思考[J].法治论丛,2009(9).
[5](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 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6]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D920
A
1674-5884(2012)05-0167-03
2012-03-10
谢雄军(1979-),男,湖南邵阳人,经济师,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责任编校 谢宜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