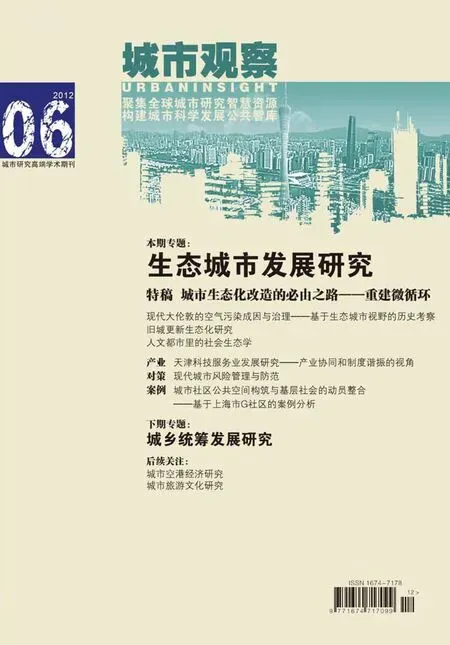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
——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2012-04-02刘中起
◎ 刘中起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
——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 刘中起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楼道自治 公共空间 共治
一
上海市G社区成立于1999年,地处中环线和外环线之间,辖区面积6.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9万,现有37个居民区、68个住宅小区,是一个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人口导入型纯居住社区。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新型社区,知识分子多、年轻人多、新上海人多成为G社区的三大典型特征。这种现代社区极易形成一种“围城”现象,使得居民被隔绝在单元住宅内而失去了人际间的交往,社区凝聚力低,难以形成现代社区情感,从而直接阻滞了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构筑。在G社区调研中发现,94.37%的新上海人愿意参与社区建设。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社区的每个居委会平均要管理1350余户家庭、4000余人口。如何在超大辖区内营造亲和的公共空间,创造一种适度的居民自治平台,促进居民亲和力的形成,消除社区人际关系陌生化,让社区自治组织能够直接有效地和居民进行情感沟通、构筑“后单位时代”的新型熟人社区成为G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的首要难题。上海市G社区从2011年起,以“守望、安全、互助、协商”为理念,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以楼道居民自治为载体,积极推动“居民楼道自治”实践。通过“楼道公共客厅”与“居民楼道自治”的实践,不断拓展社区事务的公众参与面,培养和激发公民主体意识和理性参与意识,极大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G社区从各居民区申报的127个楼道自治建设试点中,重点培育了10个“自治楼道”典型,形成了服务需求导向模式、问题处置导向模式、关系凝聚导向模式三种可复制的楼道自治模式,初步建立起党建引领下的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案例1:服务需求导向自治模式
“笃、笃、笃……”某日傍晚,家住17号楼的陈先生家门被敲响,推门一看,原来是楼上的车先生。“老陈,我在北桥买了别墅,这个是我新房子的地址,有空来白相啊。”(注:白相为上海方言也即玩的意思)一番告别之词,让老陈感慨万千。时间拨回5年前,老陈举家搬入刚造好的G社区,那时,他刚从企业管理岗位退下来,回到社区,他发现邻里间互不相识,见面了不过点点头,这让他无比留恋起小时住过的石库门,谁家有事在窗口一叫,大家都会出来帮忙。能不能找回曾经的那种感觉呢?老陈开始迈出第一步。他最先敲开的是对门的人家,这家住着两位老人,老先生姓殷,身体不好,长期卧床,夫人一直忙于照料爱人。当居委会请来社区医生坐堂代居民配药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殷先生一家,免去了老夫人每周往返市第六医院配药的奔波……如此一来二往,老陈几乎和楼道里11层22户人家都打过交道。可22户人家来自天南地北,上海人、新上海人都有,他们之间显然缺乏“串联”起来的机会,直到老陈将G社区推行的书报架搬进了17号楼。
一年前,书报架正式“进驻”楼道一角。老陈在书报架上贴出了自己写的“发刊词”:希望楼道居民贡献自家闲置的书刊,让知识流动起来。很快,这个小小的举措叫好又叫座,不仅借阅率高,更多种类的书刊出现在书架上,不少还写上了自家门牌号和姓名。如今在上电梯前,17号楼的居民都会在书报架前驻足一会,遇上邻居更会热络地聊上几句。在书报架的牵线下,“楼道自治管理小组”开始正式成立。小组成员第一次开会就提出要解决楼道里停放非机动车的顽疾。他们与物业公司商量,在楼道外辟出临时停车点,并在停放在楼厅里的非机动车上放上“温馨提示”。不到三天,困扰多年的问题就得以解决,邻居们的“自觉度”让老陈这个组长颇为欣喜。他说,这是水到渠成,邻里关系融洽了,谁都希望家里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案例2:问题处置导向自治模式
68号楼里共有24层、45户住家。楼组长樊阿姨记得:“2004年我搬进68号时,大堂停满自行车、助动车,进进出出都不方便。为争个车位,或是不当心碰倒旁边的车,几家人总会闹点矛盾。”2008年,樊阿姨当上楼组长。她选了个休息日,在晚饭后跑下楼,用楼层对讲机挨家挨户通知大家下楼开会,近三十户居民站在大堂里开起居民大会。68号楼的头一次居民大会开得相当成功,不仅大堂里的非机动车被移到地下室停放,楼里居民还自己动手布置,大堂环境焕然一新。现在这里成了68号楼的“大客厅”,有沙发有茶几,墙上还挂着楼里居民的“全家福”。
“有了第一次成功,之后有事需要邻里协商,我还是等吃好晚饭,用对讲机一家一户通知,大家听到就马上下楼来,坐在大堂里谈一谈讲一讲。”樊阿姨说。“为什么对讲机一喊,我们都愿意下来,因为只要对讲机喊,肯定是要紧事,对大家都有好处。”家住24楼的殷先生道破其中奥秘。大问题坐下来谈,小问题就在电梯里,贴张告示解决。去年,家住三楼的程老伯发现楼上常有烟头或茶叶渣丢下,还会飘进阳台。他每回见到樊频,总要反映一下。樊阿姨就此写了倡议书贴在电梯里,倡导大家注意楼道文明。过了两天,她走进电梯,正巧遇上程老伯楼上的一位租客在电梯里吸烟。她没说话,笑着指指电梯里的禁烟标志,再指指贴在墙上的倡议书。这位租客一愣,随即熄灭烟头,还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了。”在这之后,程老伯明显感到乱抛杂物的现象少了。
案例3:关系凝聚导向自治模式
前几天,家住96号楼的唐阿姨回家,看见门上挂着两包袜底酥。谁送来的?唐阿姨打电话给亲戚没找到答案。她猜想既不是“远亲”,定是“近邻”。一问,果然是楼上的吴阿姨游览千灯古镇,特地带回特产给邻居分享,送到她家时发现无人,便有了这桩“悬案”。唐阿姨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是因为这幢15年“楼龄”的居民楼有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这种本无形的温情,甚至从楼道颇具人文气质布置里“渗透”出来。走进96号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镜子,这是3楼居民吴先生多年前安上的,他说安上镜子是希望大家把楼道当自己客厅一样爱护。爱种花的他还在二、三楼的楼道窗台上摆上十几盆鲜花。
有了吴老伯带头,96号楼被一点点布置起来,从一楼上到六楼,每层楼都有装饰品。谁家有困难,楼里住户都会伸出援手。吴女士丈夫常出差,自己三班倒,晚班时接孩子放学成了难事。邻居吴先生听说后,和老伴主动揽下这活,足足坚持五年,直到孩子上中学。即使新来的邻居也能很快融入96号楼。4楼小叶来自安徽,两年前初来古美时人生地不熟,问起邻居哪里办暂住证。好心的邻居直接把她带到了社会事务受理中心,接下来是菜场、大卖场、邮局、医院。“楼里的居民真的亲如家人,待我也非常好,出门时都会喊我一声,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这对于刚迁居此地的我可是最直接的帮助。”小叶至今很是感激。作为“回报”,她教邻居们包水饺,她的水饺成了“品茶会”的保留节目。
基层社区之所以区别于社会,就在于其成员拥有较强的共同的社区意识,同一社区的居民由于共同的社区意识而被凝聚在一起,出于对本社区的强烈关注而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但这种强烈的社区关怀意识在我国城市居民当中并不明显。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的社区意识比较淡薄,社区建设又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人们的“单位人”属性并未获得根本性的转变,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都还很弱,单位制的建立,使单位部分替代了家庭的功能成为个人生活和交往的首要选择。当出现家庭和社会不能解决的问题与事务时,人们倾向于诉诸行政权力。①城市社会,楼道是最小的社区公共空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里属于每户住宅的房屋公摊面积,可视为家的延伸;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里属于楼道所有住户的公共空间,是人际交往的通道。如何充分拓展和构筑楼道公共空间,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问题处置为导向,以关系融洽为导向,通过选择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化解人心隔阂,构建熟人社会,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楼道里洋溢邻里亲情,充满家园温馨?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通过居民的自主管理产生价值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培养和激发公民主体意识,促使居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和参与公共事务,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整合。
二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②这些重要论断科学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建设的基本方向、主要途径和最终目的,为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当代中国社区发展主要由政府推动与主导,在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结构构造、功能设计与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出“行政性推进”与“社会化参与”两个基本方向的互动。由此,政府主导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意识的探索性的发育社区的客观过程,包括社区各类社会化组织的逐步发育和形成、公众对社区活动参与的不断扩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社区成员的社会化联系和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等。③上海市G社区居民“公共客厅”与“楼道自治”平台的逐步发育与形成,是上海市现代社区发展中政府主导和基层自治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楼道公共客厅、楼道自治委员会、楼道自治公约、楼道自治特色文化等自治要素是构建现代社区结构、社区功能、社区组织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公众和各类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培育社区认同和归属感的根本性基础。人们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社区草根组织及各类社区公共活动,形成相对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共同的交往产生了公共性,形成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公共事务,居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增高,自然会关注社区内的事情,对社区产生归属感,社区的基础逐渐整合,社区和谐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自由讨论,讨论的话题逐渐延伸,不受国家的干涉。”④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里,其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场所,人们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并形成“公共生活”。人们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寻找与社区发展、自我生活相关的共性问题,在保有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促使共性的问题被所有人接纳,社区内的公共空间主要用来服务居民,为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场所,促使居民聚集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因此,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是拥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人们在这个场域内从事各项公共活动,并产生各种关系网络,正如布迪厄指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⑤作为一种稳定、信任和参与共享的社会关系,公共空间一旦建立起来,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公共空间中的个体能够准确预期将来。在公共空间的关系网中包含着每个成员所需要的物质、人力、技术、情感和文化等资源和需要,而且掌握资源的个体之间非常信任,因此,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每一个人在激活、调动和整合空间资源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很快的速度,正是由于在一个信任的公共空间中能够方便获取各种资源和需要,个体希望“卷入”公共空间的愿望就强,即个体的参与性很强。由于公共空间发挥了沟通、信息交流、舒缓感情、学习与获取资源等功能,从而实现了公共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了个体能力的提高,实现了社会整合和公共参与。上海市G社区的楼道公共客厅,作为一种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楼道居民完全开放,容易形成由熟人构成的初级群体与人际网络,这个群体成员由于长期交往而逐渐产生惯习,并依据惯习来行动,当惯习被经常化之后便成为某种规则,每个获准进入公共空间场域的行动者必然会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也就是会认同场域的规则。因此,楼道社区公共空间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和社区协同,以权利互为平衡为原则,以居民事务为内容,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舆论监督为常态的场域与规则的统一体,在居民的日常行动中由一种生活共同体逐渐凝聚成为一种具有符号价值的精神共同体。
城市居住社区,作为城市居民主要的聚居生活方式,承载着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只有当二者都得到满足时,人们才能获得“诗意的栖居”。而作为其特质表征的社区公共空间,如何进行塑造就显得十分有意义。我国传统社区较少注重公共空间的建设,人们之间的居住空间尺度小,容易产生亲密互动,而传统文化中的“敦亲睦邻”思想更加深了邻里交往。从平房式的亲密互动到直筒楼式的家长里短再到单元楼房的逐渐陌生,公共空间随着住房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地域范围逐渐拓展,成为拥有中心空间的相对独立的结构,其功能也伴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逐渐从注重交往便捷向多元发展,以期缩小人们的心理距离。转型时期,社会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程度较低,而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是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的需要,因而也是我们体制建设的应有内容⑥。在我们的体制建设还不完善,不能充分回应与解决群众利益表达诉求时,社区楼道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重要通道,公共空间中讨论的议程及其结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传递给社区管理层,由社区管理层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与解决,大量社会矛盾与利益诉求被消解在社区抑或楼道的公共空间,从而在一定意义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认为,社区是指一群有很多相似社会背景、个人背景的人,经过长期相处,逐渐形成一种彼此了解并相互接受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从1887年滕尼斯提出“社区”的概念后,社会学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就层出不穷,但在内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却有着重要共识: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一群人,这群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纽带。上海市G社区“公共客厅”与“楼道自治”平台的形成与运行,深刻刻画了社区公共空间的特征与性状。作为一种新的社区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显现,楼道公共客厅的活动空间和社区公共生活的拓展,实际上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参与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居民由家门走向社区的公共空间,获得一种参与性地位与公共性身份,成为社区新的治理主体。社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单纯的地域性概念,日益获得了利益联结和公共交往的稳固性的支撑,建构了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自我管理方式⑦,成为基层社会整合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路径。
三
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即是各种力量在社区空间中相互作用、构成网络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迈向社区善治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广泛流行推进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旨在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改变了以政府统治和管制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⑧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必然要求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作用,注重民主、公开的现代意识,倡导政府、社会、社会组织多元治理、协作互动。随着我国城市社区的分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社区面临的任务与问题发生了新的转变,由此凸显出既有社区治理结构的限度,包括社区利益多元化与表达机制单一化之间的张力、社区矛盾尖锐化与协调机制的有限性以及业主委员会等新社区治理主体的出现等。近年来基层不断频发的各类群体性冲突与公共突发事件使得当前社区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和集聚区,社区自治与民主日益让位于社区和谐与稳定的目标。社区利益的多元化和社区矛盾的复杂化,凸显既有社区治理结构的失效,即社区居委会作为定位于社区居民开展自治的组织,无法涵盖和包容日趋分化的多元社区利益,以及错综复杂的社区利益矛盾。由此从构建社区和谐稳定出发,需要充分发挥政党、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及社区草根组织等多元参与,推动社区自治走向社区共治,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结构新的转型。⑨
基于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的制度功能日益健全,我们注意到居委会负责的社区公共事务逐渐涵盖了人口与物业管理、社区环境整治、社区生活服务、教体文卫发展、社会福利与安全保障的各个方面,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考核体制得以建立,其地位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作为新的社会治理空间的社区难免演化为新的权力网络而再度被整合为国家的组成部分,⑩表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特征有朝“动员性组织”演变的趋势。而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及社区居民的生活形态的改变, 导致基层各类新兴功能性组织因应特定需求而不断产生, 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活动。这些新兴组织的出现意味着社区自治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社区各类新兴自治性组织的出现,即主体多元化的事实,有利于自治力量的维护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是业主委员会作为现代社区内一个重要主体,一定意义上说是现代社区内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治组织。经过选举等法定程序成立的业委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利益诉求从根本上是同每一位普通业主相一致。新型社区内,实行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有组织地解决单个业主无法独自面对的物业纠纷事件,对解决新型社区自出现以来频繁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业委会如何更好地运作社区管理却是一种需要智慧创造的具体实践。在各类社区“老年服务团队”成立的初衷则仅仅是为了满足社区内退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等的需要。上海G社区多数居委会都成立了这种居民组织。这些“团队”在发展过程中不但满足了成员精神生活的需求, 成为社区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而且在社区决策过程中成了测试政策效果的试验田。民选居委会主任通过各团队的领袖和骨干分子可以团结相当部分的居民,把团队整合为社区治理的有效工具;居民的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参加团队并通过团队参与社区事务治理而得到提升。作为社区内部自发生长起来的居民草根组织,团队的成长就意味着社区自治空间的生长。基于社区治理的各相关参与主体需求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在解决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建立相关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结构,本着互利的原则开展合作,通过共治、共决——共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增进社区公共福利,使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达到和谐有序状态的运行机制。
可见,在社区利益多元化和社区矛盾复杂化的现实下,社区和谐秩序的重构依然有赖于社区各种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利益关系的有效调节,为此需要尊重每一个社区组织的主体地位和合理利益,而不单是强化社区居委会或是业委会的自治功能。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利益整合与协调功能,发挥社区草根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以及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与传统的居民自治相比,社区共治的参与面更广、决策立意更高、决策落实更到位、民主监督机制更有效,确保了社区成员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行使。共治格局在本质上则应具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是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它体现了从单一化主体到多元化主体转向的趋势。传统我们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单纯地依赖政府主体。而在社区共治理念中, 除了国家( 政府) 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社区单位等其他多元主体。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 以取得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是管理方式的日益参与化。现代社区治理模式越来越具有从行政化到参与化转化的趋势。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是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的。而现代社区治理则更强调居民参与精神,使得各个治理主体之间通过自愿平等合作的协商、伙伴关系来实现对社区事务的管理;第三是管理结构的立体横向网络化。现代社区治理结构日益具有从垂直科层化到横向网络化的趋势。传统的街居体制结构、单位体制结构只是垂直关系,缺少横向联系。而现代社区共治则强调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组织之间协调与沟通,凭借合作网络实现社区治理,并最终形成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横向的自主网络。
上海市G社区专门整合社区内有限的公共空间资源,为广大社区居民专门建成“市民公共客厅”,并通过“楼道自治”平台培育、扶持各类草根社团组织,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关联度和认同度,引导团队提高自我管理水平,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内目前已发展有各类社团组织390多个,参加群众达5000余人,培育了老年协会、文体联合会、志愿者协会、旗袍沙龙、摄影沙龙等一批精品团队,这些社区草根组织以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为载体,吸引社区不同群体的居民积极参与,使不同群体的社区居民在共同的生活中得到共鸣, 促进了社区公共空间的生成。正如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区草根组织为这种联系和关系的生成提供了组织空间,基于这一空间G社区通过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初步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模式,这一新模式表明在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的新方向,即首先强化执政党在社区的利益整合功能。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坚持党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社区党组织建设,理顺社区党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的关系,明确工作定位,创新工作方式。社区综合党委在制度上需要发挥“把握政治方向,传达党的意图,协调各类组织,凝聚各方力量”的功能;其次是发挥社区草根组织的服务与引导功能。社区草根组织,尤其是志愿性、自治性组织的发展,为扩大居民参与、推进社区管理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大力培育和发展草根组织,建立在社会主体权利基础上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管理模式演变的重要实践取向。为此需要通过完善备案制,进一步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为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鼓励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成为普通型社会组织。同时,也支持一部分项目型社区社会组织在项目完成后及时转型或终止;再次是发挥居委会和业委会的自治功能。一方面按照便于居民自治、议事监督、管理服务的原则,兼顾公共资源配置、地域面积、人口规模、居民结构、社区认同感和物业管理等构成要素,科学合理设置居委会。另一方面尊重业委会作为业主利益代言组织的地位,有序引导其聚合业主利益诉求,表达利益主张的行动;最后要发挥社区居民与组织的参与功能。社区共治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共同参与。社区公众与组织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通过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体系,形成居民自主管理、民主监督、平等协作的新型社区参与机制。由此不断激发社区组织与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凝聚社区意识和归宿感,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协商与和谐关系,从而最大可能地化解各类社区矛盾。
四
市场化改革使得“后单位时代”社区在提供一种共同体式的服务的同时,为重新分化后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地域和生活方式上的边界意识,这种西美尔所谓之“空间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唤起的“地域忠诚”,为共同体性质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从上海市G社区的“楼道自治”实践看,这种外部条件只是共同体得以展开的外在形式,至于如何在社区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通过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营造出事实上的“有机的共同体”,则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然而现代国家统治下的“社会”, 即使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它仍然不存在完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社区作为现代国家创构的产物,自身并不具有演化空间结构的独立意志,其在治理空间方面所做的一切变化,主旨都在于以最贴切的形式满足现代国家的治理需要,反思性地贯彻现代国家整合社会的主观意图。无怪乎城市基层自治领域的各项变革,其最初的驱动力都来源于政府的主观设计和国家权力的积极推动。从对G社区社团组织与公共生活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公共生活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必须借助具有公共性的场景和仪式才能使自身得以展开, 这就使社团组织的发展不自觉地带有天然自生性的外观;另一方面,原有的具有自发性质的社团组织,唯有被纳入现代国家的秩序建构过程中,才具有承担公共生活的公共性,正是国家的“在场”使各个公共生活主体转而具有了公共性,并借助这种公共性实现了相互间的沟通交往和利益满足。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共生关系,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在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内,党建的深入进行,使城市社会空间的领导力量实现着重构,而党政共治的推进无疑将有助于这一进程的发展,有助于党对执政合法性的追求和对执政基础的巩固,从而使社区公共空间的领导力量更好地实现整合。特别是在上海社区发展的今天, 政党对社区发展的引领成为上海社区共治的一个突出特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的社区社会力量的成长,不论是作为个体的社区人还是作为整体的社区民间组织,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看到了国家对上海社区的创新和探索, 以及一批致力于社区发展的社区政治人所具有的先进理念, 这些都为上海社区未来真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新的形势要求和社区体制的改革进程,表明社区治理创新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即:建构党政主导与社会协同有机衔接的社区共治、自治机制,关键在于有效动员社会力量、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而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如何培育多元参与的社区公共性领域?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培育社会化的社区建设主体的问题。
社区建设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社区的居民自治,难以形成社区层面的共治。居民居住形成的区域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其管理应该是公共性、自治性的。这种社区自治性和公共性的成长促进了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成,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和动力。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而社区的自治性也在这种共治参与的互动中得以成长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在社区的行政力量通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仍得到强化,各地方政府都不断将人力、物力下沉至社区,但其覆盖的人群主要是社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一旦社区遇到卫生、安全、维修等物业方面的问题,这两股行政力量因不涉及物业管理都无法直接介入解决,且社区居委会的法律自治身份与实际的行政管理身份长时间存在明显的错位;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与居民之间纯粹的市场关系,也导致大部分物业公司营运目标是获取利润,而不是让居民满意。更何况社区还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存在,推诿责任、相互扯皮并不鲜见。而近年来不断兴起的业委会有居民赋权但不具备法律身份,也使得在社区缺乏话语权,参与治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未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方向何在?在社区共治中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如何界定?在社区共治方面,如何坚持以街(镇)为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责任主体,如何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街(镇)的公共政策能力,改变社区管理与服务资源的配置方式。通过建立街(镇)层面的公共财政机制,社区管理与服务项目的招投标机制,培育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社会市场”,通过资源流通、市场竞争、利益联结等社会化方式调动各类社区组织的协同参与将成为未来社区共治的重要议题;而在居民自治方面,鉴于居委会“去行政化”面临宏观体制框架的重重制约,提升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是否可以通过自治属性的增量扩大来实现。街(镇)向居委会下派任务,如何由“费随事转”改为“购买服务”,以便凸显居委会的主体性;面对各种居民自组织和专业性社区服务组织发育,居委会职能如何一方面由“全能”转向统筹协调,以突出居委会的自治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如何提升自身对居民邻里的动员能力、对社群领袖和社会组织的培育、整合能力。同时因地制宜,以社区党建区域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社区服务项目化为主要内容,建立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注释:
①马西恒,刘中起.都市社区治理——以上海建设国际化城市为背景.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0页.
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区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
④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M], 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Mass :MIT Press ,1991:43.
⑤Pierre Burdieu and Loic J. Wacquant.. An Invitation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2:72.
⑥孙立平.构建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南方周末,2004,1,1.
⑦李海金.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中州学刊,2009(4).
⑧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2页.
⑨陈家喜,蔡国.管治、自治、共治——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转型.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3).
⑩胡位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
Building Public Space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Mobilizing Citizens: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G in Shanghai
Liu Zhongqi
Public space in urban communities is identified phys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G in Shanghai explores the exercise of residents’ autonomy in public lounges. The exten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s within residential building strengthens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establishes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mechanisms, improves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transforms it from a living community to a community of faith, guarantees a safe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and promotes mobilization of citizens. The increasingly autonomous community lays the foundation not only for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social forces, but also for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ommunities. The future trend is to develop multilayered spaces for negotiation 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ffairs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bot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utonomy. That will form a new pattern in which smooth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are to be achieved,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residents’ autonomy could combine seamlessly.
autonomy within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 public space; corporate governance
book=156,ebook=158
C912.81
10.3969/j.issn.1674-7178.2012.06.015
刘中起,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卢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