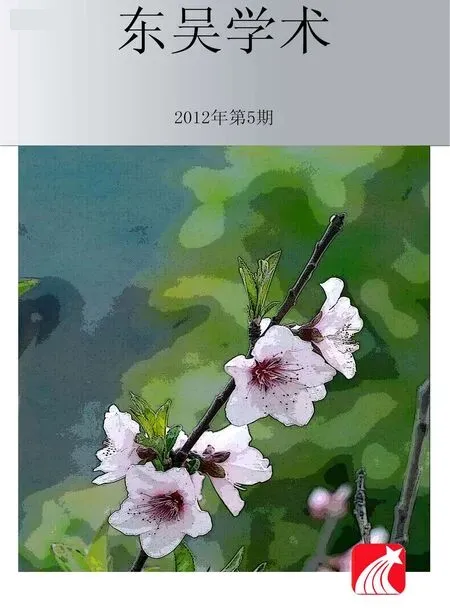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
——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2012-04-02南帆
南帆
现代中国文学
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
——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南帆
历时十多年的时间,格非完成了长篇小说三部曲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对于格非的个人写作而言,这是一个重任的完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随着对三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我的种种感想持续积累,并且渐渐地摆脱了芜杂状态从而清晰起来。我觉得,整理和表述这些感想肯定是一种巨大的乐趣。
谈论格非的三部曲,“历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一百多年历史之中若干重要的段落成为这几部小说的重要背景。如何叙述一百多年历史之中包含的几次重大革命,这是《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遭遇的难题。《春尽江南》进入了后革命阶段,然而,这个时期发生的许多故事仍然仰承了革命的余波。可以说,如果不清楚这些历史段落发生了什么,人们对于小说的解读肯定要逊色许多。尽管如此,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格非的文学工作想象为历史知识的启蒙。相反,熟悉历史著作的人多半会提出另一些问题:文学话语为什么如此处理这一段历史素材?文学的叙述聚焦于什么,同时又屏蔽了什么?这与历史著作存在哪些不同——文学的结构带来了什么?格非是怎么想的?
现在,我想提到三部曲阅读带来的一个特殊经验——疏离感的不断出现。栩栩如生的现场气氛之外,我还常常觉得故事退到了远处;生活丧失了紧迫性,人物和各种景象之间的比例改变了。通常的阅读经验表明,人们总是尾随主人公沉湎于故事的纵深,或喜或乐,或惊或怒;但是,三部曲的阅读不时把我抛到故事边缘,仿佛与故事核心存在某种难以弥合的距离。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擅长设计出各种手段中断情节的紧张性,制造某种疏离感。例如,《红楼梦》飘渺的太虚幻境,《安娜·卡列尼娜》多次现身于安娜梦境的那个俯身于铁器的胡子蓬松的老头儿。这些意象无一不是把故事悬搁起来,设计另一个高悬于故事上方的视点。这时,人们可以像上帝那样后退一步,从某一个高度看到宿命的轨迹。格非也是这方面的能手。还是先锋小说群落的一员时,他就善于抽去各种故事的重量,使之产生“如真似幻”的感觉。这个评语来自当年我撰写的一篇格非小说的评论,标题是《纸上的王国》。我愿意引述几句话形容隐含在格非小说内部的不稳定之感:
“纸上的王国”是一个奇异的意象。我企图借用这样的意象转述格非的小说——转述格非的小说产生的那种如真似幻的感觉。的确,格非的小说仿佛拥有另外一套时间与空间,那里的房屋、桥梁和人物似乎没有重量。这些小说很快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轻”的悬浮之感。一切如同梦中的景象,既逼真同时又失真。这个纸上的王国变幻无常,伸缩不定,人们甚至怀疑它可能被一阵旋风刮得无影无踪。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曲产生疏离感的原因显然与先锋小说不同。如果说,先锋小说的疏离感源于当时的某种哲学考虑,那么,三部曲的疏离感源于格非如何与历史对话。无论是高调的革命年代,还是后革命转入的实利主义时期,格非均是打发一些边缘人物充当主角。所以,所谓的“主角”并不是指他们成为历史事件的轴心,而是指他们成为叙述学的轴心——这些边缘人物提供了叙述历史的视点。置身于边缘叙述历史,这就是疏离感产生的重要原因。《人面桃花》之中的秀米是一个富家子弟,由她主持的革命显现出一种奇怪的性质——她与传统的革命主角具有很大的不同。她的革命不是从贫穷、饥饿和反抗开始,继而获得政治信念教育、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以及各种殊死搏斗,她的革命更像是书生意气、奇遇、畸恋、乡村版乌托邦思想混杂的产物。小说没有具体地交代她如何卷入革命,秀米东渡日本的情节隐在幕后。秀米显然没有成为职业革命家。革命失败之后,她寄居在自己的老宅子里,哑口无言地生活了十来年后去世。这么说或许更为准确一些:秀米仅仅是按照自己的线路卷入革命的某一个局部,短暂地绕了一圈之后就被甩了出来。尽管如此,《人面桃花》利用秀米的人生阅历联结这一段历史。秀米的家庭关系、秀米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春梦、革命党人张季元与母女两人的性关系、张季元日记的持续影响、秀米对于母亲和“小东西”的情感……这一切占据了叙述焦点的时候,所谓的革命退到了远处,而且仅仅片断式地显现。或者可以说,秀米这种人物在巨大的革命洪流之中始终是疏离的、落落寡合的,她的所作所为带有某种梦游式的恍惚。人们当然要考虑到,这种叙述方式隐藏了格非进入历史的姿态和想象方式。
《山河入梦》之中,这种落落寡合和梦游式的气质被主人公谭功达县长,即秀米的次子继承下来了。通常,谭功达的身份应当成为革命的弄潮儿。身为一县之长,主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新农村建设,他是真正的主角。然而,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气质使谭功达无法担当如此重任。他迷迷糊糊,疏于人事而耽于幻想,怜香惜玉有余而当机立断不足,不仅在各种“恋爱”事件之中节节败退,而且在勾心斗角的权力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撤职之后不久就进了监狱,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一些人认为,谭功达的性格与《红楼梦》的贾宝玉存在某种相似。但是,贾宝玉那种公子哥儿式的缠绵与革命的血与火、铁腕手段与雷厉风行格格不入。所以,谭功达注定没有好下场。当然,这同样是一个有趣的谜团——这种人物怎么可能出任县长之职?如同秀米如何参加革命一样,谭功达县长身份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得到清晰的交代。小说之中间接地暗示他的新四军出身,而且得到了某一个当权的领导护佑,这并没有解开谜团。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气质只能是一个刺眼的缺陷。县政府内部,谭功达从未树立一号人物的权威,办事员、秘书都敢向他使小脾气,遑论那几个副县长或者办公室主任了。可想而知,这种软弱的性格怎么可能在部队里建立特殊的功勋?
我要再度提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概念。我曾经在其他场合分析过,“小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依据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数量,而是某种文化气质。讲求生活情调,重视或者尊重个人,保持独立的思想而不愿意附和他人,清高、骄傲或者自以为是,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常见的文化特征——很多时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趣味相左,无法全身心地融入工农革命之中。这是毛泽东反复告诫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的原因。当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投身于危险的革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他们大多数衣食无虞,而不是因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揭竿而起。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首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当然,这也是来自工农的革命同仁不怎么信任他们的理由。理想信念仅仅是一张未曾兑现的理论支票。知识分子思想灵活同时患得患失,到了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从后门逃离——他们始终留有后路。这些潜在的观念常常妨碍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轴心阶层。相反,一旦风吹草动,他们总是成为革命队伍之中首先要被清算的对象。显然,谭功达大约就是这么一种人物。
声称谭功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没有冤枉他。他与姚佩佩暗通款曲,惺惺相惜,姚佩佩成为杀人犯之后他还恋恋不舍地包庇纵容,这些行为无一不是典型的 “小资产阶级”症状。姚佩佩是《山河入梦》之中一个相当成功的女性形象。她的情趣、小脾气和人生态度日复一日地逐渐显出了魅力。当然,这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谭功达与她的情投意合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彼此延宕了很久才共同意识到这一点。《山河入梦》之中,谭功达与姚佩佩情投意合之前居然意外地出现了谭功达与张寡妇的婚姻。这是小说之中精彩而沉重的一笔。肥硕的张寡妇带着儿子到谭功达住处胡乱纠缠一气,他就胡里胡涂地和她上了床,钻入一个拙劣的圈套。考虑到谭功达如此软弱的性格,这种男人式的错误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来,这个打击又是毁灭性的,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事业的失败。他错过了姚佩佩,几乎也就是错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姚佩佩坠入命案的间接原因,谭功达与姚佩佩亡命天涯之际的悲剧性爱情成为格外动人的一幕。
让我们再来看看《春尽江南》挑选了什么人作为主人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期。大多数人熟悉这个时期的氛围,但是又不易一言以蔽之。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繁荣的市场经济到后现代的碎片拼贴,似乎什么都有一些。总之,是多种社会文化成分的混杂。这时,主人公出现了。谭端午的身份是一个诗人。诗人在这个时代占据一个什么位置?极少数诗人可能是最富于洞察力的先知,大多数诗人是边缘人物,若即若离,百无一用。如果诗人无法站在一个神秘的高度颁布时代的号召,那么,他们的日常作业只剩下吟风弄月。然而,现在恰恰是清风明月一文不值的时刻,诗人常常无法与世俗社会有效地对话。这也是谭端午的妻子屡屡奚落他的原因。总之,谭端午诗人的激情已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之中耗尽,现在相当程度地游离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之外。他可以退出生活,站在旁边发表一些局外人的反讽性感想;当凡俗的生活过于麻烦或者令人厌恶的时候,他也可以及时地抽身而出,转过脸去表示没有看见。“旁观者清”,局外人的视点往往产生独到之见;另一方面,局外人的视点也可能回避了深刻的内心矛盾乃至精神分裂,例如,不得不违心地从事一些自己所不愿意承担——甚至是所反对——的工作。无论如何,诗人还是保留了站在时代之外指手画脚的习惯。
或许可以说,谭端午的先人——谭县长、秀米,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秀米的父亲陆侃——身上无不存在某种诗人的激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乌托邦理想的热忱。桃源图、花家舍、联结家家户户的走廊或者挖掘运河的设想,无一不是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各种现实翻版。他们如同飞蛾投火一般地扑向这个理想,哪怕被视为不可理喻的疯子。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诗人气质。诗人总是从不尽的日常琐事之中抬起头来,仰望那些不可企及的东西。然而,到了谭端午这个时代,乌托邦理想已经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摔了下来,成为一地的碎片。污染的水源、遍地垃圾、无数可耻而又不得不为的交易、形形色色的流氓地痞,还有一些似乎比现实主义者还要清醒的精神病患者。对于力不从心的谭端午说来,所谓的乌托邦理想已经完全解体。除了躲在家里听一听古典音乐或者发表几句机智而无用的牢骚,他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如同他的一个个先人,诗人又被这个时代抛出来了。
当然,如此叙述的时候,人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情况——人们身边的历史始终在持续地演变。尽管秀米、谭功达、谭端午三代人共同的命运是撤出社会生活的核心,孤寂地置身于老宅子、监狱或者地方志办公室,意气消沉,无所作为,但是,历史的洪流仍然汹涌不息。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至今,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一个封建王朝倾覆了,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远去,现代意义上新型的民族国家昂然崛起,核弹头、人造卫星乃至航空母舰陆续问世,电视机、互联网正在形成一个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中国的市场敞开了边界迎接八面来风……这些走马灯式的景象或许与秀米、谭县长和诗人谭端午的想象相距甚远,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历史会止步不前。三部曲之中,接踵而来的历史事件与主人公游离的局外人身份始终构成一种张力。这隐含了一种错位。他们与历史的关系是小说的一个焦点,所有的情节无不显示出:他们三个人均是历史之中不合时宜的人。他们试图努力成为历史的主角,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扑了个空——历史在别处。所以,他们三个人只能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之中脱离出来,低头踞守一己的秘密情感空间。乌托邦理想的破碎和投身历史所产生的失望能不能由一己的秘密情感加以弥补?
这首先建立在一种想象之上,走马灯式的历史与一己的秘密情感空间是两个不同的区域。两者界限分明,如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卢卡奇曾经认为,古希腊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表象与本质、情感与思想、个性与共性、私人与社会尚未出现分裂。荷马史诗的明亮风格正是这个黄金时代的证明。然而,这种黄金时代不可能恒久地维持。史诗之后,小说的主人公已经是孤独的主体。他们仅仅代表个人而无法显示生活的本质。如果用中国古人的话形容,“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一分为二。也许,卢卡奇心目中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将重新弥合这种古老的分裂。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将摧毁一切阶级产生的基础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型社会。这当然也是表象与本质、情感与思想、个性与共性、私人与社会殊途同归的时刻。遗憾的是,三部曲表明,如此理想的局面远未出现。尽管革命已经发生,但是,分裂仍在持续,例如,革命与爱情无法共生共荣。有趣的是,三部曲的主人公总是在革命的高潮过后才刻骨铭心地意识到真正的爱情。当然,两者的前后相随常常产生了某种回环式的效果:后者成为前者的慰藉。“兼济天下”的梦想严重受挫之际,与一个心爱的人厮守后半生就成为“独善其身”的重要内容。
然而,格非的三部曲丝毫不肯通融——《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的全部爱情无一不是以悲剧告终。主人公都是在沦落为历史局外人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爱的是谁;可是,就是在主人公意识到爱的是谁之后,他们再也不可能与爱人晤面。秀米的张季元已经死于非命,谭功达的姚佩佩被缉拿归案,谭端午的庞家玉上吊身亡。血腥、绝望和心如死灰之后,爱情的来临如同枯木逢春,这至少赢得了人生的一个局部;可是,短暂的梦幻之后是更为空旷的悲凉。这些阴差阳错的爱情注定得不到大团圆的结局,一己的秘密情感空间再度失守,背后空无一物。这时,人们不得不从一百多年的历史背后聚焦到若干悲凉彻骨的人生。
南帆,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