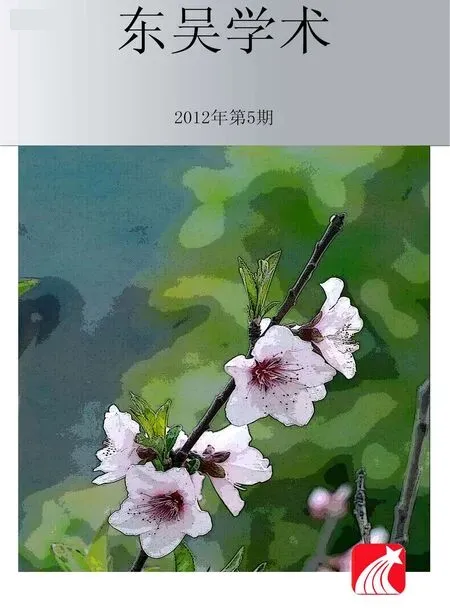建构上海·日刊一页*——世纪之交报章小说的美学原理
2012-04-02戴沙迪著郭冰茹译
〔美〕戴沙迪著郭冰茹译
海外汉学
建构上海·日刊一页*
——世纪之交报章小说的美学原理
〔美〕戴沙迪著郭冰茹译
在晚清的最后二十年,报刊连载成为中国小说最主要的发表形式,就像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和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代早期,无论是作为报纸专题每日印行、文学副刊每周刊行,还是小说期刊每月发行,这段时间的白话小说总是一段一段地发表,就像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亨利·詹姆斯。早在一八九二年,上海作家韩邦庆就表达出他对连载形式的推崇,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悬念,激发读者对后续故事的想象;在一九一〇年之前,对连载小说的“瘾”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美学经验,它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不断加剧。本文意在探求连载形式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发展轨迹,考察分期刊载与当时上海的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并描绘与分期刊载相关的美学原理的影响。
两种方法统领了关于晚清和民国初年连载作品及其社会和美学影响的研究成果:一是将连载作品看成对小说发表影响至大的商品化形式,包括忽视其美学价值;二是关注明清白话小说的章回体例,将其作为连载形式毋庸置疑的鼻祖。①“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也讨论了与20世纪初期文学作品不断商品化的相关问题。通过提请我们关注分期出版的意义,通过讨论已有的美学传统、印刷品的工业化模式和连载小说的结构特点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成果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史作了卓有意义的贡献。但是,当我们面对贯穿一八九〇-一九一〇年代与分期刊载联系更为紧密的白话小说——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叙事——时,这两种方法便遭遇到了难题。
从这些难点出发,我力图呈现:首先,这段时期特定的报章小说必须被严肃地视为美学作品:它恰恰展现了通常认为其所缺乏的鲜明的文体素质,即:错综复杂的精妙紧凑的组织结构。第二,正是通过其美学原理,上海报章小说在关于这个城市的文学想象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上海被描述成一个值得造访的幻想所在,一个媒体和文化中心,一个自一八九〇年代以来引领中国潮流的都市。
一八九二年,作家、编辑家、文学评论家韩邦庆开始在他自己主编的文学半月刊《海上奇书》上连载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专栏作家颠公后来评价说《海上奇书》开“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①转引自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13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事实上,《海上花列传》的刊行掀起了一轮以连载方式进行上海叙述的浪潮:《海上尘天影》(一八九六)、《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一八九八)、《海天鸿雪记》(一八九九)、《海上繁华梦》(一八九八-一九〇三),还有许多在文艺副刊或者日报上连载。整个一九二〇年代,像《歇浦潮》、《人间地狱》、《上海春秋》和其他在日报上首次亮相的连载小说都保留了上海小说的基本特征。②关于《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和《海上繁华梦》的出版细节见Des Forges:“Street Talk and Alley Stories:Tangled Narratives of Shanghai from Lives of Shanghai Flowers(1892)to Midnight(1933)”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98.《海上尘天影》发表在通俗小报《趣报》上,日刊一页(见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71页。也可见《游戏报》1897年7月22日的广告,介绍《新编断肠碑》,《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前19章连载在1898年春季的《消闲报》副刊上,后来很快从1898年7月开始,将其完整的一百回连载在吴趼人主编的《采风报》上。感谢Patrick Hanan(韩南)提供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采风报》上的小说广告。是这种连载形式中呈现出的叙事类型首先构成了小说发表的权威模式,是这组都市叙述将这一模式出现的最初时刻与上海这个城市连结起来。在世纪之交,弹词在连载作品中也很普遍,但是随着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刊对小说的热衷,各种叙事类型,从公案小说到暴露小说(谴责小说),像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开始以连载方式发表。作为中国新兴的传媒工业的中心,上海保有两种主要连载媒介的资源优势(文学期刊和报纸),同时上海也成为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此类文学叙述的中心主题。③1897年12月发行的第142期《游戏报》的一则通告说,会将《凤双飞》作为副刊每日免费赠阅一页。早年仅以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凤双飞》由此分期刊载许多年。
报章小说的兴盛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在一八七〇和一八八〇年代早期,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品在上海的报纸和期刊上连载。④例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73页中列举的1902-1917的27份杂志和报纸中,有21份出自上海,上海和广州并列第二,每个城市也仅各出版2种。虽然这些早期的连载作品代表了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时刻,但那时它们似乎仅仅是出版方式和文学形式的实验品,仅有少量被证明是有价值的。《申报》编辑之一,专门负责一八七〇年代连载小说版面的钱昕伯总结说,将长篇小说分段刊载是个错误,因为这些作品理应呈现全貌。为了迎合读者,他很快将后来所有《申报》发表的散文和再版的白话小说改为合订本出版。
钱昕伯诟病于分期刊载为读者留下悬念,而不能如期待中那样一下读完全文。大约十五年后,韩邦庆恰恰在这个假设的瑕疵中发现了连载作品的好处。他对连载小说的维护基于一个普遍的美学标准,即为了增加阅读过程的悬念,叙述可以通过插入其他情节或者描述性段落而延长或中断。在这个通行了超过两个世纪的准则下,连载作品就是一个精妙装置,它可以保证读者缓慢地阅读文本,充分地体会故事的微妙之处。后来的作家也认可这一观点:一九一〇年《北京新繁华梦》的序言将报章小说勾起的渴望比作酒徒对美酒的饥渴;四年后,徐枕亚提及报章小说时说:“日阅一页,恰到好处。此中玩索,自有趣味……若得一书,而终日伏案,手不停披,目无旁瞬,不数时已终卷,图穷而匕首见,大嚼之后,觉其无味,置诸高阁,不复重拈,此煞风景之伧父耳,非能得小说中之三昧者也。”⑤此处史料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作品以连载方式发表包含着阻止读者一下子通读全书、阻止读者瞬间进入几欲成瘾状态的阅读法则。这个历史时期选择了分期刊载的方式,它体现和表达了挫折感法则的叙述特征,由此也造就了“几欲成瘾”的形成。
许多中国和欧洲小说的研究者业已证明,以连载方式发表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读者遭遇小说的情形。首先,分期刊载使小说获得比从前更广泛的读者,因为读者最初的经济投入是非常少的。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言:“当报纸开始分期刊载小说,这对读者和出版商都是很经济的。对于读者而言,报纸——至少看起来是——比书或期刊便宜得多……全部的花费也许并没有不同,但是感觉却是不同的,因为每天的支出是那么地微不足道。当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理由购买报纸,阅读报纸上的小说就可以被当作一种犒劳”。①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51.即便买全一部分期刊载的小说花费不少,人们也会相信这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前一两回不好看的话,人们就不会花钱再继续买。同时,如果预期的读者群没有出现,关心利益的出版商就会在发行了前十回或二十回的时候提前终止。毫无疑问,晚清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小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化的时代,而报章小说常被视为这一商业化的代表。②这个商品化的进程在《玉梨魂》获得成功后加快了速度。见Link,第149-150页。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连载作品的推介同样伴随着对利益的关注。当代评论家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将通俗连载小说称为“工业文学”,其他的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和评论家在连载作品和卖淫之间看到了相似的联系。休斯(Linda Hughes)和隆德(Michael Lund)发现了分期刊载和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写道:“现在投资将来获利,并且持续增长,这样的假设和信心是中产阶级和阅读连载作品的共同特征。”③Linda Hugher,Michael Lund:The Victorian Serial,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1,p4.格兰维尔(Jean-Ignace Grandville)在一八四四年关于小报作家的漫画中生动地表达了这一点,这些作家被刻画成专门将文学作品切片出售以获利的人。
坚持连载作品带有典型的文体痕迹,这为许多关于十九世纪欧洲连载作品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模式,他声明成功的作家靠成行地出售他们的作品谋生,并且学会了修整情节以适应分期刊载的迫切需求。每一节的连载长度都必须适合报刊给定的版面,当然,也要将故事推进到一个新的充满悬疑和期待的阶段,以至于大结局的出现会挫伤读者的阅读激情。④Peter Brooks: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Narrativ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p147.陈平原赞同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文学的生产模式支配性地改变了文学形式,“记录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突破,都不能不或隐或显地影响文学形式的发展”。⑤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新的传播技术的确改变了旧小说的发表方式,也促使以前的手抄本出版。之前引述过的上海叙事是以石印或铅字印行的更早的白话小说,它们是首先被以新的连载方式刊行的。这些传播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向布鲁克斯和陈平原所说的那样也相应地带来文学书写的变化么?
二十世纪初叶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分期出版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作品的质量,无情地导致了作品水准的下降。因为急功近利的作家们只是每天或者每月把文字堆成一页,这些文字早上写成,下午排版,晚上就能印出来。作家们根本无暇润色修改,结果使整个作品结构混乱。梁启超是连载小说最早最坚定的鼓吹者之一,在世纪之交他自己也尝试了这种形式,不过很快放弃了。许多年后,他写道:“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初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⑥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81页。杨曼青也说:“每信笔一篇,无暇更计工拙。”⑦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81页。的确,即便像张恨水这样的名作家也充满同感地回忆说,强调写作速度可能导致小说整体结构的松散。
近年活跃的学者依然坚持,商业化是二十世纪初叶出版界一股核心的改变力量,他们始终强调分期刊载是一种新的、不经意的叙事方法的原动力。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对这种状况作了深入的解释:出版模式的“限制”(无论期刊还是日报)直接造就了一种新的松散的叙事结构。由于这段时间的许多小说是写一回刊一回的,他认为这样很难避免叙事线索的矛盾和叙述语气的变动。虽然每回可能是完整的,但合成一部则常常上下脱节或者前后重复。①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80-286页。不过,虽然在陈平原援引的许多二十世纪早期的小说中都能找到这种上下脱节和前后重复,但是在最值得关注的最先以连载形式发表的谴责小说中,这种情况却并不存在。②有些学者对陈平原关于谴责小说的研究存疑,虽然米列娜(Milena Dolezalova-Velingerova)(1980)和Donald Holoch(1980)并不着意考察出版形式的问题,但他们认为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这样的小说有着严谨的结构。事实上,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上海故事专注于人名、地名、时间、日期和都市空间关系,这些小说的结构显然比它们的明清前辈们更连贯更统一。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很以他的作品连贯统一而自豪,他坚信自己避免了重复、矛盾和“挂漏”。有趣的是,他发现写作的挑战不是源于发表的模式,而是未曾料到的复杂情节和大量人物。③“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人间地狱》的作者毕倚虹二十多年后写道:“小说文字以隽趣为工,不能不迂回曲折,点缀空中楼阁。”④毕倚虹:《人间地狱·序》,第13-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在《歇浦潮》的第二个序言中,朱瘦菊解释说:“惟读书当求其结构奇巧之处,若徒取情事之光怪陆离,而贪多务速草草读毕,以为茶余酒后之谈资,则殊辜负作者惨淡经营之精意矣。”⑤朱瘦菊:《歇浦潮·序》,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人们可以将作者的这些议论当作广告或者态度暧昧的声明而忽略它们,但事实是,这些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小说的确结构统一,组织严谨。
早期的以上海为背景的连载小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断地、有条不紊地点明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你几乎可以在当时的地图上找到这些小说中提到的街道,而悉心描述的有关城市特征的情节也总是清楚明白。时间标记受到类似的关注:《海上花列传》始于叙事人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坠入花海,跌到了上海的陆家石桥。韩邦庆写道:“花也怜侬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⑥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2页。在这部和当时另一部报章小说中,都自始至终标明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为整部作品提供了一个精细的时序结构。在中国早期白话小说中,具体的日期时常被引述,但是不符合时间顺序的叙述也非常普遍,一些评点者认为这些不一致是作者为了引导读者的有意为之。⑦例如姚燮对《红楼梦》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见Rolston(陆大伟)编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56-57。在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中就认为这个时序上的不一致是作者刻意的。张新之在他的《红楼梦》评点中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是对读者忽略文外之意的警示;其他评点者将这个“错误”当作暗示文本言外之意的信号:“如果作家依时安排这些三到五年发生的事件,那将不会有任何时序上不一致的问题,他的作品也就仅仅是西门庆家事的一份日常记录……于是作家故意将这些不一致插入时间顺序中。”(《如何阅读〈金瓶梅〉》,转引自陆大伟编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1990,p224。)相反,在世纪之交上海报章小说中,时间框架是凝固的,并且维持着内部一致。《海上花列传》在六十四回里讲述了八个月的故事,前一天的事情常常在第二天续上。《海天鸿雪记》中的大部分事件在三到五天发生,由于一些插曲,这个阶段总要从几天延至三两周,整个故事不超过五个月。⑧《海天鸿雪记》始于日期不确定的某日,大约距离四月初一不超过一个半月,终于七月初六黎明。在小说的前半部,时间总是记为“第二天”、“次日”,没有具体日期,但是在后半部,所有日期都被明确标识,毫无例外。《海上繁华梦》中,时间跨度增大,但小说经历时间跨度最大的部分是在第六十和六十一回(第二卷的结尾,第三卷的开始)。对具体日期,甚至是星期几的关注使哪怕最低限度的差错都不可能出现。⑨即便所记的两天被几周或几个章节分开,在日期计算和星期计算上仍然会保持一致。例如《海天鸿雪记》第17回,6月17日是星期五,在后来的第19回,7月3日就是星期日。
在这些和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中,对时间的标识也是空前的精准(精确到西方计时的一刻钟),叙事人或者直接告诉我们:“两人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三时”,或者人物自己听到自鸣钟报时,或者看看墙上的时钟。虽然自鸣钟或者金表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财富和精明的象征,但它们出现在文本中,主要是时间推移的标识,告诉读者时间是如何被切分的,督促他/她关注时间。在时间层面上的细节描述和不断重复提示我们关注文本中时间的意义,也标示一种新的关乎时间的美学原理,在此,不符合时间顺序的叙述不再被视为艺术技巧或阐释学线索的证明。
为什么这些小说中有着对时间和空间一致性的坚持?晚清和民国时期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的结构实际上远为复杂,它们比早些时候的白话小说更难以划分成一些离散的事件;在《海上花列传》的中点,就有超过一打的故事情节同步推进。然而,书中并没有出现我们预想中的上下脱节或前后重复,对早期连载作品进行惯常的描述如同草率而粗心的冒险。审慎而复杂的情节设计保留了从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二〇年代,从《海天鸿雪记》到《人间地狱》这些上海故事的规则。①见袁进对《歇浦潮》和《广陵潮》的对比(袁进:《鸳鸯蝴蝶派》,第128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魏绍昌在《歇浦潮》再版时的序言(《歇浦潮》,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以及胡适对《海上花列传》叙事结构的讨论(《海上花列传·序》,第578-579页,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83)。这个规则的一个特例是陆士谔的《新上海》,它的情节结构更接近谴责小说而非这些上海叙事,《新上海》也许没有作为连载发表,也从未被后来的作家当作典型而引述。虽然报章小说对时间和空间的精确描绘明确地将我们引向计时和绘制地图的新技巧,但如此精确的计量首先是由叙事技巧形式上的需要推动的。如同一个繁忙都市的铁路系统严重依赖分秒不差的开关、信号和衔接,以此证明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变得一团糟,坚持认为应该叙事多样化的小说事实上需要精细协调的时间,以便使叙述从一个故事过渡到另一个。
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被标记为复线叙事,那是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复杂的新顺序;人们也许会假设一部长期分段刊载的小说不能变得太复杂以不失去读者。然而,正如埃迪克(Richard Altick)指出,连载小说可以让读者在等待下一回,猜测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重读前面的章节。②Richard Altick:“Varieties of Readers’Response:The Case of Dombey and Son”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10:70-74,1980.陈平原认为,“记录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变影响了文学形式的发展。然而,反过来说也许同样正确。做一个类比,在摄影术的历史中,广泛使用的暗箱要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照相机的真正发明早许多年;在电影的历史中,对投射影像的兴趣和运用活动照相法捕捉随时的运动变化,要比卢米埃尔兄弟发明活动电影机早几十年。视觉和文本的风格与技巧也许偶尔简单地反映出作品模式的变化,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亦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延迟的反应,甚或至于一种文体变革预示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辩证关系。
虽然报章小说在段落中间断开,早期平版印刷的插图看上去也很粗糙,但评论家和学者将这些与作品技巧不相称的美学形式融入艺术发展史却是很正常的。这种观念始于文学变化从属于技术变革或社会发展的假定,除非顽强的传统暂时将其中断。然而,在对晚清报章小说的学术争论中,“传统”总是被理解为一套至关重要的结构成规,报章小说借此熟练地大批量生产以飨读者。从胡适开始,学者们从明清白话小说的形式特征来理解报章小说获得认同的原因,他们发现章回体与报章小说珠联璧合。明清章回体小说在每一回末给读者留下悬念,告诉他们“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报章小说可以使用这种开场和首尾的典型模式,在一段后面留下悬念,让读者继续购买下一段。在报章小说中,每一段都会有个小高潮,同时会设下个小圈套,引导读者进入下一段。
不过,两部最早的以回为单位连载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和《海天鸿雪记》并未使用这种成规。③《海上花列传》是以两回为一个单位连载,《海天鸿雪记》是一回一个单位连载。相反,每回以“按”开头,以一个简单的声明“本回完”结束,这样更有文学味,其意义接近于“记录”。每回的最后一句话没有提出一个读者在下一回将得到答案的问题,下一回的第一句也如人们所料那样仅仅是简要重述前一回的结尾。最早的每回都以“话说”开篇,以“且看下回分解”收场的报章小说是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它从一八九八年开始连载。由于不管故事的断点在哪儿出现,日刊一页的规则都被严格执行,因而这些习惯用语明显是用于修辞而非实用目的。在这些文本中,人们发现无论“页”还是“回”都不能作为小说时间分割的“自然的”单位。
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儒林外史》在文体方面的启发性,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研究长篇小说的学者也肯定《儒林外史》为另一种复杂的小说叙事的产生提供了技术资源。这些学者并不认为早期小说和报章小说之间有一条夸张的裂缝,相反,后者是前者毫无疑问的继承者。然而代际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儒林外史》通常被视为短篇故事的连缀。①后来的批评家常常重复鲁迅这种用贬损的辞藻表达出看似中立的评价,例如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这种对小说结构的描述事实上并没有看到最为重要的文体意义:每条叙述线都精妙地让位给另一条,以至于我们无法在文本中指出具体的转换点。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将《儒林外史》当作一个故事集的理解的确突出了叙述的单向性。一旦一个人物退出了舞台,除非作为配角,他/她将不会再出现。还有,整部小说每隔几段就会出现转接点,给人们的感觉是每段故事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海上花列传》和其他上海故事的叙事变化非常频繁,每条明显的情节线在充分发展之前就被另一条所打断。《儒林外史》和晚清上海故事之间重要的结构差异便是:在前者中,一段让位给另一段;而后者则是多条情节线一一成型,然后交叉、分离,最终再聚合到一起。②胡适在他1926年《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指出这一点,曾朴在区分《儒林外史》和他自己的《孽海花》的结构差异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二十世纪早期的小说声称展现宽广的社会风情画,虽然它们公推《儒林外史》为鼻祖,也将多条情节线贯穿于整部作品,但实际上它们更接近《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和《海上繁华梦》。
于是,我们发现世纪之交的文本,比如《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海上繁华梦》及其一九一〇和一九二〇年代的类似文本引发了晚清和民国报章小说数量的激增。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小说上下脱节或前后重复,但是它们的结构非常精妙连贯。它们似乎是吸收了此前小说“片段式”的结构优点,但却明显地放弃了那些看上去更自然的习惯用语和成规。然而,事实是这些小说既有连载作品的物质形式,又有长篇白话小说在更深层面上的美学原理,暗示了文学形式与当时社会条件之间复杂却明确的关系。
在借助报章小说实现上海城市的文学想象的过程中,同步(simultaneity)、中断(interruption)和过量(excess)是三个关键的文本处理方式。
如果我们回顾安德森在民族主义的形成中的追问——他将报纸和小说看作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时间关联——就会对复杂的上海故事在作为连续共同体的城市想象中扮演唯一的占绝对优势的角色毫不见怪。安德森对小说的兴趣在于小说能够制造出同步感,多个情节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③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ed.London:Verso 1991,p22-36.上海小说大多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许多人物同时做不同的事情,也表现在全部情节线(它们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出现,各不相关,却在后来证明是相互关联的)在整个故事中同时推进。韩邦庆认为这种复杂性是他“穿插藏闪之法”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随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④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2页。“穿插”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叙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海上花列传》第三和第四回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回中有八条不同的情节线展开却无一终了。前几回中的穿插一直贯穿在整部作品中,的确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为大量上海报章小说沿袭了四十多年的叙事结构。
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就以同步性和多样性为标志。不像其他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系列,首创者会产生或多或少、有序的、一代代的模仿品,《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海上繁华梦》这些上海小说几乎同时出现,随着分期刊载的出版方式同时推进。比如《海上繁华梦》始刊于一八九八年,比《海天鸿雪记》的首刊早了差不多一年,但它在后者收尾之后若干年还在随写随刊,《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和其他早期上海小说大都在两年内同时刊完,《九尾龟》在《海上繁华梦》临近终了的时候开始刊载。这种发表时间上的部分重合或者同步刊载的状况在一九一〇年代后期和一九二〇年代再度出现。《歇浦潮》、《上海春秋》、《人间地狱》和其他长篇小说同时每日连载。这段时间,即便同一个作者也可能同时创作许多不同的报章小说:在陆士谔的《新上海》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小说家,他的书房里散落着不同故事的待完稿。
由于小说分段刊载,也由于小说与日报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报章小说同时生产,也同时被消费。以上海小说为例,分期刊载使这些小说完完全全与读者同步,也使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其他众多的读者同步。正因如此,安德森所说的报纸生成的想象共同体的范围和消费量得自于报章小说的发行和消费量。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一个事实,世纪之交的上海叙事,包括日刊一页的《海上繁华梦》会因为版面的原因而突然中断,即使这个断点处于一段情节的中间,人们因此会推断这必然造成一种片段式的不连贯的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海上花列传》,会发现作者对这种“中断”早有准备,并且利用这种“中断”来结构情节。《海上花列传》没有以每两回为一个单位结束或者开始一个事件(这部书半月一刊,每次刊两回),而是常常在这两回中间中断一个事件,韩邦庆称之为“藏闪”。“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言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①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2页。“藏闪”的技巧让我们想起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叙述中交切(intercut)的讨论。有时,读者想要的信息在一段或两段内出现,但是有时候它们出现在读者形成这个问题的十多回之后。无论如何,不断地“中断”保证必要的信息不会立马呈现。
这种频繁“中断”的“藏闪”之法对应的是我刚才提到的“同步”。“同步”在某种程度上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由于叙述本身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快速地在情节线中来回剪切是让读者在单向度的文本之外同时展开多向度阅读的必须。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上海报章小说特别适用了这一技巧,说服读者相信许多不同的故事在这个复杂的大都市里同时上演。
这个阶段的报章小说迫使它的读者从一条情节线跳转到另一条情节线,同时也迫使这些读者在不断被报章小说打断的日常生活之间跳转。欧洲的学者时常提及连载小说将其每期刊载的故事融入读者日常生活节奏的力量,正如林培瑞所言,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日闻”总是能被带进与之并列刊载的报章小说中。③Perry Link,1981,p22.与此同时,例行的连载小说介入日常生活,可以让读者们或者从沉闷的生活中感受故事中的“忙”,或者从每日的压力和紧张中享受一下“闲”。当上海居民日益关注“消闲”和如何“消闲”时,报章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就绝非偶然了。
在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中,他认为聚焦于妓院的小说(大多以上海为背景)“翻新了传统浪漫文学与情色小说的欲望叙事学”,④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71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并且延续鲁迅对此类“狭邪小说”的评价,将其特点定义为“过量”。“过量”表现在三个方面: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有众多的浪漫的情色关系;这些故事流于“溢美”或“溢恶”;这些故事都非常长。我们也许还能加入另外一点:“欲望”,不仅每条情节线中的人物滥情,而且操纵着读者不断地消费这些相互缠绕伸向无尽远方的情节线。《海上繁华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孙玉声本打算写三十回,但是很快加到六十回,一百回,然后又续写了一百回。这不仅是对读者要求的回应,也是对钱包的回应。这两个一百回后,孙玉声继续写与此主题相关的上海小说。即便如此,《海上花列传》再版也超过九次。这种“欲望”不仅引起道德上担忧,也带来了美学上的问题,《海上繁华梦》由此上演了一出道德性与世俗欲望的较量,而后者远比人们所料想到的更为强有力,因为它不断地违背作者此前的声明,不断地续写。由是,问题不仅仅是读者“不应该”读得更多,而是他们“不能”读得更多——直到下一回刊出。这便是终点如何变成了没完没了的需求,含糊不清的欲望如何被明确为一种“瘾”的原因。
本文指出一八九〇到一九二〇年代以上海为背景的报章小说必须被看作严肃的有着独特美学原理的文学作品。这一原理关注叙述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不断地被“中断”,以及读者渴望读完全文的挫折感。当“现代”还未成为知识分子的焦虑时,其症候已经显现:不断增长的速度、范围和复杂性;飞快地令人迷茫的情节跳转;绝对的同步与感觉上慢半拍的对立,上海的报章小说由此提供了一个“上海是什么”的文学想象。此外,通过报章小说,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类型得以呈现,消费这些文学商品的具有上海“瘾”的读者群受到关注。而且,借助其特点,一个新的“民族的”印刷业和视觉媒介的竞技场也即将发展壮大。
*此文原载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62,no.3(August 2003)781-810。译文经作者审定,略有删节。
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校区东亚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