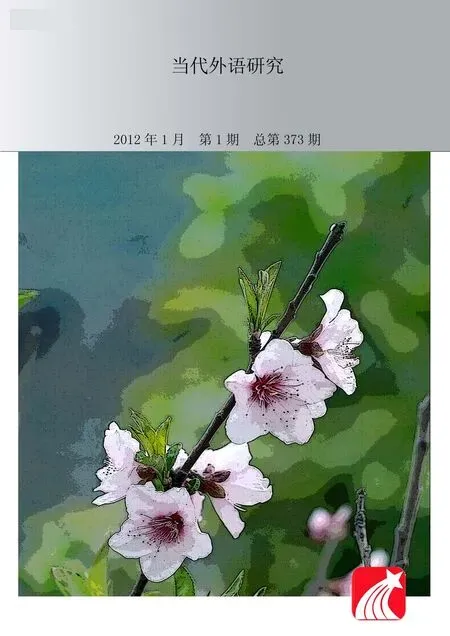应用翻译学构想
2012-04-01黄忠廉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历经三十年,翻译学在中国由无名无位升为三级学科,如今又升至二级学科,与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终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这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应用翻译学升为独立学科带来了曙光,加快了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
1. 应用与应用翻译学
黄忠廉和信娜(2011)将“应用”厘定为“满足使用或运用之需”,与应用翻译相对的是文学翻译。对“应用翻译理论”我们作过三种切分:第一,应用翻译/理论,即应用翻译的理论,是由应用翻译归纳出的应用翻译理论;第二,应用/翻译理论,即翻译理论的应用,是由基本译论演绎出的应用翻译理论,又可分为基本译论用于翻译实践的学科内应用,基本译论用于译学之外其他领域的学科外应用;第三,应用/翻译/理论,即理论在翻译(学)中的应用,是其他学科理论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而嫁接出的应用翻译理论。
应用翻译学的性质据之可界定为:研究应用翻译,译论用于各种实践,其他学科理论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规律的学科。
2. 特定的构想背景
对翻译学的建立海内外历来臧否不一。国人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上早于国外,“1927年,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横空出世,在广漠的学海上空划出一道闪亮的光芒”(方梦之2011:前言)。1951年董秋斯撰《论翻译理论的建设》,断定“翻译是一种科学”(罗新璋、陈应年2009:601-609)。1988年黄龙出版《翻译学》,其“出版者的话”交待: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科学,包括基础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三个部分。在应用翻译学方面,主要阐述了翻译实践理论和译才培养理论,涉及同声翻译、科技翻译、机器翻译、翻译技巧、翻译教学、译误分析和翻译人才的专业训练等。2000年谭载喜推出《翻译学》。尽管译界有人质疑“翻译学”能否建立,但整个学科研究的力量日见增长,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日趋成熟,如2000年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问世,2004年黄忠廉和李亚舒的《科学翻译学》出版,而后者有力地推进了应用翻译研究。
国外较早提出应用翻译学思想的是霍姆斯(Holmes 2000)。1972年他在翻译学体系中提出了应用翻译学雏形。之后,具体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在持续,但学科思考处于停滞状态,学科建构之声渐微。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新见迭出,如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刘军平2009),为译事提供了诸多解释视角。由于译学研究转向过快,定点不多,植根于应用翻译本身的理论并不多见,仅法国释意派理论之类较为突出。这些学派更多是从翻译外围论翻译:为何译?为谁译?译为何?西人坐而论道,金针何以度人?何为译?如何译?他们越来越不关注。他们要抢占的是“道”的高地,“技”的丰富暂无暇顾及,或认为已了无价值。
建国后,实用翻译虽占译界主体,但文学翻译仍是译学界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十年,译论研究的主流对象仍然未变。诚如我国第一套“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的策划者郑艳杰所言:“八十年代以来,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旅游翻译、口译、网络翻译、汉外翻译等在中国相继争相成为译事的急需或重点,文学翻译因此痛失惜日辉煌,频感生存危机”(方梦之2011:345)。八十年代,国内开始重视科技翻译研究,但重在技巧。而近二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接踵而至,译界眼界大开,研究空前活跃。各大刊物一度抢占理论高地而荒芜了脚下的实践土地,导致根基动摇;“只有纯理研究才算学问,而应用研究算不得学问”的看法曾经流行,大量亟待解决的应用性课题一度被人忽略。现在译论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引介西方译论、借他山之石抓基础研究、做逻辑推理的同时,紧扣时代和实践、贴近现实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当下之中国,只有将应用研究推至重要地位,才能服务于国家文化兴国的战略,同时为翻译学注入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并不否定翻译理论研究的宏大叙事和宽广的视野,纯粹理论可由少数人研究,只是希求它立足于应用与实践,唯其如此,才能既腾空飞行,又畅行大地。
重视应用翻译理论研究是对此前翻译学研究紧追西方的一次反思与校正。此前十几年,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介、消化国外译论新理,国外各种译论在中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繁荣了一阵。中国译学界现在开始由沉寂期进入反思期,这成了应用翻译兴起的逻辑起点。中国译学界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研究中国的翻译现实,在文学翻译失落的当下唯有应用翻译才可成为译学界首当其冲的关注对象。在翻译理论研究越来越广泛,翻译学整体及其分支学科纷纷建立的形势下,翻译实践面最广、最具现实性的应用翻译及其研究更有理由受到学科的关注,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3. 独特的学科定位
谭载喜(1988)对翻译学持三分法: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这一划分有问题,不能成立,因为“普通”与“特殊”相对,“理论”与“应用”相对。从学科层次看,应用翻译学是相对于理论翻译学而从普通翻译学里分离出来的。“理论翻译学”研究翻译本体,属于纯理研究;“应用翻译学”研究翻译实践和译论实践,属于应用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划分,翻译学可分为普通翻译学和特殊翻译学,前者探讨翻译共性问题,后者研究某领域的翻译活动,据此应用翻译学可归属特殊翻译学。
任何学科,其本体理论研究极其重要,含混不得,否则不仅无助于学科的建立,更会影响实践应用的质量。尤其是在实践应用领域,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是不可取的。其实,应用翻译学的独立不仅可以独善其身,更会反哺理论翻译学。在密切联系应用翻译、解决翻译实践问题的同时,它还兼负着发现问题、由其特殊性揭示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重任,对应用翻译及其研究的概括能推动理论翻译学向纵深发展。与本体理论研究相比,中国乃至全球的应用翻译学研究非常不成熟,有的应用理论或未完全从本体理论中分离出来,或寄于本体理论的篱下,令人信服的体系性应用翻译理论还不多,留下了不少开发的领域。因此,应用翻译学的独立是一种理论自觉,有助于自身的发展。
由此可见,应用翻译学源自翻译学,是翻译学的分支,以独立学科身份与理论翻译学共同构成了翻译学。就翻译学整体而言,翻译学缺乏本体研究会“失魂”,缺乏应用研究则会“无根”。人类探索理论的宗旨无非有二:穷究于理,成就于工。前者可满足人类的求知心理,后者可保障人类更好地生存,归根到底是为了后者。因此应用研究不仅是土壤,更是归宿。
4. 特有的研究对象
明了应用所指和应用翻译学的内涵,结合其产生的国内外语境,就可以确定其特有的研究对象了。应用翻译学研究三个层面:核心层研究应用翻译,中间层研究基本译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外围层则研究其他学科理论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以及译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三个层面涉及如下四个研究对象,前二者是应用翻译的本体研究对象,而后二者是针对翻译或翻译学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关系的研究。
第一,应用翻译。翻译首先是一种专业技能,应用翻译更是实在的技能,是一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精神活动。因此,“翻译必然是实践指向的,是注重应用的,是通过大量实际操作体现其价值并完善其品质的”(罗进德2007)。应用翻译当下和未来都是中国乃至全球翻译研究的第一要务,翻译学理所应当地将其放在理论研究的第一位。
但凡能指导实践的翻译理论,都是从应用翻译中产生的。没有理论指导,应用翻译的水平也会低迷。比如近来年,人人似乎可以操笔从译,却惊呼高质翻译人才奇缺,这就与翻译教学有关:编不出高质教材,无成型的教学方法,缺乏优质师资,等等。究其因,都与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之一的翻译教学研究水平密切相关。
第二,基本译论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应用翻译学最大的特点是应用,但非一般意义的应用。由上可知,它同样要总结规律,拥有自己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同时,它还存在许多空间有待翻译学基本理论去实践,去试验。反言之,许多基本译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应用翻译领域,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把一般性理论转化为特殊性理论,再把特殊性理论转化为个别性理论,这样才可促进基本译论的普及与应用。
还有人认为应用翻译研究无价值,无理论,只要把基本译论直接移用于实践即可,实则不然。比如,翻译批评如何开展?翻译批评标准是否等于翻译标准?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能直接用之来操作吗?翻译批评研究不够,缺乏稳定的翻译批评队伍,翻译批评发表园地不够,导致翻译批评无力,劣质译作就会充斥市场。
第三,其他学科理论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翻译学初建,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它广纳四方理论源泉,这方面西方翻译学者走在了前头。其中有一批学者,他们出身“非行家”,并非完全埋头译事译论的专家,如尼采、本雅明、德里达、海德格尔、奎因等哲学家成名于本学科,善于将其成果转用于译学,开疆辟域。这类学者中“有的善于科普,有的只是输出术语,略显艰涩,生吞活剥者也不少见。入主译坛而献身译学者少,旁逸斜出敲边鼓者多。这种引入式理论研究有自发的,也有将就的;有的赋予译事科学的解释,有的完全可当作戏说,甚至是妄言”(黄忠廉2010)。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也有了良好的开端,如语言学、美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不断渗入,国内的翻译学研究因此而多彩,为翻译学研究滋生出了众多学科触角,而这正是应用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第四,翻译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翻译学为何成不了输出学科?翻译学如同任何一门新学科,在成长过程中吸收了众多学科的养分,现在以及将来它会逐渐成为一门输出学科。比如研究翻译转换过程自觉不自觉地用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若冷静反思一下,乔氏研究的是语内转换,而翻译是语际转换,语际转换难道不能为语内转换提供另一个思维视角吗?顺此再思,语际思维转换难道无助于任何产生于单语言的心理学理论、认知科学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拓展吗?有学者认为,译介学挽救了比较文学,实不为过。谢天振(2011)就认为翻译研究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比如:翻译研究者对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外文学交流、传播、接受和影响的全景图,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为当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文学经典等热门话题的讨论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等等。再如变译理论讨论语际的变通式翻译,可为单语的变通式写作(如摘写、编写、缩写、转写、综述、续写等)提供理论资源。
5. 独特的中国气派
只要我们持平视西方、俯视中土的清醒的学术心态,应用翻译学会有助于翻译学研究形成独特的中国气派。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突出汉外特性。一直有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除将中国哲学等用于译论研究外,其实最大的中国特色就在于应用翻译研究,因为理论翻译学追究语际翻译的共性,应用翻译学则追求特性。林林总总的具体应用翻译领域且不说,仅汉语与任何一种外语,尤其是与任何一门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翻译就足以代表人类翻译的特性,藉此可以从根本上揭示人类翻译的共性。可见汉外应用翻译本身就烙上了中国印,汉外特色与生俱来,相应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自然就含有了中国气派。而要彰显这一气派,需要我们顺势而为。
第二,植根中国本土。源于亲属语言之间的种种译论只能供中国借鉴,本质上不能书写中国的翻译学主体。要建立中国的翻译学,不能依托翻译学的外围研究,必须注重翻译学本体。要振兴中国的翻译学,更不能寄望于对国外翻译学的模仿,而必须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翻译实践,要有问题意识,要研究中国的真问题;过于依从二“外”,有可能导致对本土应用翻译这一独特对象的忽视,而忽视研究对象无异于自毁学科生存。
第三,发扬中国传统。应用翻译学的中国气派还在于念兹在兹的中国学者受到了“经世济民”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潜移默化。中国学问从来都是密切关注应用的,它源于应用,又归于应用。注重事实,尤其是汉外互译的事实,正符合乾嘉学派以降的朴学传统。当今翻译学者多数了解西方研究,若能立足于中国丰富的应用翻译实践,融合西方译论,中国气派也就可以自然天成。
Holmes, James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Lawrence Venuti (ed.).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72-185.
方梦之.2011a中国译学大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方梦之.2011b.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黄龙.1988.翻译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黄忠廉.2010.“围城打援”:当代西方译论的景观[N].光明日报(7-14).
黄忠廉、李亚舒.2004.科学翻译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信娜.2011.应用翻译学构建论[J].上海翻译(2):7-10.
刘军平.2009.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罗进德.2007.刘宓庆译学著作全集代序[A].刘宓庆著.文体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董秋斯.1951/2009.论翻译理论的建设[A].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601-609.
谭载喜.2000.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2011.冲击与拓展: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关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6-28).
郑海凌.2000.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