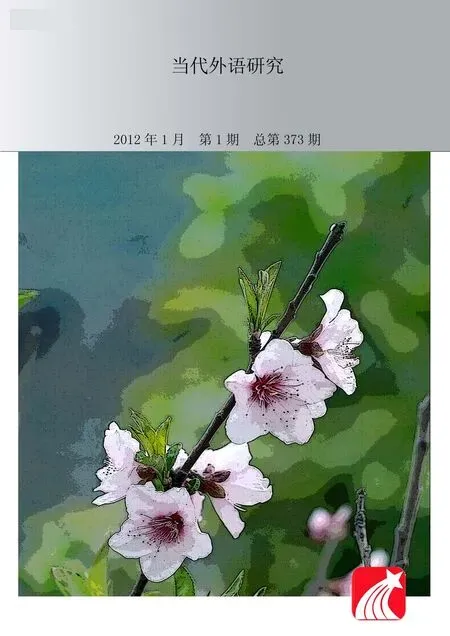中国学者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道
2012-04-01潘文国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在庆祝程雨民先生85岁华诞暨语言研究成就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为程先生献上了下面这首诗:
字基初展汉文枢,
人本还昭语学途。
只道西山采药去,
谁知东海得骊珠。
诗中“字基”指的是2003年出版的《汉语字基语法》,“人本”指的是2010年出版的《“人本语义学”十论》。“字基”是国内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重要的“纯”汉语语言学著作;“人本”则以汉语为例,提出了人的意愿与语言系统互动这一崭新的以人为本的语言学理论,在普通语言学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两部书,加上1997年出版、2011年修订再版的《语言系统及其运作》(其中提出了“语言是导向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程雨民2011:47)重要观点),实现了程雨民先生从一个单纯的外国语言学学者向普世语言学学者的重大转变。程先生的转向和成功,对于国内从事外国语言学(暂且用这一个术语,其实已有许多学者指出这个术语是不妥的)的学者来说具有方向标的作用。它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迫使我们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1. “外国语言学”研究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国内的学科体系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而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又设立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从制度上提出了语言学的中、外之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和批评,来自外语语言学界的反对之声尤其强烈,认为把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外国”语言学的研究,不利于他们介入汉语的研究。这诚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学科的设立从来只是为了便于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分工”并不意味着“分家”。语言学从本质上来讲确实没有中外之分,研究语言学更不应局限于中外之分,学科的分设在名称上或有未妥,但其本意也许只是为了强调两部分人的研究侧重点,而许多人却株守这一名称之分,画地为牢,自我拘禁,不仅自己的研究从不跨出畛域半步,甚至禁止别人跨出。君不见许多外语院系领导不许教师撰写涉及汉语的论文,一些“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硕士点的导师更禁止学生选择研究汉语的论题,否则就要指为“异端”、不务正业。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应该明白,任何语言研究,即使是最“普通”的人类语言研究,都是从母语开始的。有的语言学家如乔姆斯基等更提出从母语出发就可以达到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认为普通语言学研究可以不管母语、甚至有意无意地排斥母语、歧视母语,这种情况大概除了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挟外以自重”在中国造成的实际结果是所谓语言学研究就是外国语言理论的翻炒,今天流行这一派,一窝蜂地全搞这一派;明天一个新理论“引进”了,一窝蜂地又转向另一派。表面上热闹非凡,实质上全无根基,因为西方语言学理论是植根于西方的语言实际的,往往是“印欧语特色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在外语上既无法达到西方说母语人的语感,又自动放弃了母语的阵地,最多不痛不痒地举几个似是而非的例子,于是就只能跟在西方理论后面追、围着西方理论转,除了做到了“跟西方理论接轨”,所谓“赶上并超过西方语言学”、所谓“要对世界语言学研究”作出贡献,全是一句空话。
而程雨民先生的实践和成就启发我们的第一点,就是“外国语言学者”必须认真考虑本学科研究的目标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中国的“外国语言学”学者研究的正道?程先生的回答是,从汉语出发,借鉴外国语言理论,解决汉语研究的理论问题。我们是这么思考的吗?
2. “两张皮”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先生尖锐地提出了对语言研究“两张皮”现象的忧虑(吕叔湘1980/1992:13-14),后来许国璋先生、王宗炎先生等也多次谈及这个问题。钱冠连先生(1999)和我本人(潘文国2001)也曾撰文论述过这一现象的由来与对策。但是几十年来,这现象并无根本改观。当然从实际来说,现在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子的语言状况与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已有所不同,中文学者的外语能力比以前有不少提高,特别一些在海外、或者“海归”的中文研究者多数已有了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在论文中完全不举中文例子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但为什么人们的感觉是“两张皮”现象依然故我?我认为是因为在更高的层面上两者缺乏交融。所谓“更高的层面”一是指理论层面,二是指语言的深层。
在理论层面上,虽说有研究汉语和外语的不同,但其背后的理论都是西方语言学,那些在海外搞中文研究的多数人尤是如此,因此总觉得跟真正的汉语研究隔了一层,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过是在拿中文的例子讲外国语言学。而语言的深层尤其是汉语的深层存在于文言里,“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在经过几千年发展而成熟的文言里存在着汉语组织的根和基因。而现在的语言研究者大都文言阅读能力甚差、古文根基毫无,因而他们对汉语的感受往往是皮毛的,对“语感”的解释也往往是浅表的。“外国语言学”研究者尤其是如此,“外国语言学”学科的设立更可能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一批人安于脱离母语搞隔空的语言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指望能在汉语实际的基础上实现语言理论研究的突破呢?另一方面,一些对文言以及传统汉语研究有涉猎或浸润的人则满足于关在自己的书斋里搞他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不懂也不想懂窗外风起云涌的语言理论风景,因而理论上自然也不会有突破。一些“现代汉语”学者对传统既缺少继承、对外文也一知半解,对创新中国气派的语言理论也只能说是有心无力。我们要问:只懂中文、甚至只懂“现代汉语”的人能称“语言学家”吗?只搞西方语言学、母语反而搞不清楚的人能算“普通语言学家”吗?
程雨民先生的实践和成就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语言学家,在普通语言学领域真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学者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基础,除了对西方语言学了如指掌以外,还必须娴熟自己的母语,特别要对文言有所感受。在程先生的研究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他花了不少工夫专门研究了古文诗词甚至是骈文的组织结构及语言规律,这是国内的外语学者甚至汉语学者甚少关注的,这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的成就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3. 如何正确对待国外语言学?
如何对待国外语言学,包括几千年的西方语言学传统和近几十年层出不穷的创新理论?这是每个中国语言研究者必然会碰到的重要问题,“外国语言学”研究者尤其需要时时把这个问题挂在心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非常强调“批判地吸收”,对来自西方的语言理论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引进之前先要批判一下,“消消毒”。这样做有好处,使我们对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对某一理论的长短优劣、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多少有些了解。当然也有不足的,例如常常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未审先判地戴上个“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帽子(如对高本汉、叶斯柏森、特别是沃尔夫的批判),而对来自苏联的语言学见解包括对汉语的粗暴定性却是照单全收。但是文革以后的三十多年来,这句话却听不大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文革以前的西方理论都还需要进行精华和糟粕的两分,需要去粗取精、择善而从,文革以后的西方理论都只有长处没有短处、只有普适性没有局限性、只有真理没有谬误,只要“持续不断地引进”,就能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甚至中国自身语言学的建立?目前在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有多少人在从事“批判地研究”?有多少人只是在心安理得地做外国理论的传声筒?我猜想文革前后的“引进”之所以表现出了这样的差异,可能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文革前引进的都是二手货,是转手贩卖的,跟外国学者本人没接触、不了解,批判起来不会心疼,肯下狠手。而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理论往往是直接的,是国内学者出国留学直接从外国导师手中学来的,出于对导师的敬畏和中国人一贯的礼貌之道不敢提出与导师不同的看法,更不要说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我上面说的原因,出国留学者在外语上天生低人一截,而对汉语母语从根本上说也不甚了了,因此在“不敢”之外,还加上“不能”,就是导师鼓励他提,他也提不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从程雨民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答案。这就是:第一,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先进”的理论都只能反映局部的真理,没有包打天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每一种新理论来说,创新和局限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因此一定要学会一分为二,对西方理论一要学习,二不能盲从。第二,要有底气。底气来自对理论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语言的透彻了解,事实上,母语既是产生自己语言理论的温床,也是检验外来理论的试金石。只有对自己母语没有底气的人才会在外国理论面前束手就范。第三,要有勇气。要敢于在自身语言实际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理论的短长,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我想这是程雨民先生的成就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钱冠连先生(1999)曾经提出过一个“启功模式”,我想对程先生也同样适合:“所谓启功模式,是指母语为汉语的学者对国外语言学在汉语中的创化的心态、方式和思路。”“一是敢发疑问。二是大胆设想。三是走自己的路。四是敢负责任。五是再思。六是要有理论勇气。”
4. 如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真正结合,发展中国语言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的今天,建设、发展中国特色语言学的问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有愿望和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是两回事,中间要经过许多步骤,包括进行理论上、实践上和心理上的各种准备和积累。在我看来,心理上的准备是第一位的,不抛弃崇洋媚外思想,不放弃牵中就外的思路,中国语言学就不可能有自立的一天。精神上自立了,学术上才有可能自立。而另一方面,学术上的自立不会因为精神上的自立而天然来到。我们还要做几件刻苦踏实的工作。
第一是认真钻研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外国语言学”研究者,学习、了解国外语言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但这种学习必须是全方位的、全面的、深刻的、知其所以然的。阅读程雨民先生的著作,我们惊讶于他对西方语言学乃至语言哲学的娴熟,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从乔姆斯基到韩礼德,从奥斯汀到格赖斯,从康德到塞尔,他几乎是拈手即来,如数家珍。这使他对西方语言理论、语言哲学思想抱有一种全局观,不会轻易盲从。而我们有些研究者却喜欢从一而终,一头扎进某一派理论就再也不愿或不能跳出来。这样他即使对外国语言学,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此作为某外国语言学流派的中国代理是可能的,作为建立中国语言学的基础却是无望的。
第二是真正了解汉语和汉语研究传统。新的中国语言学决不可能在外语和外语研究传统上建立,而只能在自己语言的实际和自身语言研究的传统上建立。这是常识。不承认这一点不是无知便是偷懒,害怕作艰苦的努力。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语言研究者而言,最大的困难已不在于学习、了解外国语言和外国语言学,而恰恰是在了解本国语和本国语言研究传统,特别是将它们放到今天的语境里来重新理解。对此我们要付出甚至比学习外语更艰苦的努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准备呢?在这方面,又是程雨民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以他那一辈人,对传统的熟悉要胜过我们本来就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程先生竟以七八十岁的高龄,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论,以探究中国语言的特点,却是既出人意外,又是发人深省的。
立足本士资源,借鉴外来新知,这是发展、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要创造出新的语言学理论是一句空话,但有了这两个条件也不等于必然能创造出新的理论,这还要看各人的努力程度和悟性,乃至灵感。悟性和灵感以前常被斥为唯心主义,其实这是创新思维少不了的。爱因斯坦就很强调这点。语言学界,过去100多年中,具备上述两种条件的人并不少,但能作出创新成绩而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并不多,如马建忠、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张志公、许国璋、徐通锵等。程先生的成就令我们刮目相看,对其理论的价值我们也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评述。我并不是说程先生的理论已经非常完美,甚至我个人也并不完全赞同程先生书里的每一个说法。我只是强调他的书里有很多新东西,新得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认真研究的东西。程先生的书出版有的已有些年了,但对它的评述并不多见。其原因据我的观察,出身外语界的是“不敢”,出身汉语界的是“不屑”。搞外语的看到是研究汉语的著作,避之唯恐不远;搞汉语的看到外语界的人居然也来谈什么汉语,未看心里先已排斥。我认为这都是不正常的,这正是“两张皮”在新形势下的表现:有人缩手缩脚,不敢介入对方领域;有人宁肯自己无所作为,也排斥别人进入自己的“领地”。这两种心态不去,搞中国语言研究和外国语言学研究的人不能形成一股合力,要建设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
我那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只道西山采药去,谁知东海得骊珠”,说的是程雨民先生从西方语言学着手(“西山采药”),但其最终开花结果却是在东方、在中国,在东海“探骊得珠”。这条成功道路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程雨民.2003.汉语字基语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程雨民.2010.“人本语言学”十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程雨民.2011.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1980/1922.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A].吕叔湘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2-27.
潘文国.2001.“两张皮”现象的由来与对策[J].外语与外语教学(10):34-35,37.
钱冠连.1999.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J].外语研究(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