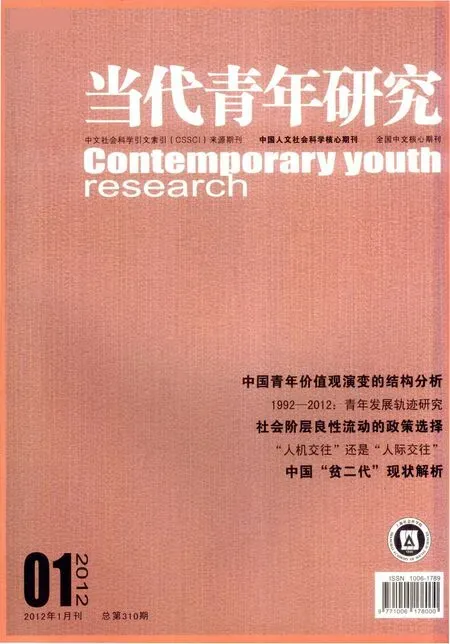偶像的黄昏
——再看网络“犀利哥”
2012-04-01彭光芒
钟 颖 彭光芒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新闻中心)
偶像的黄昏
——再看网络“犀利哥”
钟 颖 彭光芒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新闻中心)
“犀利哥”是去年网络中红极一时的草根偶像,通过对该偶像产生机制的剖析,回头审视这个被制造的网络偶像,流行文化中偶像制造和偶像幻灭的快餐机制值得我们思索,传播过程中“犀利哥”本体的缺位体现了娱乐精神下某些人文关怀的散失,揭示了一些网络活动的参与者走向没落境地。
偶像;广场狂欢;符号;后现代
一、笑中解悟流行文化 :被偶像的“犀利哥”
随着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凤姐等一大批网络公众人物出现在网络上,网络偶像或者说恶搞的网络偶像大家已经屡见不鲜,本文关注的正是去年流行一时的“犀利哥”,一年时间过去了,“犀利哥”正逐渐地被人们淡忘。当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和过来人的身份观察“犀利哥”时,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偶像制造和幻灭的轨迹。“犀利哥”由某一摄影爱好者偶然发现,拍摄成照片后上传到网络,其邋遢但颇有戏剧味的着装被网友纷纷评论,这个议题得到网民群体的认同后,人们以自己兴趣偏向解读“犀利哥”。[1]一时间“犀利哥”成为了网络当红人物。网民的嬉笑怒骂无不投影到草根偶像“犀利哥”身上,在这场带有某些后现代特质的广场狂欢中,追随者声音如过江之鲫,而很少有人思索“犀利哥”被“偶像”的特质。
谈及“犀利哥”被偶像的实质时,除了网络群体的推动外,还有媒介本身的外驱力,这种固有动力是由大众传媒的机构特性与传播特性决定的。[2]由于长期以来政治和伦理的压抑,媒介监控社会的功能被削弱,被压抑的群体积聚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潜意识,一找到合适的机会,被压抑的社会潜意识流便如同火山喷发,本我人格是按照快乐原则来行事,“犀利哥”引起的巧合诙谐和跟意识形态无关的反讽成为了被偶像的最佳选择。网络媒介制造偶像与引导偶像崇拜,彰显其操纵流行文化的逻辑与策略的力量。一时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纷纷地报道“犀利哥”,“犀利哥”家喻户晓,他被推上了网络偶像的位置,“犀利”一词正是传媒的“馈赠”。
二、文化衍生产业链条 :“犀利哥”的符号性
文化消费市场中,我们消费的不是“犀利哥”本身,而是“犀利哥”符号所带来的内容。“犀利哥”的照片被无穷地创造和联想,“犀利哥”跟T型台上的模特辉映、与现实中的明星同台、和那些现实里不能触及的名流比肩。联系生产和消费的人群的特质,该符号实质上是社会群体的个人映射,透过带有符号意义的“犀利哥”找到我们自己,找到了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场景,像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享受聚光灯下带来的快感[3]。网络中众多的网民作为草根阶层,活得是如此的平庸凡俗,但是每个小人物都有成为偶像的梦,“犀利哥”是我们“超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犀利哥”就是我们草根代言人。他是属于草根的神话,在现实符号的断裂与弥合中反反复复被解构,我们看到了一场“狂欢的盛宴”[4]。网民将“犀利哥”与那些明星挂钩,我们解嘲明星,将明星的光环取下,将明星与大众遥不可及的距离拉近,找寻一种心理的平衡慰藉。某种程度上,“犀利哥”就是我们自己,爱他如同爱己。一旦我们撕下“犀利哥”最外的遮蔽层,“犀利哥”符号消费的内容就是我们赤裸裸的欲望暗示。
事物有相对两面性,操纵符号,热爱偶像,在一种群体的狂欢广场中,一旦陷入歇斯底里的狂热,理性将消失殆尽。符号背后的内容多种多样,其内容有的可以被解读,有的永远在事情真相之下,“犀利哥”背后的那些真正该引发我们关注的东西被强大的娱乐激情所雪藏,“犀利哥”本人在宁波流浪7年之久,7年间他默默无闻,风餐露宿,流浪于街头巷尾无人关注。而他7年之后的走红网络,也纯属出于偶然,网络传播显示了它的残酷和歧视,“犀利哥”在没有被发现前只是街头一名普通的流浪者,一个生活朝不保夕的流浪者,一旦出名便被千万的网络传播者加以追捧和关照。关注“犀利哥”,而不是被他那些外在的服装搭配、眼神犀利所惑,我们更该关注的是符号背后隐性的社会意义,像社会的保障体制是否完整,人格尊严的实现,传媒的职业道德,这才是“犀利哥”符号的社会价值本真。“犀利哥”事件”虽然喧闹,其本质上却是极为悲凉的。人们对于“犀利哥”的关注,并不是源于内在的同情心,而是源于群体性的无聊、空虚、寂寞。被群体狂欢遗忘的角落,符号的社会悲剧性正向毒草一样蔓生。
三、悲喜自顾的生活态:偶像本体的缺失
“犀利哥”事件发展到最后,各种网络解读版本纷纷出现,“犀利哥”本身却被忽略,传播的本体已不在,主角已缺失。大家关注的只是“犀利哥”可以提供的瞬间快感,关注的是加载在“犀利哥”身上的符号意义——千万网络所赋予的超越“犀利哥”本体的内容,碎片化的“犀利哥”消息被无数的网民臆想,构成可以幻想意淫的网络偶像,网络偶像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传播的本体失真性越大,“犀利哥”本身的来龙去脉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符号外壳承载的大量外来的信息。某种意义上“犀利哥”是够不成实质上的偶像的,真正偶像是拥有超前性和精英似的主导性,“犀利哥”草根出生,偶像的地位是被授予的,被忘记的“犀利哥”就像是网络传播中的一个个碎片化的符号,最终归于沉寂。转播主体不在状态,偶像的没落本就是偶像的题中之意。
将“犀利哥”传播事件看成在网络场域里进行的话,这个传播场里的人都在围观着“犀利哥”。在这个广场狂欢的围观时代,就算是没有“犀利哥”,也会有其他的“XX哥”或者“XX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而更值得讽刺的是“犀利哥”本身患有精神性疾病,面对摄像镜头和大众的注视,他面无表情、眼神空洞,传播主体在场域内的缺席,暗喻了传播泡沫和主体尊严丧失。随着传播泡沫的繁盛,“犀利哥”本体从被忽略的缺位到本体走向慢慢死亡。[5]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提及的是“犀利哥”就是我们自己的代称,拨开死亡的泡沫,消逝的就是我们,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这场传播的盛宴中慢慢地散失了。
四、传播后现代语境:被消解的精英偶像
“犀利哥”事件揭示了偶像走向黄昏,意指在后现代语境下,网友对“犀利哥”的解读传播各种情形中,消解和颠覆了传统的精英文化。传统价值认为精英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支撑动力,是优秀和杰出的代名词,精英文化的阶层对人有严格的要求,其排外性也使大多数的平常民众不可企及,在文化的导向上,精英文化注重深度思考、专业范式和技巧。但是精英文化偶像在网络社会下却被无限地消解了,偶像““犀利哥””的草根性特质,其创造者是网络中籍籍无名之辈,推动力是广大的下层网民。自发点击链接传播““犀利哥””的行为不受权利意识推动,精英文化偶像在“犀利哥”事件中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众视域的统摄,显示了自身的自主性、自由性。网民文化颠覆权威、蔑视传统对精英文化发出挑战,它极大地宣示了网民的精神世界。传统的精英文化是“表达—接受”的模式,该模式下,大众是被动接受而缺乏主导的单向模式,而“犀利哥”事件所代表的网民文化是网民表达—接受—再创造表达,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它更加积极地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在“犀利哥”偶像创作流行中,精英文化偶像被去中心化,逐渐地游向了边缘地带。[6]
除了对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解,网络“犀利哥”的解读中充满大众文化趣味和个体的审美意象,草根民众在其中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努力,是一种非传统精英表达方式。而且公共领域众多参与者其身份可疑,难辨行踪,他们完全地区别于传统的精英阶层,是解构精英的主体力量。将“犀利哥”哄抬到网络民众偶像地位的行为,宣告了网民社会下代表着民众阶层的觉醒。“犀利哥”事件,让公共领域在网民社会上有了一次伟大的实践,让大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能被讨论后形成舆论争论的场所。
“犀利哥”被解读成无数个T台模特场景,无数个明星演绎过的经典场景,网络偶像“犀利哥”置身在这些场景中,对传统偶像地位提出了挑战,减淡了偶像的神圣性和骄傲性。网络的娱乐大大兴起,虽有其批判的一面,也有其乐观积极的一面。大家授予“犀利哥”以偶像的头衔,就是对传统偶像的颠覆,削弱传统价值偶像的地位,这一行动无疑显示了民众力图打破传统的决心。在这个传播正向力冲击下使传统的偶像走向没落的黄昏。
五、变化莫测的流行文化:制造偶像又消灭偶像
网络制造出的偶像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人只是被同质化和操纵的机器,传媒生产什么我们便消费什么,我们成了追寻群欢的符号,单向度的我们在强大的娱乐面前被异化了,而偶像化的“犀利哥”正是给我们的一种暗喻。尼尔·波茨曼说过,我们终将死于热爱的东西[7]。一种产品被狂热地制造出来,也意味着事物热度的不正常性倾向,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膨胀往往会使人产生巨大的精神真空,带来信仰缺失,所以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在网络狂欢广场享受“犀利哥”给国民带来的娱乐时,大众同时以其注意力资源承担娱乐费用,关注和参与某个事件就是燃烧我们的生命时间。在娱乐化时代对生命时间及其价值的追问,表达了对流行文化的反思和抗议。
纵观整个“犀利哥”传播事件,我们咀嚼着“犀利哥”的事件种种,安享着“犀利哥”带来的种种欢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截止到本文的写作时间,一年已经过去,“犀利哥”的浓烈已经逐渐地淡去。网络偶像快速走向黄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在我们的预见范围之内。流行文化制造偶像又消灭偶像是一个非常迅疾的过程,这种快餐般的速食文化营养不良,并不会给我们留下些许有价值或值得回味的东西。“犀利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走红网络的人物,流行文化制造偶像,又抛弃偶像,偶像的黄昏是这种文化的文化负面性的先测。
传播时代精神凋零,而盛产网络偶像的年代,偶像一旦产生就注定要迈入黄昏。我们应该以评判的精神看待这种网络文化的负面性,使一个过热发展的事物回归良性的轨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之地》对文化有过警告“你们是半开的门,而挖坟穴的工人就等在门外。你们实在便是‘一切都因归于寂灭’”[8]。
[1]万晗.“犀利哥”——扇了谁的耳光[J].纺织服装周刊,2010,卷(3):53.
[2]孙瑞祥.大众传播动力学:理论与应用[J].新闻爱好者,2010,卷(10):4—5.
[3]鲍德利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J].江汉论坛,2001,卷(10):91—92.
[5]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J].读书,1998,卷(8):152—154.
[6]秦志希,葛丰,吴洪霞.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性[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卷(11):55.
[7]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尼采.尼采生存哲学[M].杨恒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An Interpretation on Web Idol——Retrospect on"Brother Sharp"
Zhong Ying Peng Guangm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rother Sharp was quite a big hit as a grassroots idol in last year's network.The fast-food mechanism of idol production and idol disillusion deserve our thinking by looking back the produced network idol and analyzing the idol production mechanism.The absence of brother sharp himself in propagation process revealed the losing of some humanistic care in the entertainment spirit and some participators in network actions were going decline.
Idol;Square Carnival;Symbol;Post-modern;Elite;Destroy
G112
A
1006-1789(2012)01-0062-04
2011-11-20
钟颖,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彭光芒,华中农业大学新闻中心,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科技传播。
责任编辑 曾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