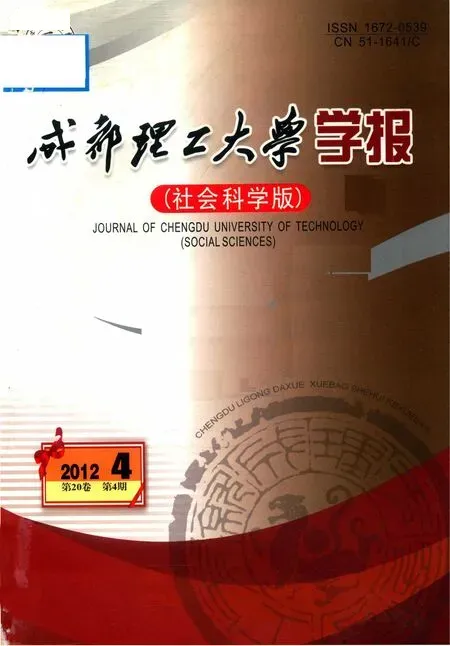从面子互动看中国现代婆媳关系管理
——以《双面胶》(1)为文本进行解读
2012-03-31谢清果曹艳辉
谢清果,曹艳辉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从面子互动看中国现代婆媳关系管理
——以《双面胶》(1)为文本进行解读
谢清果,曹艳辉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面子意味着自身在他人心智中占据的形象和分量,是个人判断其被他人接纳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婆媳关系不仅是面子互动的活跃场所,也是面子问题层出不穷的敏感地带。通过分析热播剧《双面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话,可以窥见面子心理的本质内涵及其在婆媳关系管理中的重要性。固然,婆媳在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无疑是矛盾冲突的原因所在,但面子互动的失败在放大婆媳差异、激发婆媳矛盾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能否理解面子的符号意义;能否迎合对方的面子需求;能否换位思考,避免伤人面子;能否公正客观,平衡婆媳面子是影响婆媳间面子互动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
面子互动;婆媳关系
面子牵动着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给面子”、“丢面子”、“伤面子”、“撕破面子”等面子互动行为是中国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互动双方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婆媳关系一直是人际关系管理中的难题,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从客观上形成了婆媳融洽相处的障碍,但沟通交流中的面子互动却能从主观上缩小或放大横亘在婆媳间的障碍。本文就从面子互动来研究和分析现代婆媳关系管理问题。
一、面子的符号意义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脸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符号意义,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中,“面子”的含义早已超越身体的“脸”部,具有更加丰富微妙的象征意义。
“如何定义面子,以何种方式完成面子工作,却是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1]在日常生活中,“面子”一词虽耳熟能详,但要给它一个准确的界定确实很难。就连熟知中国文化心理的林语堂也一再声称举例容易,下定义太难,只能说它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2]131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胡先晋女士最早对面子下定义。她认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是借由成功或夸耀获得的一种名声,[3]40任何有修养的人都应该给别人留面子,不要触及他人声誉,不要毁了他人名声,以免伤人自尊[3]53-54。20世纪70年代,香港学者何有晖否定了关于面子的许多说法。他认为,面子不是人格、地位、尊严、荣誉及威望等,而是个人要求他人对自己表示尊重和顺从而得到的相应评价。[2]翟学伟认为,面子是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2]133美籍华裔学者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将面子定义为“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它包括有关尊敬、荣誉、地位、联系、忠心和其他类似价值的感受。换言之,面子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你期望的自我形象,或者是别人赋予你的身份。”[1]面子有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正面含义是指“颜面”,也就是尊严。伤了一个人的“面子”,就等于伤了一个人的尊严。负面含义指的是“虚荣心”,也就是名誉或声望。所谓“打肿脸冲胖子”。[4]舒大平在运用东西方文化对“面子”的比较和分析中提到,“面子”的作用是在社会关系中起到承认成员身份和地位的作用。[5]
尽管各位学者在界定面子这个概念时角度略有差异,但可以窥见面子是与尊严、地位、形象等概念息息相关的符号。因此,在人际交往中,面子经常被视作尊严的外衣、地位的象征,是个人判断其被他人接纳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面子意味着自身在他人心智中占据的的形象和分量。
二、婆媳关系是面子互动的活跃场所
面子与关系都是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并相互作用。个人面子的大小、获得或丢失都是由与之交往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决定,因此面子互动渗透到中国人际交往的各个层面。而关系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互动而产生或者说是被创造出来的。[6]在这个互动过程中,牵涉到个人颜面的互动往往能推动交往双方的关系朝着新的、有时甚至是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面子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调节器。交往双方总是以对方是否给面子和给多少面子来判断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并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7]若礼尚往来给足面子,往往会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建立起互帮互信的亲密关系;若忽略或故意伤害彼此面子,则有可能导致关系疏远;若不顾情面撕破面子,则意味着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据中国网关于中国人“面子观”的调查表明,认为“面子”在中国人社会交往中很重要的占83.33%;认为一般的占11.98%;认为不重要的仅占2.61%。[8]足见面子在人际关系管理中的重要性。
面子虽然渗透到人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但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领域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台湾学者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中为解释人情及面子的社会机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构建了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此模型将中国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类,即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人际关系都是由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成分构成的,其间差异仅在于两种成分的比例不同。情感性关系的典型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成员,是一种长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关系双方的感情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而不需要面子功夫;工具性关系是短暂和不稳定的,这种关系是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如医生和病人、店员和顾客,因为不期待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也就很少牵涉到面子上的礼尚往来;混合性关系介于两者之间,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比例相当,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相互认识,并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等。他认为,“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利”,[3]20“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3]10
婆媳关系非常特殊,形式上是情感性的家庭成员关系,其实质却是混合性关系。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其他关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婆媳关系是以以上两种关系为中介结成的特殊关系。根据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进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媳妇娶进门,婆媳自然就成为一家人,构成了形式上的情感关系。但婆媳之间少了亲子之间的血缘联系,也不具备夫妻间的亲密,其关系的建立只是为了丈夫或儿子更加幸福,有着相当比例的工具性成分。由此可见,婆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性关系,不仅属于面子互动的活跃场所,而且是面子问题层出不穷的敏感地带。混合性关系的实质决定着婆媳双方看重对方是否给自己面子;情感性关系的形式,使得婆媳在实际互动中,容易忽视双方的面子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婆媳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利益冲突,其矛盾冲突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争夺自身在家庭特别是在儿子(丈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即面子问题。对自身面子的维护和重视以及对对方面子的忽视和伤害,会导致婆媳间形成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使得婆媳关系紧张甚至恶化。此外,婆媳的中介——(儿子或丈夫)在面子修复中的失衡或失策则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婆媳矛盾。
三、面子互动对婆媳关系的影响力和作用机制
电视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本文以《双面胶》(1)为文本,解读剧情中“给面子、忽视面子、平衡面子、伤面子、撕破面子”等面子互动行为对婆媳关系发展的影响力和作用机制。《双面胶》是一部以现代婆媳关系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共22集。剧中女主人公名叫胡丽娟(以后简称丽娟),是一个上海姑娘,嫁给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东北小伙子亚平。在婆婆(以后称亚平妈)未来上海之前,丈夫对其嘘寒问暖、端茶倒水,小夫妻亲密无间、恩爱无比。但自从婆媳共处一室后,由于婆媳矛盾的不断升级,最终婆媳仇视、婚姻破裂。在这一悲剧的演绎中,婆媳在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无疑是矛盾冲突的原因所在,但面子互动的失败在放大婆媳差异、激发婆媳矛盾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有心“给面子”,因迎合面子需求而互相欣赏
中国有“给面子”和“不给面子”的说法。从字面上理解,“给面子”就是给予、增进他人的面子;从心理感受上讲,“给面子”是让他人觉得有面子,即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对方感到被尊重或是受欢迎。因此,“给面子”会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或心生感激,由此拉近交往对象之间的心灵距离。如果我们期望与对方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往往会尽可能给对方面子。在正常情况下,婆媳之间是愿意或者说是乐意给对方面子的。从感性的角度讲,“进一家门就是一家人”,能成为婆媳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缘分;从理性的角度讲,“婆媳亲,全家和”。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会让对方觉得有面子。面子是一种人际知觉或人际评价,[9]不同人对面子的感知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婆媳间面子互动成功的关键是把握双方的面子需求。
从剧情中可以窥见,对于婆婆而言,最有面子的事莫过于媳妇欢迎的笑容和一声亲切的“妈”。例如,剧中亚平妈在和亚平爸聊天时这样评价丽娟:“你还别说,这丽娟我第一眼看着还挺喜欢,这孩子没啥心眼儿,笑呵呵的,她不像有的媳妇,整天拉着个驴脸儿。你说叫人看着心里头别扭。你觉没觉着,这丽娟和亚平有点像,我看他俩真有点夫妻像,……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由此可见,媳妇的笑脸是赢得婆婆喜欢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婆媳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社会中婆婆对媳妇来说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父权、夫权及孝道庇护下,婆婆对媳妇有无上的权利;而在当代社会,由于传统观念的消失与媳妇在经济上独立经营等客观变化,使婆婆的地位已经日渐衰微。[10]因此,婆婆搬进儿子家,最渴望得到的是媳妇的认可和欢迎。因此,对于搬进媳妇家的婆婆而言,媳妇的笑脸是非常给面子的做法,意味着媳妇对自己的欢迎和在家庭中地位的肯定。
而对于媳妇而言,最有面子的事莫过于婆婆对自己的爱护和尊重。出于对丈夫的爱以及对婆婆尽孝道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媳妇不得不接受和婆婆同住,在一定程度上包容和尊重婆婆守旧的思想观念,失去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但这是有限度的,用丽娟对丈夫的话来说“我没有义务对她好,因为她没有生我,我对她好,那是情分。”面对分歧,若婆婆能主动尊重媳妇的生活方式或用关爱感化媳妇,也会让其心生好感。例如,第二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丽娟提议去外面吃饭:“妈,那个我们出去吃饭吧,你们坐了几天火车,也挺累的了,我们早一点吃,早一点回来,好吗?”亚平妈是个过分节俭、非常反感外出吃饭花钱的人。但她没有严词拒绝或责备媳妇不会持家,而是委婉提出反对意见:“出去吃干啥啊?又不是外人,就在家吃呗。出去吃,花钱,又不卫生。”为了进一步让媳妇有台阶可下,不失面子,接着说:“你妈来了,我还能让孩子那个出去吃饭呀,是不是呀?那个啥,妈就是你们的贴身厨子。”一句“贴身厨子,不会让孩子饿着”让丽娟觉得很温暖,她的内心独白是“亚平妈也蛮和善,不像我妈,总板起脸来训我”。
《双面胶》虽然以婆媳间的各种矛盾为主轴,但“给面子”的情节时而穿插其中,且集中在剧情发展的前期,消失在婆媳关系完全恶化后。
(二)平衡面子,有失偏颇激化婆媳矛盾
形象地说,亚平犹如婆媳关系中的“双面胶”,是婆媳关系的粘合剂。在婆媳发生矛盾时,儿子(丈夫)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能够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有利于婆媳关系的协调。而偏向于任何一方,均不利于婆媳矛盾的协调和处理。[10]婆媳间的许多小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而矛盾常常伴随着对面子的威胁,这就需要一个中介来修复双方受损的尊严和面子。此外,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非常重视自身在儿子(丈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儿子(丈夫)在平衡婆媳双方面子中的原则、立场、态度和方式都会深刻影响婆媳的心理感受和关系发展。
《双面胶》中亚平在婆媳面子的平衡中是有失偏颇的,其基本立场是维护其母亲的形象和地位。他死守儿子的身份,在母亲与妻子的矛盾中,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明知母亲某些地方不对,也不指出来,只因为“这里有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古训”。[11]因妻子对母亲的不恭敬而对妻子发狠,让妻子理解体谅婆婆,将“不许给老人作脸”作为妻子的行为规范。剧中的许多情节都反映出他在婆媳矛盾和冲突中将平衡面子的天平倾向于她的母亲,例如第七集亚平对妻子发狠:“胡丽娟,你这,我一直对你抱有幻想,她是我妈,她把我辛辛苦苦抚养这么大,我孝敬她是应该的。你是我老婆,也就等于是她半个女儿,她说什么你就得听。你如果再惹她生气的话,我要你好看。”丽娟反驳:“没错,你妈没养我,我报答她,那叫情分,她没权利支使我做任何事情……”亚平:“你看我面子,看在这个小家的面子上,只要你给我妈一个笑脸,我求你了。”丽娟:“我实在忍太久了,我不喜欢你护你妈的样子。让我心里好难受的,我真的好委屈的,亚平,好咯。我答应你,我以后尽量不跟她发生正面冲突。”
虽然看在丈夫求情的面子上,尽量避免和婆婆起冲突。但丈夫对待婆婆和自己的双重标准,导致丽娟对婆婆的敌意和不满。她开始尽力减少待在家里的日子,曾经让婆婆赏识的笑脸也收藏起来,婆媳关系走入冰冷紧张的冷战期。由此可见,“双面胶”在婆媳面子平衡中的失衡加深了婆媳之间的矛盾。
(三)无意伤面子,因忽视婆媳差异而心存芥蒂
“无意伤面子”是指无意之中伤害到对方的面子,不是故意的。在沟通交流中,人们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经历来理解对方的言行举止。婆媳沟通中的言行举止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参与或介入进来的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传播者的意义、受传者的意义以及传播情境所形成的意义。[12]婆媳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因此婆媳在理解对方的言行举止时容易产生误解或者是难以理解,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方看来可能就是对其不尊重或蔑视,感到有伤自己的面子。若婆媳双方忽视彼此之间的差异,经常无意伤害对方面子,则会累积对对方的不满,从而心存芥蒂。
例如,对于媳妇来说,让丈夫为自己端茶倒水是老公疼爱自己的方式;但对于婆婆来说,媳妇当着她的面使唤儿子就是另一种滋味了。如第二集中,亚平妈教育亚平:“亚平啊,我说你,咋那么惯你媳妇呢还给她盛饭呢,还吃她的剩饭,我的妈呀,你说,她没长手呀,她没长嘴呀,一个大老爷们也不嫌埋汰”。亚平解释说:“自个儿家的媳妇,还嫌这嫌那的又是上海,都是男的伺候女的你那是老脑筋。”亚平妈据理力争:“老脑筋啥的,新脑筋啥的,这男人在家就这么作践,我这捧星星,捧月亮,把儿子捧大了,我那舍不得,儿子结婚了,给老婆当使唤丫头去。我看不惯,真的看不惯。”又比如,丽娟觉得自己和婆婆本来就没什么共同的话题,因此很少与之交流,但在婆婆眼里,这就是目中无人、不尊重她的表现。在第三集中,亚平妈抱怨:“不过这孩子也有点不大懂事,你说吃完饭,拍了屁股就上楼了,你帮我收拾收拾,我也不是说,说这活儿我怕累 多少活儿,不就几个碗的事吗?我就是说那意思,你吃完饭了,就是说站我身后了,帮我拿个这,递个那儿的。我毕竟不是保姆啊,我是你婆婆你妈呀,站后头说个话什么的,咱像一家人似的,另外,就是我心头也热乎的,这可好,一早上就走了,晚上回来也没个话,叫我觉着这心里头凉哇哇的。”
而对于婆婆来说,自己作为长辈有权利有义务管教引导媳妇做人做事。用亚平妈的话来说——“做老人的,说什么不都是为了孩子好”;但对于媳妇来说,婆婆把自己当家庭女主人、通过其儿子来限制自己自由是难以接受的。第四集中有这样的情节:因为亚平在家吃饭,亚平妈难得做了红烧肉。这让被“猪肉炖粉条”折磨得够呛的丽娟开心得要命,这肉就一口接一口的吃。可坐在旁边的亚平妈看着心疼,一块肉也不夹。因为在她的思想观念里,儿子和丈夫是第一位的,女人在家里是从属地位,好东西都应该给儿子吃。亚平劝母亲夹肉吃,亚平妈的回答含沙射影:“我不馋,我少吃一块,我儿子就能多吃一块。”言语中暗示丽娟别吃那么多,丽娟故意装着听不懂,还是继续吃,心想:“说这种话,不是明显说给我听的吗?我又不是不挣工资,吃两块肉,我还要看你脸色。”又如第六集中亚平妈指挥媳妇洗碗时,不停地教导:“我的吗呀,怎么放这么大水,小点儿就行,一半,你放多了又废水,又溅一身”、“你往这里倒不行,一下子就半瓶,多浪费啊,拿个布,完了就这么擦就行”、“外头,外头也得冲啊,把外头沫也得冲掉了,这就跟化妆似的,你不能化半拉脸,对不对呀”、“娟儿呀,你刷碗不能不刷锅呀,再说这灶台上也得擦”……
(四)互伤面子,口不择言导致关系恶化
面子是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13]良性循环时是礼尚往来,恶性循环时是互相伤害。当心存芥蒂累积到燃点时,婆媳点燃互伤面子的战役,彼此关系越来越疏离;而关系的疏离,使得对方在沟通交流中越发口不择言,不顾及对方的面子需求。随着剧情的发展,互伤面子的情节频繁出现,给彼此心灵留下一道道伤疤,从而导致婆媳关系进一步恶化。
对待长辈,最伤面子的事莫过于蔑视她的权威,否定她的地位;对于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最直接的蔑视莫过于不给笑脸,无视对方的存在。剧中,媳妇故意伤婆婆面子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言辞激烈和冷战上。例如第六集中,丽娟在婆婆挑剔的监督下完成工作,出言讥讽:“你要我干活,就要按我的方法,你要看不惯呢,你就自己干。这个锅呢我之所以特意不刷,是留给你的,因为凭我对你的判断,锅底还有两滴油,你完全可以留着再炒一盘菜。”自从刷碗的正面冲突后,丽娟开始有家不能回,一下班就到处约人或是去健身房,尽量减少在家待的时间,每次叫“妈”也是一个称谓而已。丽娟的当面讥讽和冷战策略给婆婆心理留下了阴影,让其觉得自己是不被欢迎和重视,是“不要钱的保姆”或“贴身服务员”。
对于媳妇而言,最难受的事莫过于被丈夫否定和质疑。因此婆婆伤害媳妇面子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儿子抱怨数落媳妇的缺点和过错,从而损害媳妇在其丈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如第七集中,亚平妈通过数落媳妇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你说说,这么多天 拉脸给谁看啊,我叫她刷几个碗,怎么啦,还记仇啦?”、“健啥身,你少吃点肉,多干点活,不就把身给健了吗?目中无人,好吃懒做,一进屋一句话都不说,我呢,这个家呢,就是旅店,我呢,就是那个不要钱的贴身服务员”、“你说我咋要怎么伺候她,内衣内裤我都尽心给她洗,可就唤不回她叫我一声妈。以前我还夸她,笑呵呵的,对谁笑啦?在外头笑了,一回来就拉着那个驴脸子,我欠她的,我……”在亚平妈的影响下,亚平开始反思,在第十一集中他发出这样的内心独白:“上海女人的娇媚只适合观赏却不适合一起生活”,婆媳关系的恶化危及到夫妻和谐。而媳妇对婆婆的尊重来自于对丈夫的爱,以及期待自己在丈夫心中拥有美好的形象。而当婆婆总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数落媳妇的不是、威胁到媳妇在其丈夫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时,婆婆在媳妇心中就成了挑拨离间的坏人,失去了获得面子的资本。
不论是言辞激烈还是暗地抱怨,如此“口不择言”的话语,或许能发泄一时的情绪,却在她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进而相互报复,恶性循环。
(五)撕破面子,不留情面催化恩断义绝
撕破面子意味着不给对方留任何情面,越让对方无地自容、丢尽脸面,就越解气。其中尖酸刻薄的言辞是打击个人尊严的有力武器。彼此撕破面子常常标志着关系的彻底破裂、婆媳从亲人走向仇家。
例如第十七集有这样一个情节:亚平爸得了癌症,丽娟大费周折,从爱财的老妈手里又借到三万为公公治病,打算拿到报销费后再还给她妈妈。但后来亚平姐打电话说厂里没有报销只给报400块钱,这下丽娟急了,让亚平把妈妈的养老钱还回来。亚平妈看媳妇逼儿子,说丽娟没良心。
亚平妈:“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钱,这不是家里碰到困难了吗?你作为儿媳妇,你不帮忙,你还这样,你还是人吗,你——”丽娟被激怒了,言辞激烈地顶回去:“你说什么,我不是人,你是人对吧?你老公快死了,叫你卖房子,你死活不肯,你这样就算是个人了吧,我提醒你呀,你老公现在躺在医院里面的钱,全是我妈妈出的,要讲做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全家谁都比你有资格谈做人,谁都比那你有个人样。我告诉你,别逼我,还好意思说我呢,你除了在李亚平面前挑拨是非,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之外,你什么都不会做,你就是全世界最毒最坏的老太婆……我不看你是亚平妈,我早把你扔出去了……亚平突然冲上来死命的掐住丽娟的脖子,亚平妈也激动地气晕过去。
这是婆媳间第一次撕破面子,彼此心中都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疤。后来丽娟和亚平妈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试图想修复彼此关系,但曾经撕破过的脸面,伤害过的自尊,却如同一枚枚埋在彼此心中的地雷,随时都有可能被踩爆的危险。
大结局中婆媳再次撕破面子就是以往失败面子互动的大爆发。在大结局中:一天丽娟逗刚会讲话的宝宝说话,怎知宝宝却清晰的吐出“妈妈坏”的字眼,显然是调教的结果。丽娟气急败坏:“搞了半天,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狼,不仅要吃掉我,而且要吃掉我儿子。李亚平,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个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那就是我。我留下,请这个老女人给我滚蛋。”言辞越来越失控的丽娟终于激怒了亚平,他失去理智地痛打丽娟,就在两人厮打成一团时,婆婆失声大喊,无人看管的宝宝从二楼摔了下来,后来幸好宝宝得救,但一家人从此彻底分开。
丽娟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性格、婆婆的记仇发泄,撕破面子的事从此以后时有发生,并随着剧情的发展达到巅峰,直到曲终人散,家庭分崩离析,婆媳关系彻底决裂。
四、结语
社会学家根据长期调查研究发现,我国8对离婚夫妇中,有4对是由婆媳矛盾造成的,又有约50%的夫妻因婆媳关系无法调和而长期冷战甚至分居。[14]可见,婆媳关系管理不容小觑。婆媳间的融洽相处的确存在一些客观上的阻碍,但沟通交流中的面子互动却能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或放大这些障碍。影响婆媳间面子互动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能否理解面子的符号意义。面子是外,尊严和地位是里,面子意味着自身在他人心智中占据的形象和地位。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有强烈的面子需求,并以对方是否给自己面子以及给面子的程度来判断自己被接纳和重视的程度。
其次,能否迎合对方的面子需求。婆婆和媳妇对自身形象和地位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因此满足双方面子需求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对婆婆而言,媳妇的笑脸相迎、夸奖和一声发自内心的“妈”类似的言行举止可能比贵重的礼物更让她感受到被重视和欢迎,感觉更有面子;而对于媳妇而言,婆婆对其生活方式的尊重比为她打点家务更能赢得其好感。面子是人际关系中人情媒介,遵循着礼尚往来的原则,迎合对方积极的面子需求,有利于亲密关系的培养。
再次,能否换位思考,避免伤人面子。换位思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和评估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婆媳思想观念、文化知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若要处理好婆媳关系,必须正确对待这种差异,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解读彼此的分歧和冲突,从而伤及对方的面子。
最后,能否公正客观,平衡婆媳面子。儿子(丈夫)是粘合婆媳关系的“双面胶”,但若在处理婆媳矛盾中偏袒一方,则会加深婆媳间的矛盾,使婆媳走到完全的敌对面。
注释:
(1)《双面胶》的编剧六六说:“婆媳矛盾存在于每个家庭中,而且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我从朋友那儿听来的,绝对真实。”摘自:灵芝仙草.当“双面胶”变成“双面焦”——中国式婆媳关系面面观[J].社区,2008(14):22
[1]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01.
[2]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1.
[3]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40.
[5]舒大平.东西方文化中“面子”的比较和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101
[6]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22
[7]姜彩芬.面子文化产生的根源及社会功能[J].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09,(03):116-120
[8]张艳丽,司汉武.中国人面子心理的文化解读[J].理论观察,2010,(1):52
[9]吴铁钧.“面子”的定义及其功能的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4,(04):930.
[10]李乐红.当代中国城市婆媳关系的伦理考察[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13-14.
[11]李丽.解读《寒夜》与《双面胶》婆媳关系之差异[J].安徽文学,2009(下半月):336.
[1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9.
[13]韩萍.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之“面子”理论[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0,(04):43.
[14]张华.双赢的婆媳关系[J].天风,2010,(01):42.
Abstract:In Chinese society,“face”represents your image and importance that occupy other people’s mind,and the critical index of judging your acceptance and attention by other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is not only an active place for face interaction,but also sensitive area full of face-related problem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ots and conversations of pop drama“double faced adhesive tape”,which reflects modern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 and wife,it is easy to discover the essence of face psychology and its importance in managing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then concluding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face interaction and summarizing main factors deciding the success of fac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Moreover,they are main factors deciding the success of fac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which can we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face,and can you meet each other’s face needs,and can we be empathy to avoid wounding the face,and can we be ability to fairly and objectively balance the two sides face.
Key words:face interac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责任编辑:刘玉邦
Mana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from the Respective of Face Interaction:Viewing and Analyzing from Pop Drama“Double Faced Adhesive Tape”
XIE Qing-guo,CAO Yan-hui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D669.1
A
1672-0539(2012)04-0055-07
2012-03-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0921108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二批特别资助项目(200920307)的阶段性成果。
谢清国(1975-),男,福建莆田人,哲学博士,历史学(传播史方向)博士后,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传播;曹艳辉(1987-),女,湖南邵阳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大众传媒与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