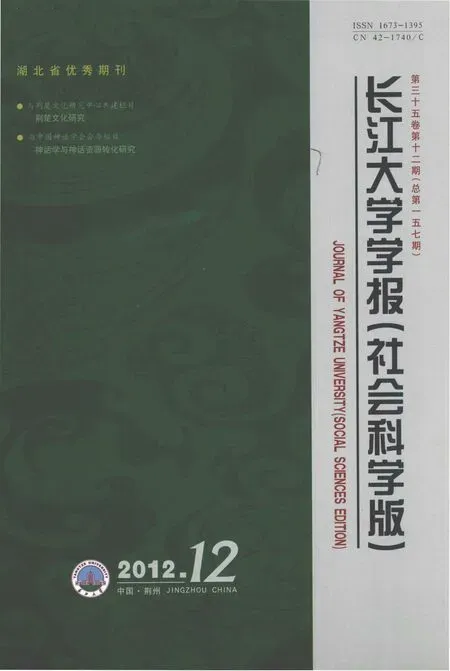《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新感觉与言意矛盾①
2012-03-31朱道卫
朱道卫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斯普特尼克”是文学与科技事件相关联的象征之物,也是构成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核心与契机。美国诗人、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是Beatnik(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Sputnik(斯普特尼克,俄语意思即“旅伴”)则是由前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Beatnik与Sputnik 发音相近。由“垮掉的一代”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斯普特尼克”,自然成为小说人物堇、敏谈论的对象,作家与卫星莫名其妙又极其自然地巧合在一起,且作为贯通始终的新感觉之“象”,成为小说的主线。借用修辞手段进行新奇、陌生的感觉描绘,是小说突出的艺术特点,如开篇一段:“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1](P1)极度夸张的非文学材料经过陌生化后,进入文学作品,娴熟而陌生的新感觉风格和技巧,显示了作家对日本传统文学的吸收与承继。
一、新感觉与陌生化
20世纪20年代,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组成“文艺时代派”,评论家千叶龟雄正式提出“新感觉派”。作为其延续,新心理主义作家学习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心理主义创作方法,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艺术地表现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1930年,伊藤整将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引入日本。[2](P428~429)该派在语汇、诗或韵律、节奏感方面所具有的感觉艺术新颖、生动,如“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3](P1),具有鲜活的动感。“新感觉派”强调主观和直感,重视象征性因素,表现出对于文体和语言技巧革新的热衷。其主要特色是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根据刹那间的主观感觉把握外部世界,运用想象构成新的现实,然后通过新奇的体悟和词藻加以表达,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有意采用欧洲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表现方法,用感性表达的方式描绘人物的纤细感情和心理活动。“新感觉派”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叙事的方法,华丽的语言铺陈、精巧的句子修辞、过量的词汇堆砌等,“使强烈的表达愿望得以释放”[4]。
村上以叙事和感受的精细、清晰参与到难以遏制的表达渴望中,其新感觉技巧犹如他所钟爱的音乐一样,繁多而精致,“脑袋像大雨中的水田,一片茫然,分不出边际……”[1](P72)之类的句子随处可 见。村上热衷于在感觉、语汇、韵律、节奏感(尤其不离音乐)方面体现艺术的新颖性,语言富于张力,部分来自于对细腻、新奇感觉的把握与坚持。他以感性认识为起点,以直观的视听因素认知和表现世界,追求新的感觉、感受,并对观察对象作精美加工,甚至直指人的内心世界,华彩的文字下潜藏着由心理新奇与叙述陌生共同构成的敏锐感觉。故而,村上春树笔下俏皮语言迭出,如“这种时候我的判断力,就像保险丝烧断似的戛然而止”[1](P66),将 人失去 判断力的刹那感觉表现得精准、鲜活而陌生。
陌生化即“奇特化”、“反常化”,是使艺术作品增加可感性的各种手法之统称,又是使文学作品具备文学性的必要手段。它把生活、文化和思想中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为强化文学的清新化,对于事物的通用名称,它惯于采取反常称呼,即往往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形象描绘事物,创造其视像,使形象清新化。[5](P133~134)如《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句子:“电话一下子断了,简直就像有人用铁榔头砸断电缆似的,唐突地、暴力性地断了……”[1](P73)声音与形象的清新感强化了作品的陌生化意识,使人感受到题材和形式的耳目一新。为表达需要而创造视像,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谓“立象以尽意”,立言不足以达意,则立声形之象以达表意目的,最终构成的即是感觉上的新奇与陌生。
二、内心感觉外化与意识碎片
新感觉与陌生化的基础是人的内心感觉及其最终的外化,类同于意识流。意识流指人的思想或感觉的持续流动,后被借用指称现代小说中模仿意识流程的创作流派与写作手法。意识流是河流一般的思维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充盈着感觉与想象,并积淀为沉思默想的主体内容,“流动”成各种思绪。“意识流”概念把人的意识描述为无法切断的河流,即心理时间上的主观生活之流。
“那情形像是想把什么一脚踢开,却无可踢的东西”[1](P11),《斯普特尼克恋人》的这种新感觉意识极为简短,是内心感觉外化之后形成的“意识碎片”,还不足以多到构成流动之势,但能直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构成新感觉图像。它们是作家调动想象、联想,从心灵深处观察、描绘、刻画和展示他所熟知的生活,并巧妙地加以外化的结果。日常现象感悟与心理认同形成意识碎片,再通过描述或象征方式使得社会文化现象充盈新感觉甚至哲理意味。
“其中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存在,而是不在。不是生命的温煦,而是记忆的静谧。”[1](P187)此类心理流程以心理感觉为基础,作家将它们外化为言辞,成为话语形式,尤其是成为“内心独白”(叙述者销声匿迹,人物取而代之),是自由联想的真实记录,是未经审查、未经理性控制、未经逻辑编排的先于理性层次的心理活动。
新感觉外化时常会碰到障碍,需要借助于中介。“我们的生存过程,无非像捯细线那样,一个个发现其交合点而已。”[1](P188~189)“捯细线”充当中介,有助于捕捉人物的心理轨迹,更好地传达作家关于人的生存过程的思想,具有科学性和写实性。
村上春树有效地将新感觉镶嵌在意识流动里,以配合情节推动和细节描绘。意识流程中,新感觉会不期而至,如“她乘的小艇在港外消失后,我觉得身上有几个小部件被人拔去了”[1](P133),作品在探测人物的内心世界时,通过感觉上的“几个小部件被人拔去”,自然形成想象冲动与张力,构成人物内心的诗意化流程,温婉之外,还具有思想的力度和耐久性。新感觉裹挟意识流动时,意识是基础,陌生是表象,语言则是纽带。林少华认为,村上文学在艺术上大量使用幽默、比喻、隐喻等手法,语言含蓄委婉、优美细腻,“文笔洗尽铅华,玲珑剔透”,是将语言洗净后加以组合。[1](译序P18)林少华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村上文学的新感觉特点。
三、言意矛盾与修辞手法
新感觉外化时碰到的言词表达障碍,即中国古代文论所说的“言意矛盾”。言意矛盾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常常迫使诗人借助声形之象而立意,以补立言之不足。
言不尽意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首先由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学派所倡导,后来成为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文学离不开语言,但往往言不能达心,书不能达言,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不尽意、超言绝象等,成为作家解释语言痛苦的理论命题,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斯普特尼克恋人》重视“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境界,如“她把一粒橄榄放入口中,手指捏着橄榄核,十分优雅地投进烟灰缸,犹如诗人清点标点符号。”[1](P83)
言不尽意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的意指无能,从而造成言不达意、言不尽意。语言说不清楚,释家干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文学终究离不开言,只好借助于外物,立象以尽意,言意间被插入中介象。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专门谈到明象的问题:“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曾艳兵认为,若停滞于言,便得不到真正的象;停滞在象上,便得不到真正的意。只有忘象、忘言,才能获得真正的意;只有越过言、象,才能摆脱日常束缚,超越现实和自我,进入自由审美的境界。[6](P55)“我像呼吸一样,极为自然地用纸和铅笔一篇接一篇写文章,并且思考。”[1](P119)“像呼吸一样”,便成为连接言与意之间的象,它正是建立在新感觉基础上的陌生化对象。
象主要有两种:声象与形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大象”将内心之音外化,将内心之象形化,都能补立言达意之不足。萧统《陶渊明传》所谓“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音声相合正是“大音希声”的高妙化境。
但文学作品要表现的声不能时时处处都是胜于有声的“无声”、“无言”似的希声大音,文学毕竟不同于音乐,它最终要归结为言或象,为意服务。所以,超越言、象之前,必先借助于言、象,使之具备一定的意义指向性。如《斯普特尼克恋人》用“累得枕木一般”[1](P54)写累,“睡得铁砧一般昏天黑地”[1](P22)写睡,借助“枕木”、“铁砧”这些极为生活化、新奇化的具象进行外化,简洁明了,引发读者积极参与到无尽想象之中,从而引发新感觉共鸣,文笔曲折而寄寓丰富,言外有不尽之意。作家撇开正面描写,采用侧面形容,累和睡的情状全由读者想象联想,不仅感觉新奇陌生,而且取得“半多于全”的艺术效果。
借助于声象立意,实际上就是《诗经》开创的比兴手法。村上春树依循的是人类共通的比兴经验和传统,此即西方文论中所谓的修辞格。“你的文章中有自然而然的流势,就像文章本身在呼吸、在动一样。”[1](P45)这里便有比喻和通感的因素。
修辞手段又称“修辞格”,是修辞学家对语言表达方式、效果的分类,是与日常谈话和写作习惯相距甚远的、奇特的语言方式(即陌生化方式),它生动、优雅地附加在词和语句之上,意在使表达更富于文采,借以增强叙事效果。它被看成是作家控制读者的手段,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叙述手法都可以看作修辞格。
处于言意之间的声形之象,实际上是修辞中通过奇特的语言方式生动、优雅地附加在词和语句之上。村上小说善于捕捉生动、优雅的声形之象,营构比喻、拟人、夸张、通感等修辞效果,达成新感觉。如“鸡像报复什么似的气势汹汹地啼叫起来”[1](P22),用“气势汹汹”写鸡叫,虽不优雅,但却生动;“长得如同吹过世界尽头的风”[1](P112)的一声喟叹、“狂奔的马蹄跑过木桥般”[1](P17)的巨大心跳声,以有形描绘无形,皆精彩、陌生,传达出人物的内在意识。诸如此类,作家借助于修辞格,沉溺在语言能指符号中,心安理得地自由嬉戏,达到“意新语工”之境。
一切文学文本都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修辞性语言,而修辞性语言就是用一个文本描述另一个文本,用一个修辞语替代另一个修辞语,这就是“互文性”。[6](P65~66)如“敏留出一次呼吸那么长的空白”[1](P73),《斯普特尼克恋人》用“呼吸那么长”形容空白的时间长度,感觉鲜活、准确,语言丰富、湿润、简洁、光亮而透彻,修辞效果远远超出直接描述。
结合西方的修辞手法以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言意和声形之象理论,笔者认为,声象作为修辞性语言,犹如现代技术语境中的超文本,能更好地链接处其两端的言与意,体现出更强大的表现功能。
四、“诗不可注”与读者参与
语言无能进一步造成“诗不可注”。中国古代批评家反对诗歌注释的坐实、穿凿、虚妄,反对注释对诗歌浑融意蕴的破坏,要求通过原句领悟原意;或者不加言说,得意忘言。得意忘言,旨在探求象外之意,所谓“境生象外”。作为审美境界,“境生象外”,强调诗歌通过有限形象传达无限意蕴。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即反对“词意浅露,略无余蕴”,提出“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之主张,符合“意新语工”之要求,正是在追求陌生化、鲜活化的艺术效果。有象方能境生象外,得象外之旨意,其中真幻,自然分明。“幻”指作品艺术形象的虚构性,“真”指形象所蕴含的意旨之“正”,“幻中有真”揭示了虚构和真实的关系。“意新语工”、“幻中有真”的要求,更增加了注诗的难度。
新感觉在于捕捉瞬间的陌生感受,并加以精准描述,体现了作家欲为之作注又无力作注的心态,具有反常化和不可重复性,其感觉本身也不可注。可读不可解,一旦强行注解,肢解言说,必致割裂、穿凿、错出种种,韵味殆消。新感觉一如诗歌,也有不可言说之妙,熟读久思,妙理自明。如“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上打孔”[1](P52),“这夜景给人的印象很深,真想拿剪刀剪下,用图钉按在记忆的墙壁上”[1](P86)等,极具诗意。套用“诗不可注”的说法,用常规语言来阐释新感觉语言,也会出现语意断裂。“诗不可注”的文学观要求读者以言观意,言外别有会心,不能泥辞以求,在无文字处求其精神要妙,此即所谓“善读”。“世界失去了现实性的核心……背景是纸糊的,星星是银纸剪的,浆糊和钉头触目可见”[1](P76),这些鲜活的句子证实,新感觉主要不是以言注意,而是以象通意,对读者有更加强烈的呼唤意识,它要求读者共同参与,完成阅读活动。就像诗人处理言、象、意的高明手段必须得到读者配合,才能最终实现传情达意的效果一样,新感觉也呼唤读者“善读”。
总之,新感觉从意识出发,经陌生化和修辞手法的共同参与而得以完成。或者说,言、意、象之间,为了表达意,从言出发,经象的过程,最终完成对意的传达。林少华指出,比喻是将两个类似或相关的事物连在一起,而“村上的好多比喻一反常规,硬是把基本毫不相干的东西连接起来”[1](译序P17)。连接“毫不相干的东西”,正是象的作用和效果,因为新感觉修辞往往是非比寻常甚至反常的、新奇而陌生的修辞。“意识—陌生化修辞—外化为新感觉”,几乎等同于“言—象—意”程序,不妨将新感觉手法看作《诗经》比兴手法的翻版。一方面,村上作品娴熟而成功地应用“言—象—意”程序,为小说主题凝聚、情节展开和人物塑型构筑了新感觉基座,并节省了叙事成本,增强了叙事趣味,提升了叙事效率。另一方面,小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感觉过剩之弊,势必增加读者的阅读成本,易引发审美疲劳。
[1](日)村上春树.斯普特尼克恋人[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郁龙余,孟昭毅.东方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日)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M].叶渭渠,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陈晓明.三十年来文学变革的十大后果[J].南方文坛,2008(6).
[5]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曾艳兵.东方后现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