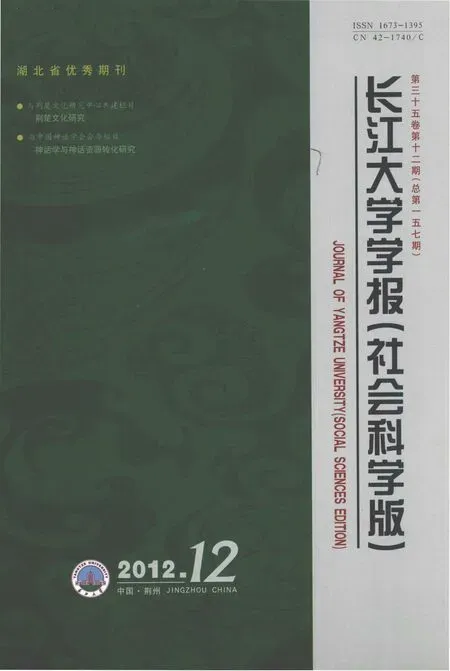《咏怀诗》与阮籍的儒学情怀
2012-03-31左慧青
左慧青
(山西大同大学 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历来阮籍因其放浪形骸、不拘儒法而被披上玄者的外衣,但只要细读他的《咏怀诗》,就不难发现阮籍是一个饱有儒学情怀的地地道道的儒者。前人已从《咏怀诗》入手来探寻阮籍,《咏怀诗》的精神实质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情言其志”[1](P3),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咏怀诗》来认识阮籍。
《咏怀诗》的内容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归结其思想内容与旨趣不外乎对人生,特别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感叹,以及刺时、刺世。阮籍内心的“焦虑、痛苦、伤感、恐惧、忧郁”,在《咏怀诗》中被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而在这些情感的底层则是对当时政治的痛恨,是无比的愤世情怀。阮籍缘何如此愤世呢?儒学对他的影响可谓是主要原因。
阮籍的儒学情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于世儒家族,立志奉儒守官。阮籍生长于世儒家族,从小便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这是阮籍有儒学情怀的基础。阮籍的先人视儒学为其家学,阮籍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表现出爱好诗书、有志于儒学的志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诗》、《书》是儒家经典;“颜”、“闵”指颜回与闵损,他们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大贤,可见阮籍早年是按照儒家思想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的。正始二年(241年),阮籍32岁,作《乐论》,称“刑教礼乐一体”[2](P90),主张以礼乐教化天下,与儒家思想吻合;正始五年(244年),阮籍35 岁,作《通易论》,从哲学理论高度阐明了自己以儒教为依托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由此可知,阮籍在35岁之前是信仰儒教的,即此前阮籍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学说为主。
第二,被迫谦退冲虚,披起玄学外衣。政治斗争使阮籍不得不披着“道”的外衣来守“儒”。就在阮籍作《通易论》的同年,大将军曹爽为提高自己的威名,兴兵伐蜀,骆谷之役不利,伤亡甚众,引起司马懿的不满和野心的膨胀,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走向分裂,双方政治斗争开始明朗化,政治局势由相对的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在其《咏怀诗》第四十二首里自述曰: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阮籍本来对“王业”抱有极大热情,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设想与朝中“八元”、“八凯”式的贤臣共同合作,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但现实与愿望恰恰相反,魏氏朝廷经过短期的相对平静后,形势猝变,政局日趋恶化,“人事盈冲”犹如“阴阳舛错”,“由泰变否”。因此,希望被失望代替,满腔的功名热情为隐遁的冷漠代替,阮籍由儒家“八元”、“八凯”式的良辅走向了道家超世式的“园绮”、“伯阳”,他发誓做个“万载垂清风”的名士。此后,正始七年(246年)又作《通老论》,阮籍由儒入玄。
第三,自居玄学名士,信守儒教不悖。此后阮籍的行为、气质也似乎在标榜自己玄家的身份,俨然一个玄学名士。他不拘礼俗、旷世不羁,对礼俗和恪守礼法之士充满了鄙夷。儒家的传统礼制,阮籍全然没当回事,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不满,假如曹魏政权昌明有为,阮籍身居高位(按照当时的取士制度和伦理习惯),踌躇满志,正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积极奔走,他必然会中规中矩,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深恐这些琐细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阮籍要从政,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其实是有机会的。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集团无时无刻不在庇护和拉拢阮籍。如晋文王批评司隶何曾而庇护阮籍;“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3](P1360)钟会以此为罪,而文帝以酣醉赦免;阮籍提出要做东平相,“帝大悦,即拜东平相。”[3](P1360)但一天后他却不做了,文帝也并没有怪罪他,反而“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3](P1361)。也正是阮籍的种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得司马氏集团不得不对他留一个心眼。
阮籍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很显然是坚守儒礼的结果。儒家讲求以忠孝伦理治天下,而司马氏操权违背君臣之礼,是对曹氏皇室最大的不忠。虽然司马氏一再标榜以孝治天下,但他们试图以阴谋的手段夺取曹魏政权,就是不忠不孝,这是为信仰儒教的阮籍所不齿的,他自然不会与之合作,转而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阮籍骨子里对儒教的信仰并没有泯灭,只是借老庄来掩饰,寻求心理的平衡。
阮籍骨子里是信守儒教的,但行为上似乎对礼教和恪守礼法之士持极端鄙夷的态度,生活中也常常背弃儒礼,这为儒教的一些正派人士所不容,阮籍历来因此而饱受指摘。但从这些批评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当时,司马氏集团以及依附他们的朋党,正是利用“名教”来窃取曹魏政权,达到自己的私利目的的。于是,阮籍便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但从这些对抗更能看出阮籍对儒礼的奉守。阮籍在服丧期间,饮酒食肉,但他能“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4](P136),这是至孝;眠邻家妇侧而“终无他事”,是儒家所讲的清者自清。
由此看来,《咏怀诗》是阮籍的儒者情怀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忠于曹魏政权,却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出仕,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却让他出仕无望(而非不愿);反对司马氏篡权,却不得不畏于高压;虽身在朝廷,却旨在保命。《咏怀诗》是阮籍面对污浊、黑暗的社会,无法找到真正出路的哀鸣,是乱世悲歌,是其发泄心愤、平衡心理的直接结果。由《咏怀诗》反观阮籍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孝仁义的阮籍,一个有着坚定的儒学情怀的儒者,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穿了玄学的外衣,把儒学情怀和对现实的不满一起融化在酒里。82 首《咏怀诗》,是阮籍真实思想的反映,是作者真实感情的隐约曲折的表达,是作者儒家情怀的象征与标志。
[1]钟嵘.诗品·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房玄龄.晋书·阮籍传(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