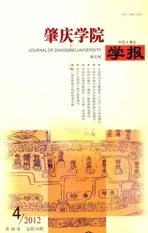王富仁学术研究论略
2012-01-28李金龙
李金龙
(汕头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汕头 515063)
一、“回到鲁迅”与“思想革命”:学术范式的颠覆与重置
王富仁在学界崭露头角始于后来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之作”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的出版,但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则是其后续的一系列学术活动,针对建国后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条条框框扭曲、肢解鲁迅的混乱现象,他提出了“回到鲁迅”的学术口号,但面对当时重重禁锢的研究樊篱,鲜见学者有打破坚冰的学术胆略和勇气。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则是第一次从理论到实践完整地诠释了 “思想革命”的真意,展示了“如何回到”这一实践课题,一举扭转了用政治模式来研究鲁迅的意识形态范式,确立了以鲁迅的精神文化体系阐释鲁迅的新范式。此举影响巨大,不仅打破了鲁迅研究沉闷平淡、陈陈相因的局面,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学风的变革,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权威话语的颐指气使,剥离非学术因素的掺杂、干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却遭到一些借意识形态套语所作的狐假虎威式的批评,有人认为王富仁的研究“已经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用他的‘研究系统’去代替‘旧的研究系统’,实际上是对三十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根本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根本否定”[1]。“回到鲁迅”的提出,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正本清源,而且隐含着知识分子如何感知和认识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问题,这里面还包括如何处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不合理的约束和成见,像鲁迅那样勇于进行自我反省和解剖;其次,面对研究对象本身,在全面了解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借助问题的分析充分展现其独特性的价值,而不是削足适履地用已有的框架对研究对象进行扭曲或肢解。实际上,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正像胡塞尔所说的“面对问题本身”,只有直面问题本身,才能真正洞察对象的存在本质,客观地揭示出对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张梦阳指出:“从史的角度审视,仅这一举就具有重大的学术史价值。”[2]135以此为开端,作者将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知识分子的阅读和感知向更广的范围拓展,从曹禺、冯雪峰、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到闻一多、冰心、许地山、巴金、老舍、朱自清等;从“维新派”、“洋务派”到“创造社”等,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依然只有一个:通过一系列的清理和反思去除附着在文学肌体上的寄生物,使之回复原本的面目。得益于王富仁的洞见,学界逐渐响起了更多的附和之声:“回到郭沫若”、“回到现代中国新诗”、“回到文学”、“回到……”等,这些日渐壮大的“回到”之声既表明首倡者的开拓性努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说明学界在“纠偏”的层面上有了更大的进展,学术研究日渐向一度偏离的正常的学术思想文化轨道回归。
“学术史的发展实践证明,无论多么好的阐释视角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阐释饱和与意义超载,如果不进行视角转换与移位,学术就无法发展”[2]135。作为打破鲁迅研究禁区的“第一燕”,正像自己意识到用社会政治视角来阐释鲁迅的弊端而主动进行转换一样,王富仁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研究系统是囊括一切的万能模式,所以,他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对各种鲁迅研究学派(包括曾用各种手段攻击过自己的学派)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叙述与评论,一一指出其功过得失,期待鲁迅研究能有更高层次的进展,尤其是面对学界新人对自己的挑战与批评,他更是显得谦虚、诚恳,理性地反省自己的局限和缺憾,正如他自己所说:“绝不以自己的论述限制或斫断向深层次空间作无限伸延的研究根须”,并“愿做起点,不愿做终点”[3]。不乏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善能容人的雅量,正是王富仁这一代学者的可贵之处,这一点即使在他们成为执学界牛耳之泰斗时依然如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与浸润下,有关鲁迅研究的高水平论著不断涌现,并相应带动了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新国学”:绘制新文化地图的建构基础
文学是构成文化系统的因素之一,文化研究是王富仁宏大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有更大的学术构想:“使鲁迅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3]《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功能刍议》、《中国文化的亚文化圈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几大分化》、《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流变》、《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化》、《论当代中国文化界》、《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等长文以高屋建瓴之势,对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进行观照,不仅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各种因素和流派互动、演变、分化、整合的过程,而且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文化表象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对中西古今文化宏大格局的考量中,鲁迅成为勾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中枢,“鲁迅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又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中国古代没有一种文化是为鲁迅这样一个脱离开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背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他得独立地前行,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自己的路来”[4]140。因此,鲁迅自然地成为反思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重估并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思想基点。正是因为有了鲁迅、陈独秀、胡适这样一批思想者的努力,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才成为中国文化涅槃 蜕变的新起点。
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鲁迅那代人身上交织着中西古今文化的复杂因素,而中国历时久远的文化传统更多地表现出对人本性的压抑与桎梏。新文化的建构既不能简单摒弃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也不能直接移植西方的文化模式,而必须在荆棘丛生的文化丛林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路径,建构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系统。王富仁认为,在这种艰难的跋涉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与整个世界文化的沟通与对接,将一个封闭的、停滞的、落后的旧文化系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与世界文化同时发展着的新文化系统。但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却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与破坏为代价所换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并未达到预期的应有高度,不仅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相形见绌,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亦失色不少,故而他们或取西方文化立场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与清理,或取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对中国现代文化予以否定。实际上,这不仅抹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真空,而且由于观念上消除了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调整缓冲期,造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那么,如何回答关于中国现代文化解构性的因素远远超过其建构性的一面这个问题呢?王富仁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新的文化样态的产生必须在对固有文化系统的解构基础上产生,没有这个解构过程,中国文化就无法成为开放的、动态的、新的文化系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与根深蒂固,要想瓦解其继续存在的文化基础就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采取貌似极端的操作方式。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太喜欢调和折中,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5]这就不难理解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高举破坏的大旗,执意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一面了。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当年的文化先辈们为开拓新文化生长空间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雷霆之势扫除了新文化发展的第一重障碍,催生了新文化的萌芽,实现了与世界文化的接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生发的原点的根本原因,也是作者一贯坚持五四立场的根本原因。在面对中西文化碰撞后所造成的文化变局时,时人曾经作过多种努力,有提出“国学”与之对抗撷顽者,有以西式方法“整理国故”者,还有醉心欧美全盘西化者,事实证明这些都因缺乏坚实的文化根基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活力,只有像鲁迅那样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血脉,整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因子推陈出新才是建设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化的合适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学也好,西学也罢,都不再是固定僵化的教条,而是可以按需取用的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应该说,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在新的起点上加快中国文化独立性、创造性建设的时期,遗憾的是,多数文化论者常常顾此失彼,不是抱残守缺、盛气凌人,便是在西方文化面前丧失自信、自我贬低,所以,王富仁有针对性地提出“新国学”的理念,目的是赋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一个整体性的框架,突出其包容性和建构性。与“新国学”相对的,则是“国学”。这个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是为了体现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而出现的历史性概念。时人曾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6],其中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表露无遗,但作者并不主张一味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紧接着又补充道:“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之,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欢迎之。”[6]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发展大势,认为应该以辨证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学”,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的学术文化,绝不能因噎废食,丧失与世界文化对接的契机。遗憾的是,后人却对“国学”这一概念作了绝对化、凝固化的理解,章太炎的国学内涵“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7]则被奉为圭臬,而这样的理解仍然是将“国学”限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范围之内。
平心而论,“国学”作为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自有其价值与意义,但绝对不能将它凝固化、实体化,20世纪初的学者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许啸天说:“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8]5这说明所谓的“国学”根本无法课以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标准,它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全部构成体,但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人不肯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力图通过重新阐释和界定使之成为相对具体的某一学科:“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学术门类是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学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级学科,以国学基础(小学)、国学方法、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集部研究、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学与社会习俗、国学与出土文物、国学与海外汉学等作为二级学科。”[9]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学科系统性的问题,不过是把传统的小学、经学、史学等早已独立存在的学科改头换面塞到国学名下,不仅缺乏建构性,而且恰恰违反了科学思维的基本精神:若无必要,勿增实体,除了聊增噱头,实在于事无补。
纵观中国文化史,“国学”的历史就是不断发展、生成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学术整体的‘国学’,在纵向的流程中,永远以积淀与生成两种形式存在并发展着”[8]6。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五四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学术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吸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学术文化也没有理由被排斥在外,否则就会中止这个生成、积淀的过程,甚至最终会导致“国学”的消亡。但事实上,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归宿感的危机和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10],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裂变形成了事实上的绝对分裂和对立,这种分裂和对立肇因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并未随文化冲突走向整合而达致和谐与统一,而是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争先恐后转投革命怀抱的现象也并没有避免在表面的统一之下互相倾轧、攻讦的实质分裂。“国学”也被部分知识分子用来作为非难、攻击另一部分群体的借口和武器。因此,王富仁认为,“国学”理念已经难以体现出其作为中国学术共同体和中国知识分子同存共栖的归宿地的意义,“新国学”理念的提出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学术理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10]。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各种不同领域、不同思想、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术成果能够找到它们独立的价值空间,各种流派、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也能够在文化创造的意义上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为当下的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各种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自我生存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三、“我站在我自己的这一边”:由自我体验出发的启蒙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个人的发现”[11],但五四之后本应该顺理成章的 “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却因为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不得不停滞甚至倒退,标志着启蒙程度的个体主体性建构过程也随之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民族主体性、集体主体性几乎一面倒地压抑了个体性的萌芽,而这既抹杀了五四新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和价值,也扼制了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还是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它们存在的重要前提都是对个体的独立意识、情感意志、人性权利的消泯与禁锢,其目的则是实现对全体人民的宰制和奴役。直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兴起,历史才真正步入了人性意识觉醒的个人解放时代,康德早就提出:人类生存的意义只在于人类自身,因而自身就是最终目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和发展的具体载体和最终目的必然指向个人,而每个生命也都是在自我具体的体验和感知中感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与西方以科学理性反对外在的宗教迷信禁锢不同,中国的启蒙运动内涵更为复杂,人们不仅要摆脱外在的封建宗法桎梏,而且要与自身思想和肉体里积淀已久的纲常名教意识作斗争,就其持续性和艰巨性而言,后者远超前者,因为推翻外在的政体和社会组织形式可以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政治运动的能力和智慧,但一次次的政治变革最终结果却都与其初衷相去甚远。尽管有感于“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荒谬与无奈,鲁迅依然坚持“立人——救国——改造国民性”这样的人生立场,并甘愿充当“历史中间物”的过渡角色。而要实现自我的蜕变与超越不仅需要具备鲁迅那样犀利的自我解剖勇气,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更需要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毅力和行动来排除来自把持着“国家”、“民族”等“大义”名份者的指责和干扰①中国的启蒙表现在两个向度,外在的反对宗法专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诉求被概括为“救国”,内在的摧毁纲常名教建构现代人格的诉求被概括为“救人”。详见张岱年等:《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旧道德历史意义》,见《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507-523.。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启蒙在中国的艰巨性,中国的启蒙者面前还有很长的路。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历史已经悄然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走向世界”、“现代化”、“思想解放”等一系列宏大命题众声喧嚣之际,王富仁却坚持以自我生命体验和阅读感受为研究起点,他批评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化、教条化:“所有的研究活动似乎都是要为了证明一个与自我的实际人生追求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是非,而这种历史的是非却与他们人生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观念毫无关系甚至取着对立的形势。”这明显已经严重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本意,他明确提出:“任何研究活动,其目的都在增益人的认识,并且认识历史归根到底仍在于认识自我和自我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人生。”[12]要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人生就不能抛离个体的生命活动和心灵体验,所以必须重视个人:“只有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合法的‘公民’,他们的价值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生命才有必须尊重的理由。 ”[4]121
“人”、“自我”、“自我生命”、“自我体验”等一直是王富仁学术活动中的关键词,他之所以走上鲁迅研究的学术道路也是源于自身的阅读体验而不是外部灌输的政治教条:“我对文学的爱好并不是从要搞文学研究的意图出发的,我直接接触的是文学本身,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不是学问家。我爱好文学比较早,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喜欢读文学作品。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没有先入之见。当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既不知道他属于一个什么流派,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他的思想。我读他的作品,哪个地方感动了我,我的印象就很深。当我后来搞研究的时候,我想到的首先就是文学作品,不是哪个理论、哪个学者的一个什么观点。”[13]而这种冥思独断式的研究不免招来“闭门造车”之讥,“几乎从我开始进入鲁迅研究界,关于鲁迅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议论,不仅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对我们这一辈人的鲁迅研究产生过一些异议,而且新一辈的青年对我们的鲁迅观也有过种种嘲笑和批评”[14]。但王富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为所动,他认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怎样崇高评价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或外国的现成文化学说,但我们的思想基点却都应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一种坚不可摧的社会愿望上,它不是在别人的文化学说中得到的,而是在自我的、民族的、现实的(现实生活或文化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没有这种确定不移的真诚愿望(不论它是大还是小),我们的所有文化都必将是软弱无力的,再广博的知识也救不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命。”[15]扎实、深入的生命体验和独到的人生感悟,使王富仁获得了比常人更为清醒的意识和犀利深刻的思维穿透力,这使得他常常可以穿越文化的幻象而发出前瞻性和预见性的呼吁。如在人人都为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额手称庆的时候,他指出中国文化的逆向性发展特征,提醒国人不要过分乐观;针对欧美理论和学术范式蜂拥进入国内学界的状况,在人人竞谈走向世界的喧嚣声中,他提出应该警惕欧美学术话语霸权的问题,在貌似公正、客观、平和的学术操作中很有可能遮蔽了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而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其论断的正确与睿智。
正因为以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社会人生感受为学术根基,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才饱含着生命活动深沉炽烈的激情;正因为能够坚守自我人生立场和不从流俗的思想品格,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才体现出理性思辨的严谨和犀利;正因为对个体具体的人生感悟的强化,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才体现出思辨的深刻独到与精细入微;正因为扎根于当下的文化语境,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才总能让人感受到恢宏阔大的气魄和视野,因而他博得学界前辈“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的赞誉[16]。但无论外界评价如何,他总能做到宠辱不惊,岿然不动。他说:
中国人好问: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说:我站在我自己这一边!
假若人们再问:你自己这一边到底是哪一边?
我说:我自己这一边就是我自己这一边!
大概人们还觉得不踏实,会进一步追问:你自己的这一边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是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我则回答:如果你在我的左边,我就在你的右边;如果你在我的右边,我就在你的左边;如果你在我的东边,我就在你的西边;如果你在我的西边,我就在你的东边……
人们觉得我说得太不具体。
我则觉得我的回答比任何人的回答都具体可靠。
——《呓语集之八十九》
这是一位有操守、有追求的当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立场的坦然自承,正如李怡所言:“王富仁在90年代的学术活动不仅没有在新锐理论的攒击之下退缩和‘失语’,不仅没有因文化环境的混沌而意志疲软,相反,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尊重自我的真实生命体验,也格外珍视自己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和独特的文化立场。”[17]
[1]陈安湖.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J].鲁迅研究动态,1987(9):48.
[2]张梦阳.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3.
[4]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
[6]师薑.学术沿革之概论[J].醒狮,1905(1):33-44.
[7]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J].国粹学报,1909(10):132.
[8]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1.
[9]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
[10]王富仁.新国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6(3):98.
[1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5.
[12]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78.
[13]王富仁,王培元.王富仁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1(11):101.
[14]王富仁.中国文化指掌图: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
[15]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29.
[16]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M]//樊骏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1.
[17]李怡.论王富仁的“90年代”[J].中国文学研究,200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