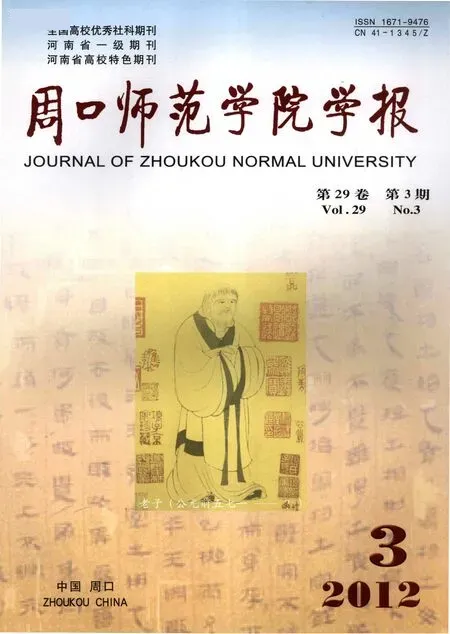卑微灵魂的折光:申艳诗歌印象
2012-01-28刘成勇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申艳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不算长,大概从2004年开始。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成为周口诗歌界的代表人物。这当然与她个人的才情和勤奋有关,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歌创作显示出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某种价值走向,这种价值走向就如诗评家霍俊明在评论1989年以来女性诗歌文本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葆有新的女性体验的同时,又向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伸展。”[1]申艳的诗歌既触及到女性的生命隐痛和灵魂创伤,又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与世界达成和解。她抓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激活了存在者的生命意识,从而赋予平凡以亮丽色调。这样一种“弯下腰”(《田陇上》)的低姿态写作,使申艳能够自如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世界、永恒与短暂、生命与存在等多重时空,在边缘地带发现了存在的价值,在卑微者身上发现了生命的高度,而在与卑微者的灵魂交流中自我的孤独与焦虑也得以抚慰和缓解。这也许是面对申艳的诗歌,需要细细品茗的原因。
一
申艳最为关注的是宇宙之中那些卑微的存在,在她的诗作中,出现了诸多卑微者的形象:受伤而执拗叫着的鸟、断成两截的蚯蚓、“裸着柔弱的蕊”的小花、一个写错的词语、太昊陵庙会上像蚂蚁一样聚在一起的香客、空阔静寂的黄泛区、飘动于麦浪之上的小村、被遗弃于路边的玫瑰、兀立田间的小叶杨、微弱亘古的温暖与光等,它们渺小、孤独,没有耀眼夺目的光彩,也没有恢弘阔大的气势,但就是这些“由野菜、茅草、蝼蚁/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生命”组成了和煦的春天(《田陇上》),那“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累积为成长”(《紫薇岛》)。与个人化的不及物写作和主流叙事择取宏大意象相比,申艳偏爱着这些更带有日常色彩的事物,让卑微灵魂在诗歌的高贵国度中自由翱翔,同时也使诗歌本身有了来自生活的基石,就像诗人雷平阳所说:“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2]
与那些宏大意象比起来,卑微者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它们是被忽略的群体。就像在喧嚣的城市,那在“匆匆而过的雨伞下”穿梭不息的“纤腰、肥臀、长腿、高跟鞋”构成了城市的主题,同样是构成城市一部分的“月季花、爬墙虎、梧桐树”(《雨滴和城市》)自然地被忽略了。但如果凝神细观,卑微者在自己独处的世界散发着悠然自足的生命光辉,在话语的边缘做着无人倾听的低诉,就好像“河滩上羞于说出自己名字的草”,它"被霜染黄,被水淹没/却不曾离开。等待风来的时候/发出卑微的低鸣“(《三川》)。它们会像月光下的菊花那样起舞(《月光下的石榴》),或者如萤火虫那样,尽管发出的亮光微不足道,却”活跃每一个发光细胞/掀开黑夜的一角/敲响吊钟海棠,阻止玫瑰的隐匿“(《萤火虫》)。”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醒它们的灵性“[3],唤醒的方式取决于观察者的姿态。也许”在大千世界中它们仅仅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一个被太多的人忽略的生命个体"[4],但当俯下身子,以一种平视的目光聚焦,这些卑微之物焕发出的是圆润柔和的生命光彩。
生命过程并非总是氤氲着恬淡和闲适,卑微者也常常经历着磨难或是厄运,在它们的内心世界也常常体验着难以言说的生命隐痛。一条蚯蚓被铁锹斩成两截,留下了“断肢和惊恐,匆匆钻回泥土”去承受那“卑微而真实的疼痛”(《蚯蚓》);一只受伤的鸟如果不是因为过于绝望或者是悲伤,它不会在暗夜里执拗凄厉地鸣叫,以至于“不肯与黑暗和解/一定要把夜晚啄破”(《一只鸟执拗地叫着》);一条流浪狗在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一定经历过无数次的驱逐、唾骂和殴打,它“皮毛肮脏,神情怠倦”,对这个赖以寄生却又给它不断带来伤害的城市保持着警惕,它的内心世界有着和漂泊者一样的孤独寂寞与惶恐不安(《过马路的狗》)。但卑微生命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于那些不期而遇却又无法摆脱的磨难或是厄运,不仅能够独自承受,而且能够悄然化解,让生命释放出它的绚烂和执著:
白雪皑皑。道路安静
冷不防,一束被弃的玫瑰
撞疼我的眼。鲜红的花朵
仍坚持着那一份火热
——《雪地玫瑰》
申艳说过:“我意识到唯有这种分行的写作,才能给予这卑微的个体生命以些微的补偿。”[5]在诗歌中,这些卑微之物被理解为生命个体,申艳以理解和爱为它们雕刻了生命群像。
一般而言,诗歌总是将美与永恒作为价值归依,但诗歌中承载美与永恒的意象在经过主体的刻意修饰之后,常常会染上文化色彩而丧失物之为物的自然属性。比如在中国传统诗词中,“杨柳”总是作为惜别之物出现,并带有一丝哀婉感伤的情调。当主体意识投射于杨柳之上,作为存在者的杨柳默然隐身,存在因此而被遮蔽。如何让物之物性也就是存在本身显现?申艳在诗歌中还原了卑微之物的生命过程,让生命自身言说出存在的意义。在《一只蚂蚁举着一只蚂蚁》中,诗人面对在夕阳斜晖里“一只蚂蚁举着一只蚂蚁遗体”的微型景观,看到了“生”与“死”这一最根本的存在问题。麻雀是自然界常见之物,“落下,是一小块跳跃的土地/栖息,是一小片枯卷的树叶”,甚至它的一次起飞,也不过是“行人的一次眨眼”,它不承担道德,也不承载任何希冀,赞美或是贬抑在赤裸裸的生命面前显得有些多余。它对生存的要求也仅仅简单到有虫子和麦粒可以果腹的程度,存在的真相在麻雀的起落之间被完整诠释。
申艳认为:“诗歌在形式上是语意表达可能性探索最尖端的方式,在艺术表现方面则是对事物真相或者心灵真实的最深度的挖掘。”她在诗歌中对生命本身进行了原生态描摹,她笔下的卑微之物也因此如海德格尔评论到的梵高的《鞋》一样,获得了柔和自足的艺术光辉,无言地昭示着自身的存在价值。
二
在申艳的诗歌中,更多的时候这种卑微的存在就是主体自身,是“遗失在粉墙之外”的少女(《剧场》),是沉睡在水底满身披绿的石子(《微澜》),是被生活提着的一只吊偶(《吊偶》),是月光下一枚成熟的石榴(《月光下的石榴》)……
作为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自我主体有着对爱情的渴望和追寻,有着充盈的生命意志,也有着女性存在宿命般的孤独与焦虑。《微澜》一诗塑造的主体形象具有代表性:
月色如霰,寒夜封在水底
寂静抻平微澜。一粒沉睡的石子
梦见自己满身披绿
瞬间的惊恐又拉皱寂静
黑色漫延,泼醒水边居住的女人
月光、寒夜与水为诗意空间调制出富有质感的冷色调画面,显示出宁静而又有些伤感的诗意氛围。寂静是永恒的主旋律,即使是因一粒石子的进入而中断,但泛起的微澜终被寂静拉平。时间消失于梦境,又被“满身披绿”的存在的久远与散漫所惊醒。 “瞬间的惊恐”是因为生命逝去的毫无意义,还是对未来的命运充满焦虑?但无论如何,寂静被打破,凝固的黑色四处流溢漫延,那居住在水边的女人从黑色梦幻中渐渐苏醒。诗作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女性写作的黑夜意识,显示出鲜明的女性写作的性别特征。抒情主人公在封闭状态中对自我生命进行隐秘体验和对女性心理真实做着深度挖掘,呈现出抒情主人公由懵懂无知到豁然觉醒的心路历程。觉醒之后,生命意识联翩而至。即如那“水边居住的女人”一样,在被黑色“泼醒”之后,就有了“让一只修炼千年的火狐/吸走我的魂魄,跟着月亮远行”的渴求(《我请求》),有了“渴望澎湃,又惧怕决堤”的犹豫(《汛期》),有了“涛声渺远。河床任大水来了又走/却漠视我整整一个季节的澎湃/只剩下水洼”的醒过之后的失望(《水洼》)和“往日的激情浓缩为/一粒盐,腌在自己的心头”的痛苦(《汛期》)。
“黑夜意识”是“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构建的是一个仅仅关涉女性自身的生命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女性“把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各种经验剥离到一种纯粹认知的高度”[6],这固然丰富了女性生命的内涵,使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充溢于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写作中,却也使女性在精神失控中一次次失去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机会。走出黑夜,走出“一个人的房间”是女性建构主体自我的必经之路。于是,申艳将痛苦与焦虑溶解于内心,不再执著于女性意识激荡下尖锐的但常常是空洞的追问。当伤痛袭来,是淋漓尽致、毫无顾忌的大声宣泄还是默然无声的暗自抚慰?在经过种种努力——逃避、遗忘和漠视之后,抒情主体渐渐直面自身伤痛,认识到“总有一些残缺一生相随”(《总有一些……》),也认识到“只有捻亮自己的心”才能“温暖手和脚”(《异乡》),只有打开窗,在与自然万物的接触中,那“体内凝固的黑”才会“立刻瓦解”(《早春日出》)。于是,在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心灵的磨砺后,无论是“被丢在季节的边缘”的孤独(《深秋或者被丢弃的石头》),还是“遗失在粉墙之外”的焦虑(《剧场》),或是贪恋红尘的畏怯(《在法海寺》),作者有了直面的勇气和能力:
不能故意回避
内心最深处的那些伤痛——
多年来,我反复对自己说这句话
今天,我偶然回过头来
却发现有几块疤痕
已被打磨得温润如玉
——《时间》
这是一种成熟之后的优雅,一种经历过岁月沧桑的淡泊,一种与伤痛和解之后的洒脱。这几乎是从一刹那中得来的人生感悟,诗人从那个在黑夜意识笼罩下膨胀的自我后面看到了那个小小的真实的自我面影:“不挺拔,不坚韧,不崇高”(《青竹》),“比沙子还要细小,沉在河底”(《河沙》),有一颗“卑微的心”(《紫藤》),有着“小小的,没有方向的爱”(《迷失》),即使是幸福来得也有些简易,只要“几棵鲜嫩的青草就能举起我的/惬意”(《简单的幸福》)。处身于卑微者的行列,诗人缓解了存在的焦虑,沉潜于生活的深处同样能够领略到存在的真谛。
但诗人并没有因卑微而自卑,也没有因渺小而藐视自我,而是“从心底郑重地发出/轻微得可以被世界忽略的声响”(《黄河日夜奔腾》),宣示着一种严肃的生活姿态:
风起的子时,我随着花影歌舞
需要观看或者倾听
一起把孤独摔得脆响
——《杂谈》
正是因为面对卑微生活的郑重和严肃,诗人尽管有过心灵的创痛、理想的幻灭和面对宿命的无奈,但她并未陷入到颓废或是放弃的地步,而是在自我疗救和自我安慰中羽化成蝶,以一种宁静的、宽容的,发现的心态重新面对世界:
即使空载,心
也可以抵达一个美好的终点
不要惧怕方向错误的行驶
也许一头撞在墙上也是一次
美丽的绽放,只要你的心路
有足够的宽度
——《心路的方向》
生命并不因卑微而贬值,相反,在卑微中能够发现生命的光辉,生命的高度和尊严由此凸显。这是一种含蓄内敛的生命品格,也是一种切实质朴的生命体验,从而使女性重构自我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生命平台。在《月光下的石榴》中,诗人为自我作了一幅理想的塑形:
我认真倾听,一枚成熟的石榴
讲解它甜蜜的结构。月光下
菊花起舞,流萤照明
蟋蟀以无字歌配着背景音乐
我的肺腑,充盈汁液
渐渐有了石榴籽的光泽
假如不是风在这一刻染黄了树叶
我也会端坐于枝头,让月光抱着
做一个红衣女郎多子的梦
而我现在要继续倾听它的讲解
希望自己的身体有它的甜蜜
更希望具备它的品质
满腹晶莹,才开口说话
凝固的黑夜开始稀释,月光出现在女性自我建构的天幕,尽管微弱模糊,却足以为那些在历史隧道中蝺蝺独行的生命个体照亮前行的道路,并能够发现自我同所处世界的关系。在《月夜哀伤》、《悼念》、《我请求》、《月圆的秋夜》等作品中,月光作为一种新的生命背景给诗人以启示和安慰。借助于月光,诗人走出了作为女性生命隐喻的黑夜,那曾经绝望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呼喊转化为更为理性的沉思和知性的探寻,在“满腹晶莹,才开口说话”的完美而又苛刻的企盼中,显示出告别黑夜的女性更为注重内在品质的修炼,这样一种内向“建构”而不是激切的“命名”的转向,透露出的是理想主义的高贵与女性自我拯救的另一种可能。
三
正因为主体自身的卑微,于是对于世间那些同样处于卑微地位的存在者就有了发现和理解的同情。面对干涸的湖底一条惊醒的鱼,“我能做到的,只是用单薄的身影/挡一挡太阳,让它在稍微的阴凉里/回到一个更长的美梦”(《一条鱼从梦中惊醒》),在一朵初开的野菊花的旁边,诗人感受到的是婴儿般柔和、纯真、温存的关注(《目光》),一个在诗中无所适从的逗号表现出的则是惶恐与窘迫:
低头沉默它不解
为何在我的诗里
找不到
自己的作用
失望也许是羞愧
腰更弯了脑袋
似乎也更大了
躲进我的指缝里
诚惶诚恐又踮脚眺望
——《逗号》
面对具有同样价值诉求的生命存在,诗人不再矜持于人类的崇高与伟大,而是谦逊地俯下身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自然万物做着物我无间的灵魂交流。古典文化追寻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只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主体性价值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成为自我的核心价值。人对自我的深入认识固然提升充实了生命内涵,但却颠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人成为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主宰者、无休止的索取者和贪婪的占有者。当人被无限膨胀的自我私欲所蛊惑,也就无视自然界中具有同样生命高度的“他者”的存在。申艳改写了这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降低了自己的高度,去发现那些同样绚烂和精彩的生命存在。就好像她在《日月或者陷阱》中所说的:“从低处仰望你能/看见,他们悠闲或者匆忙的挣扎”,也许只有这样,“才看清楚/一朵小花颤动着的,淡淡的蓝紫色/裸着柔弱的蕊。细微的香/在风中,和着雨后泥土的湿气/一只更小的蝶,藏不住/浅粉色的春心,绕着小花翻飞”(《田陇上》)。在自我主体温情意识的投影下,冲突达成和解,艰辛升华至收获,破碎隐喻着完满,即使是一块坚冰,也会在“在寻找一株幼苗的路上”“还原为柔情的润泽/回到草茎或者花蕊”(《一块冰赶赴春天》)。
诗人并不仅仅是发现了卑微者的存在价值,更主要的是在发现对方的同时,卑微者能够以自身的生命光辉点亮自我主体,给予主体灵魂以润泽、安慰和启示:
抖瑟的目光与一朵从容的野兰花
相遇。我看见它妩媚的开放
改变了危崖的坚硬
连大山都倾向于柔美了
峭拔的群峰倾过身来,流露着赞叹
点头鸣叫的鸟纷纷示意
微风吹来,野兰花转身
淡淡的兰,照亮我内心的深渊
——《危崖边》
在卑微者身上,诗人发现了一种自足的人生态度:“有没有蜂蝶相随也无所谓/农历四月,我曾开放在/紫藤的序列中,这已经足够”(《紫藤》),在与卑微存在的灵魂对视中,诗人的内心世界在起着一些悄悄的变化,“我的爱没有冻僵,只因/对岸的微光,尚在风中闪动”(《微光在风中闪动》)。在爱的驱使和感召下,诗人面对自然,感到“无法拒绝它们,渴望成为/其中的一棵,一朵,一滴/宁愿被覆盖,淹没,甚至融化”(《请不要在它们中间辨认我》),她愿意化作杜鹃、青草或是林泉,“占据一条石缝已足够/树叶绿,我就红/岩石坚硬,我就鲜艳”(《杜鹃峰》),“和路边的野菊花蹲在一起/学习宁静和忍耐”(《深入秋天》),而诗人最终则是希望“隐于丛林,不再猜测人心和命运”(《在丛林》),在“在原始的洁净中/避开喧嚣”(《溶洞遐想》)。在物欲化的今天,诗人的这种愿望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出脱成素心的忍冬花”的女性的高洁(《你的月亮》),同时也领略到返璞归真的惬意和自然率性的恬淡。
在所有卑微存在中,与诗人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尽管有着太昊伏羲的传说和老子故里的荣耀,但在一场场洪水的冲刷下,留下的似乎是亘古的荒凉、孤独和寂寞:“没有一座山停留在这里/日月从河流窥视天空/蒿草在河滩里摇曳往昔的洪荒”(《黄泛区》),但它在积蓄荒凉的同时,也孕育着生命的奇迹:“蒿草与麦子,尸骨与生灵/无穷地循环交替。” (《平原史》)苦难铸就了家乡的性格:“平淡中蕴含着个性的奇崛,散漫里深藏着生命的韧性”[7],正因为如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面对苦难的轮回选择的是坚守,在由犁铧、镢头、镰刀和独轮车支撑起的散漫悠长岁月中,一代又一代,“像这儿的庄稼,收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我的平原》)。这就是养育了自身血肉之躯和灵魂的家乡,它“亘古的空旷”(《豫东平原》)和“卑微的安静”(《从小李庄到彭埠口》)对诗人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召唤:
仿佛她丢失的一滴水
或是扬场时飞走的一粒麦子
——《彭埠口》
诗人不是如天涯羁客般抒发着绵绵不断的乡愁,而是以此在在此的姿态真切细致地言说着那些隐藏在家乡角角落落的记忆和伤感。这里有丢失的童年、苍老的母亲和装满细屑故事的老房子,有从绿到黄的麦浪、长满木耳的小桥和埋藏在黄土下层层叠叠的村庄,有寂寥的思陵冢、无人倾听的鱼鼓道情、朴拙稚气的泥泥狗……当然,家乡的皱褶中隐藏的不仅是记忆和伤感,在平原历史的尽头流淌过来的是辉煌与自豪:
最早的人是用这儿的黄土捏成的
最早的五谷是从这儿开始播种的
——《我的平原》
有什么理由离开呢?对家乡宗教般的执著与挚爱使诗人站成平原上的一粒麦子,“等待风雨雪霜,等待太阳月亮和收割”(《我的平原》),面对着家乡的空旷、平坦和宁静,诗人发出了铮铮誓言:
即使是一株稗草,我在家乡的田埂边
心中也是饱满的虔诚
……
即使是一块贴不上墙的泥巴
我身上也有洗不掉的黄土和黏性
——《家乡》
申艳以女性的细腻与温情在诗歌中为那些卑微存在刻画生命群像,“让它们在自己的文字里站立起生命的尊贵”。事实上,在建构他者生命尊贵的同时,诗人也使“自己的生命尊贵站立起来”[8]。主体与他者在生命的节点上建立起内在关联,在生命意识的烛照下,申艳的诗歌折射出的是卑微存在的灵魂之光。在谈到陈染的《私人生活》时,学者戴锦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那在阳台(私人、个人空间)长得过大的龟背竹是否该移到窗外的世界中去?女性写作是否应走出'私人生活'再度寻找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部?”[9]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女性写作显示了其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可能性,完成了从“从'闺房'到'旷野',从'个人'到'万物'的转变”[10]。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申艳的诗歌以其对卑微存在的深切关注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女性写作转型的轨迹,这也许是申艳诗歌的意义所在。
[1]霍俊明.1989-2009中国女性诗歌的家族叙写[J].南开学报,2010(2):23-29.
[2]雷平阳.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J].文艺争鸣,2008(6):82-83.
[3]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
[4]申艳.在诗行中品味生命的尊贵[EB/OL].[2011-10-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51fbd1260100b3lm.html.
[5]申艳.我的诗,我在它们的对面[EB/OL].[2011-10-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51fbd1260100fswz.html.
[6]翟永明.女人.黑夜意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23.
[7]申艳.我是你的看麦娘[EB/OL].[2011-10-15].http://blog.sina.com.cn/s/blog51fbd1260100fsx0.html.
[8]申艳.在诗行中品味生命的尊贵[EB/OL].[2011-10-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51fbd1260100b3lm.html.
[9]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206.
[10]张莉.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十年[J].文艺争鸣,2010(8):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