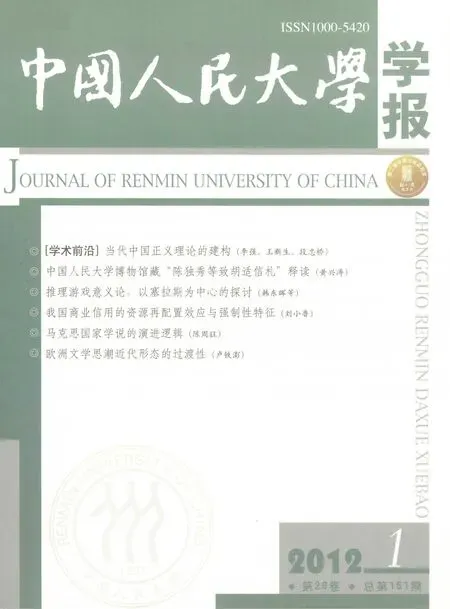欧洲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过渡性
2012-01-23卢铁澎
卢铁澎
文学思潮理论研究是文艺学领域长期以来的荒僻之地,偶有涉足者却鲜能持续开拓。从根本属性而言,文学思潮不是逻辑归纳的抽象类型,但从历时状态考察,则可见其历史形态的客观性。忽视历史形态的研讨,文学思潮问题的解答就无法摆脱概念游戏的窠臼。在文学思潮的所有历史形态中,近代形态尤其复杂,更有必要深入辨析。本文拟以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争议为中心,探讨文学思潮近代形态的主要特征。
一
近代欧洲文学史上有三种文学: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而在文学思潮研究领域,除了古典主义是公认的文学思潮之外,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否文学思潮,迄今尚无定论。1980年,国内出版的 《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1]将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都确定为欧洲近代的文学思潮就招致了强烈质疑:“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吗?”有人以此为题著文加以否定,主要从 “什么是文学思潮”的理论标准和有无先例的研究实践两方面来判断。批评者主张,文学思潮是 “(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由有共同的纲领、共同的创作理论以及相同或近似的艺术风格的作家群掀起的思想潮流。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2]尽管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在风格的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共同性,但在纲领和创作理论上却是“零碎不全”,甚至 “相互抵牾”,都没有达到“共同”、“统一”。从研究实践方面看,“在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也不曾把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来论述,而是把它们看做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本间久雄著,沈端先译,1929年,开明版),以及我国近几年出版的 《辞海》、《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上册)、《外国文学简编》(朱维之、赵澧主编,上册)、《欧美文学史》(石璞著,上册)、《法国文学史》(柳鸣九等著,上册),等等,都持非 ‘文学思潮’说”[3]。所以,结论自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都没有资格叫做文学思潮。”[4]被批评者针对这两方面的指责进行反驳,认为批评者实质上是把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相混淆来界定什么是文学思潮,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性,不符合文学史事实。以浪漫主义来说,若以“共同”、“统一”的定义考察,浪漫主义也达不到,也不能称之为文学思潮;而且,批评者还凭古今专家权威有无首肯来作为判断标准,也是不可取的研究态度。[5]无独有偶,在国外,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早在其1978年出版的 《文学原理》这部理论代表作中,也否定了欧洲近代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是文学思潮,只承认古典主义是文学思潮,而且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思潮。波斯彼洛夫的依据也是从以上两方面着眼,他认为文学思潮是具有共同创作纲领的流派、作家集团的创作,古典主义有共同纲领,有独立自觉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没有提出和自觉奉行的共同创作纲领,不是古典主义那样独立自觉的世界观,只是一种类型性的“思想方式”;而且,在文学研究史上没有人谈到古典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内存在有文学思潮,“显然是因为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学中,从埃斯库罗斯时代到莎士比亚时代,都还没有明确地形成思潮”[6](P172)。因此,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不是文学思潮。
为什么国内外否定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的依据似乎基本一致?当然,不能排除国内持论者受波斯彼洛夫观点的影响——在中译本问世之前已阅读过俄文或其他外文版波斯彼洛夫的 《文学原理》或相关文献。无论是否不约而同,否定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的两方面依据都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思潮研究必须深究的理论问题。其中,有无研究先例或权威的判断只能是学术论证的一个方面,不足以作为理论发现的决定性条件。尤其是前人或权威尚未关注和研究过的问题,若必须依据他们的判断为标准,岂不是缘木求鱼?判断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否文学思潮的关键,还是最基本的定义问题——什么是 “文学思潮”?前述否定论者明显都持 “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国内持论者并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仅以 “一般认为”就自命权威,似乎不太妥当。波斯彼洛夫在文学意识形态本性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性,通过欧洲文学史的考察,形成其流派创作中心论的文学史观。在对古典主义的重点分析中进一步探究流派与思潮的关系时,提出了自己的 “共同纲领流派创作论”(下称 “共同纲领论”),这一观点能否作为界定文学思潮的正确标准,也应该结合文学史事实进行考察和鉴别。
二
何谓 “文学思潮”?波斯彼洛夫的回答毫不含糊:“文学思潮”是指 “某个国家和时代的那些以承认统一的文学纲领而联合起来的作家团体的创作”[7](P175), “统一的文学纲领”—— “共同纲领”是怎样产生的?他说:“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8](P173)某一国家某一时代的作家集团在这种明确的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这种纲领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及其作品的完整性,这时, “文学思潮”即告产生。[9](P173)在波斯彼洛夫看来,一个流派或由不同流派构成的作家集团有没有 “共同纲领”和是否明确地提出 “共同纲领”,作家们是否以这种明确的 “共同纲领”指导自己的创作,这是判断某一作家集团的创作是否 “文学思潮”的绝对标准。虽有艺术和思想的共性,但没有 “共同纲领”的作家集团的创作,就只能称之为 “文学流派”。这一标尺十分明确,似乎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以波斯彼洛夫心目中的文学思潮典范——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来考察,这一标尺也碰到了历史事实的障碍。波氏自己就承认,古典主义的共同纲领是从马莱伯到夏普兰再到布瓦洛历经数十年才形成的。那么,真正称得上是古典主义文学共同纲领的应是布瓦洛的 《诗的艺术》,这部诗体文学理论著作是公认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 “法典”,其问世时间是1674年。而高乃依、拉辛等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作家的主要创作都在1674年之前已完成,尤其是高乃依在1636年发表的悲剧代表作 《熙德》,因为在内容上有违当时专制王权的政治、道德要求,从而受到了斯居代里等人的猛烈攻击和法兰西学院的指责,引发了一场论争。由于此次论争,夏普兰代表法兰西学院起草的 《关于悲喜剧 〈熙德〉对某方面所提意见的感想》迟至1637年年底(或谓1638年年初)才正式发表,即使把这篇代表官方意见的文献视为已基本形成的古典主义“共同创作纲领”,《熙德》也很难说是自觉遵循古典主义共同纲领所创作的作品。何况夏普兰的《关于悲喜剧 〈熙德〉对某方面所提意见的感想》不过是对这场剧坛论争的一篇评述,并非具有严密逻辑的系统的 “纲领性”理论著作。被公认为古典主义 “纲领”的布瓦洛的 《诗的艺术》,也迟至波氏声称 “以归附古典主义思潮的戏剧家身份出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性地赞同了它的纲领”的莫里哀死后一年才问世。如此,以波氏的标准,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也不能算是 “文学思潮”。如果再用波氏的 “共同纲领论”去衡量其他早已公认的文学思潮,结果也会令人瞠目结舌。例如,英国浪漫主义没有法、德浪漫主义那样的自觉意识,英国诗人无人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如果要以有一个 “有意识地形成的纲领”作为标准的话,那么,英国就不存在 “浪漫主义”文学思 潮。[10](P127-131)而 英 国 的 现 实 主 义 文 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它不曾和敌对派浪漫主义进行过公开的斗争,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纲领,也见不出有什么哲学思想的基础”[11](P730)。
波氏在 “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的误导下,对近代欧洲的三种文学进行厚此薄彼的定性,只承认古典主义才是文学思潮,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文学思潮,毫不犹豫地把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贬为类型化的思想方式,而不是文学思潮。他认为作为思想方式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可以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思潮的作家所运用。为此,他还列举了伏尔泰、卢梭等一批法、英、俄等国的作家为例加以论证。他说:“在18世纪的法国,伏尔泰是最杰出的启蒙作家,就其创作的思潮而言,他是属于古典主义的。而在法国启蒙作家中间,他的对立者是写了感伤主义小说的卢梭。19世纪十至二十年代初的英国,雪莱就其创作思潮而言是明显地属于浪漫主义的,他却是一个启蒙思想的诗人。在19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柯罗连科等人是启蒙主义者”,因此,他断言,“把启蒙运动作为文学发展本身的特殊阶段是没有任何道理的”。[12](P186-187)
波氏的观点和论证恰好暴露了 “共同纲领论”思潮观对文学思潮历史形态的无视或无知。在他眼里,文学思潮仿佛是横空出世,一下子就以一种成熟、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文学史上,没有经历从雏形到成熟过程的种种历史发展形态。正是这种狭隘视角,使他看不到文学思潮历史发展事实上存在着的丰富形态:既看不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在历史形态上所具有的质的区别,更看不到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与古典主义都是作为文学思潮存在所具有的近代精神文化历史类型的过渡性特点。
三
苏联美学家卡冈曾指出,文化类型 “像所有活物一样,经历形成、繁荣和衰落的时期,它能够在文化的活的躯体中,同消亡着的文化类型的萎退器官或者 (而有时和)同正在成长的文化类型胚胎共存并处;最后,一种历史类型的文化被另一种排挤掉的过程,每次总产生过渡型文化。在过渡型文化中,过去文化和未来文化的特性处在活动的平衡中,或则相互矛盾地冲突和对抗,或则相 互 趋 向 协 调”[13](P307-308)。 从 文 艺 复 兴 到 古典主义再到启蒙运动的文化都是具有这种过渡型特征的文化类型。“文艺复兴的本质正在于探索关于世界、人、艺术的综合而完整的观念;文艺复兴文化虽然已经摆脱宗教神秘主义,但是它还不能成为无神论的;它推崇现实的、尘世的人,但是没有把人本主义引导到个人主义的极端;它确证认识、理性和思维的最高价值,但是不把它们同信仰、体验、享受对立起来。虽然17世纪已经无情地摧毁了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幻想,暴露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所有矛盾,然而在启蒙运动时代,仍然进行了英勇的、虽然是没有前途的努力,以创造人、艺术、世界的完整模式……这样,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乌托邦的最后回声。”[14](P319-320)只 有 到 了 19 世 纪,新 型 文 化 和 作为它的基础的新型意识才以纯粹的和历史原型的形式展开。卡冈对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过渡性文化史类型的特质的概括,统摄着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文学思潮。
作为文化史上的近代,是封建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时代,过渡性是其总体特征。那么,这一历史阶段内的文学思潮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文化类型的过渡性,故可称之为过渡型文学思潮。具体说来,这种过渡性首先表现在文学思潮主体意识自发与自觉的交织。由于是过渡时代,文学思潮的群体性既有古代时期自发性的沿袭,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觉性,但远未达到整体的自觉。其次,在文学思潮构成上,仍然以创作、接受思潮为主流,批评思潮比古代自发期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并没有在总体上与创作、接受思潮同步。再次,支配群体文学活动的文学观念体系虽然出现了与自发型文学思潮对立的新规范,但没有完全摆脱原有规范体系的限制,新旧思想既互相冲突又相互依存,只有在最后的临界点上,新思想才以绝对优势战胜旧观念,跃转为新的文学思潮形态。这种过渡阶段的特殊性使近代时期的文学思潮难以定位,甚至被人们否认其是文学思潮。
无论是人文主义、古典主义,还是启蒙主义,它们的文学观念规范体系及其所支配的文学活动都贯穿着新旧两种文学意识的矛盾,并且也“时而或多或少是尖锐的冲突,时而或多或少是紧密的交织”[15](P319)。但丁 《神曲》的宗教寓言、神秘主义与写实的笔触共存一体,神学的构思中放射出思想和艺术上的世俗追求的新世纪曙光。这种过渡性也体现为人文主义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各行其是。例如,在戏剧方面,对情节因素的强调和倾向于类型化的性格塑造这种理论主张,并没有为代表文艺复兴最高文学成就的莎士比亚所接受,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倾力而为的是人物心灵的全新探索,以展示人物个性的千差万别。莎士比亚有自己的主张:“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16](P67)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形成于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过渡时期,它所崇奉的理性文学准则,也无不体现着新旧意识的混杂。布瓦洛的 《诗的艺术》把真善美的统一推举为文艺的最高标准,洋溢着新时代的精神,而这部古典主义艺术 “法典”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又都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文艺思想的翻版。伏尔泰虽然崇尚古典主义的典雅风格,称颂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才是文明的艺术,拉辛胜于莎士比亚,但其文学观点却与古典主义的艺术主张存在着质的差别。古典主义尊重古代传统而趋于泥古,伏尔泰却认为,“在任何方面都逐字逐句地学步古人是一个可笑的错误”,因为今日的一切已与古代大相径庭。[17](P323-324)古典 主 义 强 调 恪 守 艺 术 规 则, 而 伏尔泰却宣布,“几乎一切的艺术都受到法则的束缚,这些法则多半是无益而错误的”,即使有些法则是正确的,但对创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像荷马、维吉尔、塔索和弥尔顿这样的伟大作家“几乎全是凭自己的天才创作的。一大堆法则和限制只会束缚这些伟大人物的发展,而对那种缺乏才能的人, 也 不 会 有 什 么 帮 助”[18](P318-319)。 他对天才和想象的重视,更是超越了古典主义的局限而接近浪漫主义的畛域。与其将伏尔泰这样一位作家粗暴地归之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还不如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合情合理。何况这位启蒙思想家还开辟了哲理小说这一富于启蒙特色的艺术形式,仅此就表明他代表着一个并不属于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比起大多数18世纪的启蒙作家来,卢梭身上显示的趋新意识更突出。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因为他排斥理性而推重感情,否定科学、文明而号召 “回归自然”,这些观念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可是,他否定科学艺术的理由不过是柏拉图观点的重复,他对感情的推重,也只是表现了18世纪法国已经存在的 “善感性崇拜”这一 “潮流倾向”[19](P213-214),他对 艺 术 的 否 定 甚 至 使 他 不 惜 加入清教主义者行列,支持日内瓦对一切戏剧的禁演,扮演了一个 “禁欲美德斗士的角色”[20](P230)。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感情的赞赏和对自然的向往,并不是建立在否定文学与艺术的基础上,恰好相反,他们主张诗歌是 “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21](P17),诗歌的目的是要引发一种激情,使它与失去平衡的快感并存,诗歌的作用并不是卢梭所说的那样使人浪费时间、败坏德行,而是直接给读者以愉悦,通过愉悦激发人们的同情心,矫正人们的情感。华兹华斯等甚至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22](P13-15)在卢 梭 那 里, 文 学 艺 术 与 情 感 和 自然是对立的、矛盾的,他否定前者而肯定后二者;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文学 (诗)与情感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否定前者也就是否定后二者,因为前者——文学 (诗)恰恰是后二者——情感和自然的必然产物。由此可知,这是两种差距极大的文学观念。韦勒克在谈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时的一段话也可引以为证。他说,在研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源头时,“卢梭自然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甚至被称为全部浪漫主义的源泉;其中有J.J.泰克斯特这样的友人,也有想把浪漫主义贬低为卢梭主义这样的敌人。然而,如果把卢梭说成是这类姿态的激发者,那么,对他的估计是不恰当而又过分的;他不过是促进了这类态度的传播,并没有制造这类态度。但是,所有这些分散的法国学术著作,都分别地预示出了浪漫主义的态度、思想、情感,而不是18世纪的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运动”[23](P152)。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卢梭与伏尔泰一样,属于过渡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不能贸然地把他从该思潮中开除出去,并将其硬塞进后来的文学思潮。再看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他在文艺观上的过渡性质更为明显。他同时主张种种不同甚至相互之间极为矛盾的文艺观点。例如,他对诗歌的看法颇重激情。他认为,诗人应是集情感和天才于一身的人,是充满悲剧性的忧郁的人物,诗人 “执笔之前,他肯定翻来覆去,面对眼前的题目,战栗不已,夜不能寐,深更半夜爬起来,套上睡衣,光着双脚,借着夜明灯的光亮,连忙手不停笔,挥洒草稿”[24](P72)。诗人要是没有狂飙般的情感,就做不出好诗来。显然,在狄德罗眼里,“强烈的个人情感的专注,乃是衡量诗歌伟大品质的标准”[25](P62)。推崇天才,重视情感,这不正是浪漫主义的诗歌观吗?如果仅仅凭此而论,狄德罗的文学观当然可以划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了。可是,狄德罗还有与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完全对立的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例如,他倡导市民悲剧这一新体裁,但他 “几乎完全是用新古典主义理论所能接受的说法揭橥的。他精心阐发了一个戏剧体裁的等次体系,其中家庭悲剧,似乎填补了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空白,而反讽喜剧和惊奇剧,则降低至下等的次要体裁的地位。悲喜剧,他明确地斥之为一种不良体裁,因为它混淆了由一层天然屏障截 然 分 开 的 两 种 体 裁。”[26](P63-64)在 后 期 的狄德罗看来,“艺术,或者至少就戏剧这门艺术而论,显然并非是指单纯的情感主义,而是指摹仿自然;当然,所谓 ‘自然’,狄德罗指的是典型者、普遍者、假想中的自然和谐。”[27](P64)除了上述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观点以外,在狄德罗的著述里,还可以看到 “19世纪布尔乔亚的自然主义”,甚至 “象征主义的诗歌观念,也不乏先声”。[28](P75)面对狄德罗这样充满矛盾性和复杂性的文艺观,如果只看到他这种难以捉摸的非连贯性而认为其文艺观无足轻重,或者相反,“大胆地挑选出我们认为属于他的基本观点的那些内容,而他的其他学说统统视为左道旁门,或者是对时代所作的妥协,而一笔抹煞”[29](P53),都是错误的。就文学思潮而言,对待诸如狄德罗这样的复杂文学观念,应该客观地承认其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过渡性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其多变而且多样的观念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在理论层面上确认这种共同特性所具有的文学思潮范型属性。
“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的代表人物波斯彼洛夫正确地认识到,文学基本特征的阐释离不开对文学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发掘;而前者的阐明,也有利于后者的研究,两者相互依存。但在文学思潮的理论研究中,波氏并没有彻底贯彻这一科学思想,从而在文学思潮特征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研究方面得出了片面的结论。因此,只有摆脱 “共同纲领论”文学思潮观狭隘视野的囿限,我们才有可能从宏观、系统的历时维度上发现文学思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认近代文学思潮所具有的 “亦此亦彼”、“或此或彼”的过渡形态,更有效地把握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规律性,促进对文学思潮基本特征的深入认识。
[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组编:《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2][3][4]富扬:《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吗?》,载 《广西大学学报》,1984(2)。
[5]陈伯通:《关于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思考——兼答富扬同志》,载 《广西大学学报》,1984(2)。
[6][7][8][9][12]格·尼·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5。
[10][23]R·韦勒克:《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3][14][15]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6]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载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7][18]伏尔泰:《论史诗》,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9][2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1][22]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4][25][26][27][28][29]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