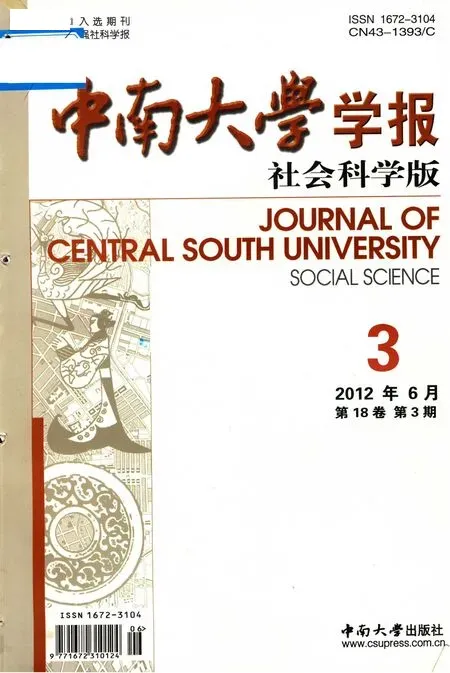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2012-01-22熊海英
熊海英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56)
惯常谈到唐音、宋调,往往指出这两种诗歌审美范式对自然与人文世界的表现各有偏重。宋代从西昆体开始的“资书为诗”发展到江西诗派的“闭门觅句”,正如严羽所言,“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成为宋调的典型特征。南宋诗人的创作大多属江西派,杨万里却以“活法”独辟蹊径、自成一体——“诚斋体”。论者皆称其创作走出书斋、师法自然,是南宋诗风转变的关键。不过,诚斋体的创作并非简单地将视角、诗笔从书本转向大自然,回归唐诗审美范式,而是承继唐诗渊源、在江西派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诚斋体”诗的“自然”特质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涵义。
一、写眼前景、身边事,注意力从内心转向外界自然
概括地讲,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偏重对人文意象、主观世界的关注和涵咏,正如李彭所言“以彼有限景,写我无穷心”(《次九弟游云居韵兼简郑禹功博士》),对外界自然的依赖降低;江西派的创作由天分转向学力,由直寻转向补假,由缘情转向尚意,诗中大量用典,增添了渊雅风味;而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意象转换与语言锻造,更表现出高层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需求。宋调打破并改变了唐诗情景交融、主客平衡的审美范式。到了南宋中期,风会始有转变,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为代表的中兴大诗人在创作中将目光重新投向自然,创作成绩最为特出的就是杨万里。杨万里曾称赞友人“四诗赠我尽新奇,万象从君听指麾”(《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之四),“中原万象听驱使,总随诗句归行李”(《跋丘宗卿侍郎见赠北诗一轴》),自己更以自然为诗材,在自然中寻找灵感。对于帮助杨万里写出“诚斋体”的“活法”,钱钟书的解释是:“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1](255)《荆溪集》492首诗中,写景咏物之作占六分之五。在杨万里现存的4200余首诗中,写江山风月美景、日常生活情趣的也是绝大多数。“三月风光一岁无,杏花欲过李花初。柳丝自为春风舞,竹尾如何也学渠”(《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诗》),渲染出明媚绚烂、喧哗闹热的春潮涌动;“旋裁蜀锦展吴霞,低低挂在秋山半。须臾红锦作翠纱,机头织出暮归鸦”(《夜宿东渚放歌三首》之三),活画出山水间云彩与暮气的飘忽不定,光影变幻;“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春来一日深”(《过杨二渡》),春来无声,诗人却从渐深的柳枝与草色间发现了它的踪影。“芙蕖落片自成船,吹泊高荷伞柄边。泊了又离离又泊,看它走遍水中天”(《泉石轩初秋乘凉小荷池上》),莲瓣飘落,风凉水清,是秋天来了。正所谓“报答江山唯有诗”,置身自然的诗人只是敏锐体察、细腻描画,却不在物象中寄寓深意。杨万里在《送郭才举序》中说:“人之聪明有不用,无不达也。……用而精,精而达,物何坚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穷哉?”又如《观化》所云“须把乖张眼,偷窥造化工”,“只愁失天巧,不悔得诗穷”,诗人所做的就是以其“聪明”去体察、以其妙笔去表现,不遗漏造化的精巧微妙,令“天亦不能逃于人”。[2]卷82
诚斋诗中的色彩描写,更能鲜明体现出诗人诗笔对自然界的偏爱。大自然本是五彩缤纷,呈现在杨诗中,颜色也同样丰富。如“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早春》);“一路东皇新晒染,桑黄麦绿小枫青”(《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七首》之六);“霜红半江金罂子,雪白一川荞麦花”(《秋晓出郊二绝句》其一);“草色染来蓝样翠,桃花洗得肉般红”(《明发海智寺遇雨》二首之一),诗例不胜枚举,故陈衍评杨万里诗“体物浏亮”。[3](125)从杨诗中浓烈明朗、丰富真实的色彩就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注意力已经从内心转移到客观世界。唐宋诗史上运用颜色词特点比较突出的诗人有李商隐、李贺、姜夔等,一经比较就可明显看出李商隐等人对颜色的表现具有高度选择性。李贺好用高浓度、冷色调的颜色词,尤其是红、碧、黑,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又以之形容鬼火、恨血一类意象,形成对其郁结幽深心境的象征;李商隐则喜用青、白、金等中间色类,这有助于暗示其情感的朦胧迷惘、暧昧温柔;姜夔诗词中的颜色也是冷调,但单纯明净,且常用以形容莲、梅、雪、月等意象,喻示其摆落俗世的高洁性情。这些诗人笔下的颜色多非外物的真实色彩,而是诗人想象中的颜色,它有助于渲染情调氛围,构成从属于诗人主观意念的诗境。反观杨万里诗中的色彩,显然更接近自然界和生活的真实;且亦不象一般文人那样偏好清雅色调,而是如农村年画一样热闹有力,呈现一种直接胎息于自然的原生态的美。
二、重视性灵本真在诗歌创作中的保持与表现
杨万里不但以诗歌生动逼真地再现客观自然,其创作亦体现其性灵的天真自然。论诗者往往以杨万里比拟李白,如刘克庄云“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太白”。[4](43)袁枚谓诚斋诗:“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5](272)吕留良在《宋诗钞·诚斋诗钞》中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其实杨万里与李白的诗歌风格并不相似,相似处其实是诗人的性灵天分在诗歌创作中的保持与表现。
论诗者皆道“诚斋体”诗有奇趣,“奇”在何处?其实就是思出常格,对自然外界、物我关系有特殊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理解,在诗歌中突出表现为想象奇特、比拟新颖,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情感。传统诗歌中当然也有不少这类主客、物我之间互动交融的表现。如杨万里《宿小沙溪》其二云:“诸峰知我厌泥行,卷尽痴云放嫩晴。不分竹梢含宿雨,时将残点滴寒声。”而苏轼《新城道中》云:“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也许正是杨诗范本。杨万里《过西山》“一年两踏西山路,西山笑人应解语:‘胸中百斛珠墨尘,雨卷珠帘无半句’!殷勤买酒谢西山:‘惭愧山光开我颜!鬓丝浑为催科白,尘埃满胸独遑惜’”,与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同一机杼。杨万里写月亮:“屋角忽生明,山月到庭户。似怜幽独人,浑夜约清晤。我吟月解听,月转我亦步。何必更读书,且与月联句。”(《感秋》)而李白早已写过:“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
诗人与自然万象发生情感共鸣,彼此交心、会心、知心。他感受到落木的幽怨,“举头视嘉木,向人惨无姿。渠乃怀秋悲,瑟瑟声怨之”(《感秋》);与山宾主相得,“我行山忻随,我住山乐伴”,“有酒唤山饮,有簌分山馔”(《轿中看山》);杨柳依依,为惜别情,“柳线绊船知不住,却叫飞絮送侬行”(《舟过望亭三首》);梅花幽独,恨少知音,“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明发房溪》)”;《彦通叔祖约游云水寺二首》(其二)云“风亦恐吾愁寺远,殷勤隔雨送钟声”,《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归得绝句》(其一)又云“湖山有意留侬款,约束疏钟未要声”,一殷勤、一约束,足见山水风月皆有情思。与传统诗歌中的诗人移情于物不同,杨万里笔下的山水云月、花草树木不光有情感,更有自己活泼、独特的灵性,能与诗人互动,产生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欲借微凉问万松,万松自诉热无风”(《中元日早起》);“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暮热游荷池上》);它们那样调皮,竟然与诗人谑戏,“溪边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迟出。归来闭门闷不看,忽然飞上千峰端”(《钓雪舟中霜夜望月》);“两朵三枝梅正新,不疏不密最欢人。花枝夹路嗔人过,径脱老夫头上巾”(《至后与履常探梅东园》);它们也有嫉妒之情,争胜之心,“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似妒诗人山入眼,千峰故隔一帘珠”(《小雨》);“岭下看山似波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陡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这些诗歌皆令读者忍俊不禁。再如《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其一:“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冰。忽然觉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独自行。”写玲珑冰月,怀抱幽独,悄然独行。《过五里径》云:“野水奔来不小停,知渠何事太忙生。也无一个人催促,自爱争先落涧声。”写溪水伶伶俐俐,争先自爱。“鹭鸶已饱浑无事,独立朝阳理雪衣”(《壕上书事》);“小蜂得计欺侬睡,偷饮晴窗砚滴干”(《南溪山居秋日睡起》);“却是蜘蛛遭积雨,经纶家计趁新晴”(《蛛网》),在诗人眼中笔下,鹭鸶闲雅,小蜂狡黠,蜘蛛勤于家计,各具性情,无不活灵活现。杨万里诗中不仅有物我互动,更写出万物间的情意交融。如“着尽工夫是化工,不关春雨更春风。已拼腻粉涂双蝶,更费雌黄滴一蜂”(《春兴》),春装点万物,即使是细小如蜂须蝶翅,亦是一样的精心着意。如“自觉玉容微婉软,急将翠掌护婵娟”(《宿新丰坊咏瓶中牡丹因怀故园》);“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池》);“青山自负无尘色,尽日殷勤照碧溪”(《玉山道中》);“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桂源铺绝句》),……诗例甚多,毋庸赘举。
传统诗歌常用移情手法,如“数峰无语立斜阳”,或者“泪眼问花花不语”“红萼无言耿相忆”等等,物与人同情,实即是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强加于客体,就像月亮接受太阳的投射而发光,故诗中物象多是默默承受、无语旁观的状态。反观“诚斋体”诗中客观物象情态之活跃、丰富,则说明其创作并非简单的“移情”,仅从比喻、拟人等修辞层面来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杨万里在《庸言》中进一步提出“观吾心,见天地;观天地,见吾心”,[2]卷九四孟子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杨万里认为这个“赤子之心”是有喜怒、有哀乐,能“觉万物之痛痒”“爱及乎万物”的。[2]卷九二诗人遂与万物为友,泯灭大小、主客之界限。赤子之心本不知贵贱,天性亦无分雅俗,诗人用一颗初心去体悟,发童心之所感,言童心之所欲言,与万物嬉戏相亲。诗歌是艺术,从艺术形成的角度来看,艺术创造与赤子的游戏本质相通,都是为了一种乐趣。而从诗歌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看,王国维曾言:“诗人心中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6](15)杨万里《应斋杂著序》则称:“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2]卷八三似乎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对于充满生命活力,保持性灵之真的他来说,自身的生命律动与万物相通,其实就并没有轻视与重视之分别,刘过称杨万里“达人胸次元无翳,芥子须弥我独知”(《投诚斋》其六),可谓的当。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在诗中沆瀣融合,无分彼此,再现大自然的同时也表现了其性灵的本真。
三、表达方式的返璞归真
诗歌发展到宋代,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变得语言精粹、句雅味醇,一些书面词汇渐渐定型,一些意象已经积淀了有明确所指的涵蕴,甚至因为被反复沿用而显得陈腐,不能给读者新鲜的感受。而学诗之人饱读名言佳句之后,作诗最易“搜猎奇书、穿穴异闻”,如与人决战而利器在身,不能不倚助,结果遂如钱钟书所言,诗人渐对自然失去了直接接触的亲密和新鲜感,失去了自己的视角。[1](256)“诚斋体”则直如王国维所言,“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6](13)杨万里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题唐德明建一斋》),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彻底摒弃前代写作成法、惯用成语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性灵之本真去感受,用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方式去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出各种未经人道和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
如梅花傲雪凌霜,是士大夫喜爱的人文意象。杜甫写白梅,有“雪树原同色”(《江梅》)的佳句,王安石对红梅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红梅》)的感叹,吕本中描写腊梅则云“学得汉宫妆,偷传半额黄”(《腊梅》)。杨万里《蜡梅》云:“江梅珍重雪衣赏,薄相红梅学杏装。渠独小参黄面老,额间艳艳发金光。”诗歌采用对比衬托之法,让江梅、红梅、蜡梅在同一画面里绽放,信手将杜、王、吕的诗境纳入己诗,却不沿袭咏叹梅花高洁品格的传统立意,而是切实写出眼前腊梅的勃勃生气、光彩照人。再如描写月亮,古来名篇佳句极多,月亮意象中已经积淀了丰富的人文意涵。杨万里也很喜欢写月亮,如《初九夜月二首》其一:“珍重姮娥住广寒,不餐火食不餐烟。秋空拾得一团饼,随手如何失半边”;其二:“也知月姊是天姝,天上人间绝世无。雾刷云撩何不可,却须插一水精梳”;《舟中买双鳜鱼》云:“江神挈月作团扇,一夜挥风卷波面”;《携酒夜饯罗季周》云:“淡月轻云相映着,浅黄帕子裹金盆”。月亮在杨万里诗中,有时是仙子的灯笼,有时是江神的团扇,或是素娥头上的水晶梳,抑或是望舒所驾冰车的轮子被冻凝了,等等。形容月亮的这些意象都来自日常生活而非典籍,虽然感觉有点凡俗,读者不一定喜欢,但无疑会产生审美经验上的新鲜感。杨万里将“梅”、“月”等传统意象上沉淀附着的人文内涵全然撇去,纯粹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描绘,等于是自愿放弃武器,赤手空拳去生擒活捉。清人翁方纲评其为诗“敢作敢为”,“颐指气使,似乎无不如意”,[7](1437)固然意在贬斥,想必也感受到杨万里具备普通人不及的胆气力量。钱钟书说杨万里善于以“创辟”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耳目观感,[1](254)如果了解古典诗歌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就能了解身为宋人的杨万里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了不起。
在“诚斋体”诗中,大批传统意象固有的涵义、固定的感情色彩被尽行剥除,而赋予当下最真切、最朴实的感受,得到新鲜的内涵。如他写雨落林中,“雨入竹林浑不见,只来叶尾作真珠”(《二月一日雨寒》);写清晨的日光,“金篦落地拾不得,却是穿窗晓日痕”(《晓起》)”;写闷热蒸人,“也无半点爽风吹,坐轿分明是甑炊”(《午热》)。同是描写“早行”,温庭筠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清冷静谧,写景如画;杨万里则道:“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皋渡》)机杼虽一而写景令读者如身临其境,鸡鸣狗吠增添俗世的热闹,青鞋踏霜又何等粗朴有力,诗人真正走出书斋,走进自然、走进生活方能如此形容。又如描写烟光山色,陆游云“山光染黛朝如湿,川气熔银暮不收”(《杂题》),杨万里则道“暮山如淡更如浓,烟拂山前一两重。山背更将霞万匹,生红锦帐裹青峰”(《晚登连天观望越台山》)。一为氤氲弥漫之境,淡雅脱俗;一为红青映照,艳丽夺目,二者正有水墨画卷与活色真香之别。再以吟咏花卉的诗歌为例,一般文人诗客注目的对象往往是名花幽草、国色天香,如牡丹、白莲或是瘦菊、幽兰,“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数苞仙艳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来”(唐李山甫《牡丹》),其高贵脱俗如彼;“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诗人的态度珍重赏爱如此。杨万里却道“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明发西馆晨炊蔼冈四首》其一),诗中多是山花野芳,粗枝大叶。如“东扶西倒”的野荼蘼,“金黄铜绿两争妍”的野菊荒苔(《戏笔》),“素罗笠顶碧罗檐,晚卸蓝裳着茜衫”的牵牛花(《牵牛花》),“花似鹿葱还耐久,叶如芍药不多深”的山丹花(《山丹花》),又或是鸡冠花、映山红等等,而诗人“绕遍岩花恣意看”(《昨日访子上不遇裴回庭砌观木樨而归再以七言乞数枝》),亦是向未见于诗中的姿态。传统诗歌中文人墨客对自我的表现具有共性,大多是情怀高逸、风度闲雅,或非狂即傲,落拓不羁。杨万里也具有豁达无羁束的气质,他“仰看青天不看人,醉里哪知眼青白”(《赠都下写真叶德明》),自谓亦是一狂客谪仙,但在“诚斋体”诗中,文人士大夫的固有形象亦被颠覆,是“汉宫威仪既不入贵人样,灞桥风雪又不见诗人相”。如《梅花下遇小雨》云:“仰头欲折一枝斜,自插白鬓明乌纱。傍人劝我不用许,道我满头都是花。”菊花插满头,正好衬托文人的疏狂;花片落满头而不自知,还忙着簪花的诚斋则象刘姥姥一样惹人忍俊不禁。《晒衣》诗中“亭午晒衣晡折衣,柳箱布袱自携归”,学富五车、居官朝廷的老爷也亲自料理生活琐事,呈现出赤足老奴的形象。可见在自我的表现方面,杨万里也不沿袭传统手法——注重表现士大夫身份特有的高雅脱俗气质,反而笔触朴质地写出真实家庭生活中日常的自我形象。总而言之,在“诚斋体”诗中,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新鲜内涵的传统意象,它一方面扰乱了读者早已形成的固定感觉和印象,但又给人亲近、切肤的感受,大大增强了诗歌表现现实世界的明晰度。
[1]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2]杨万里. 诚斋集[M]. 四部丛刊本.
[3]陈衍. 宋诗精华录[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4]刘克庄. 后村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袁枚. 随园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6]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7]翁方纲. 石洲诗话[M].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