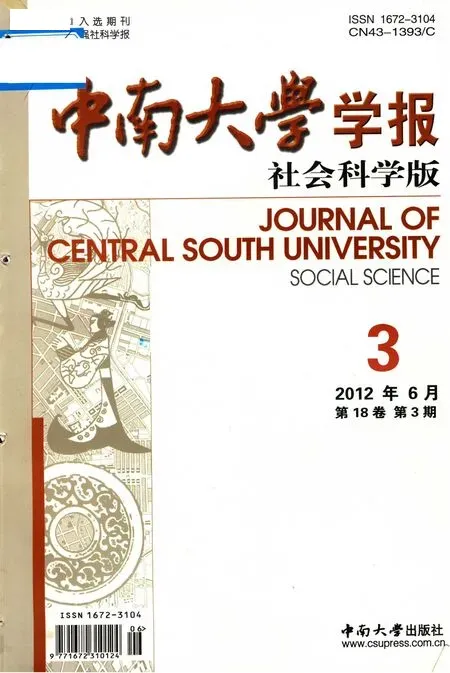揭示分裂,追寻聚合统一
——拉斯普京作品的深层内蕴
2012-01-22杨世海
杨世海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揭示分裂,追寻聚合统一
——拉斯普京作品的深层内蕴
杨世海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拉斯普京是一名对俄罗斯传统具有深厚情感的知识分子,其创作以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为特色,但在这表征之下是对聚合统一的执着追寻,而这一思想深植于俄罗斯东正教精神之中。拉斯普京的创作秉承这一传统,强调人的有限性,重视具体生命体验,揭示分裂,追寻聚合统一,这是其创作的深层内蕴。
拉斯普京;东正教;分裂;聚合统一
拉斯普京出生于西伯利亚安加拉河边上的农村,俄国传统的旧宗法制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在那里保存完整,人们大多承续古老传统,几乎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正是在家乡环境的熏陶下,作家充满了东正教情结,并于1978年在叶利茨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东正教徒。拉斯普京一向认为俄国人民是虔诚信仰宗教的人民,东正教理想是俄国人的道德理想。在创作师承上,拉斯普京推崇高扬东正教价值,追求人类聚合统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因而他接续前人高扬精神价值,探索人生终极意义,并执意追寻聚合统一,这一旨趣在他苏联时代的创作中便有流露,新时期作品则更加明显,并成为其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的根基。俄罗斯聚合统一思想植根于东正教传统之中,拉斯普京的聚合统一思想同样以东正教精神为前提:强调人的有限性,为上帝保留位置;关心个体存在,重视个体生命体验。
(一) 强调人的有限性
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伴随对理性的强调,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痴迷形而上学,人类一步步驱逐上帝,从而产生一种思潮:把自己立为神以完成对上帝的僭越,自命为自己和自然界的主宰,宣称对自我和自然具有绝对支配权,主张对社会和自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20世纪苏联社会变革和推进现代化正是依着这股思潮进行,由于驱逐上帝,过于强调人,把自然、社会对象化,也就造成了巨大生态灾难和道德问题。
拉斯普京对这一社会思潮很反感,极力批判,他的批判并不像艾特玛托夫《断头台》《白轮船》那样刻意渲染生态灾难具体的惨状,而是显得更哲理化,他抽掉近代极端理性主义思潮的根基,恢复上帝位置,强调人的有限性。在《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说:“人,我是看透了啦,他们很小。不管他们站得多近,总是很小。”[4](334)反对“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对人在利用科技征服自然中流露出的傲慢与狂妄表示怀疑和担忧,“人们忘了自己的地位是在上帝下边……。咱们的地位,上帝可没忘,他看到人变骄傲了,你就要倒霉了。……它是很大呀,可你们呢,过去很小,现在还是那么小”。[4](362)她为人类的无知而虔诚地祈祷:“上帝啊,饶恕我们吧,我们软弱、健忘、心灵空虚。”[4](174)在这朴实而形象的语言中拉斯普京借作品人物之口强调了人的有限性,为上帝保留位置。人在上帝面前不可骄傲,正是东正教意识的体现,其生态关注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基于对作家强调人的有限性的认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作品中的超自然书写。在《告别马焦拉》中,作家写到岛主和树王:没有人见过岛主,但它却无处不在,它看见一切,知道一切,又不妨碍一切;树王,无人能胜过它,两次火烧仍然安然无恙,斧头对它无效,油锯也不起作用。小说还写到马焦拉的迷雾,在小说结尾,巴维尔等人驾船去接岛上的老人,但水面升起大雾,怎么也找不到马焦拉岛。在《农家木屋》中,木屋有生命,还能自己灭火。这些都是神话书写方式,在理性和科学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从文学来看也只是一种艺术手法,但深入去看,发现这样的书写正是强调人的有限性,向现代理性主义知识观和世界观挑战,正如布尔特曼所说,神话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的特定理解:“人并非世界和自身的主宰,人的生活世界充满了不解之谜和不可把握之域,人的生命是不可思议的”。[5]因而,仅仅把这些理解为象征手法,象征家园、大地、自然是不够的。正是对人有限性的强调,使上帝在无神环境下(苏联时期)显现,才使拉斯普京的生态关注有了根基,使聚合统一思想有了根基,显示出东正教信仰的价值。
(二) 重视个体生命体验
勃洛克说:“时间的潮水把我们淹没,我们的不幸只是一瞬。”对于这“一瞬”我们该如何呢?按照历史理性主义逻辑,只要前途美好,那不幸的一瞬就不算得什么。而且不幸也是必要的,“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如果着眼于那“一瞬”便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有其合理性,却忽视了具体的个体存在和生命体验,更何况历史理性并不如其所宣示的那样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文学有必要对这样的理性主义进行反思或者保持距离,不应一味去应合所谓的历史潮流,而要关怀那不幸的“一瞬”。
世纪之交的苏联,在声势浩大的现代化和随后重大政治经济变革中,无数个体陷入历史漩涡之中。如果按历史理性来说,为了推进工业化,失去一个世代都没有发展变化的破烂岛屿有何可惜?那些“死脑筋”的老太太们的叹息和眼泪又算得什么(《告别马焦拉》)?面对国家和民族道义,关注和同情一个逃兵和一个包庇逃兵丈夫的妻子有何必要(《活着,可要记住》)?转轨经济,砸碎大锅饭造成失业,有什么痛惜(《新职业》)?城市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恋恋不忘那破败或已消失了的乡村干嘛(《故乡》《往返》)?但拉斯普京关心的就是具体而真实的个体存在: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惧,害怕变迁的旧脑筋的老太太(《告别马焦拉》);那些抱着旧式生活不放,顽固的阿加菲娅们(《农家木屋》);那些在社会竞争中落败,处境窘迫的阿廖沙、巴舒达们(《新职业》《下葬》);那些没能懂得市场规则,在新生活中不能得心应手的塔玛拉、阿纳托利、尼古拉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等等。东正教传统拒绝理性价值的绝对性,坚持把个体价值置于首位,强调精神和个体体验,拉斯普京正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关注这些被时代主流抛弃,在社会演变中遭受不幸的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舍斯托夫一样依托东正教价值反抗理性霸权,彰显被历史主潮遮蔽的人的存在,把个体存在解救出来,深入展示人的具体存在和生命体验,以此对人的生存现状、生存意义进行探讨。关于作家这样的创作旨趣,如果不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关心个体,重视生命体验来理解,在历史理性观照之下,就会认为其文化取向充满悖论,价值迷失,并缺乏深度。②
拉斯普京作品强调人的有限性,重视个体生命体验,拒绝历史理性主义价值之思并不是否认理性、否认价值,走向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更不是走向虚无主义,乃是承继俄罗斯传统精神,强调对人完整存在的关注,反对分裂,寻求聚合统一,此乃其价值诉求。
二、揭示分裂,追寻聚合统一
为什么拉斯普京要抛开历史理性主义,用一种我们认为“落后”“片面”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和人呢?这就需要探索其深层所指,这深层所指即是作家秉承万物聚合统一的传统俄罗斯精神,所以其创作之根本在于对分裂的揭示和对聚合统一的追寻。
(一) 揭示分裂
受东正教影响,俄罗斯精神始终强调人是上帝之子,人在对自我有限性和罪性认同的前提下,克服理性和情欲的诱惑,通过承受苦难,在苦难中爱,不断自我完善,最终回到上帝那里,达成人与神的合一。那么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都应该是聚合统一的,但现实中,这些往往处于分裂之中。而且由于对上帝否定,人们忘却了原本应该的聚合统一,对分裂麻木不仁,或者视作理所当然,认为此乃历史的必然,但拉斯普京坚决反对,不断在作品中揭示现实中的分裂以及由之带来的悲剧。
拉斯普京对分裂的揭示包括很多方面。有人伦关系的分裂。在作家成名作《给玛丽娅借钱》中就显示出这样的意味,小说通过库兹马给妻子借钱这一线索,展示出现代农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尤其写到库兹马夫妻对上了城的兄弟阿历克塞的陌生和距离,亲人间的隔膜凸显分裂的悲凉。《最后的期限》中亲人间的分裂进一步突出,并导致悲剧。安娜老太太病倒即将离世,在家的米哈伊尔把在外的兄弟姐妹召集回家准备办理丧事,5个子女除塔乔拉外都陆续赶回,这个家庭因此得以团聚。因子女的到来,老太太奇迹般的好转,但几个子女在几天的相处中,间隙渐生,最后大吵一场,负气离开,可在他们走后的当晚,老太太就在孤寂中离世。小说悲剧性地展示了现代家庭亲人在分离后,距离横生难以沟通。柳夏回家后,什么都看不惯,谁都看不顺眼,一想到要同大姐过上一整天就愁,“她已不想留在家里,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跟任何人交谈——不管是泄气的话,还是鼓励的话”。[4](374)不仅兄弟姐妹间难以沟通,母亲和子女也难以沟通。当他们要离开,老太太哭着挽留:“我要死了,要死了。你们看着吧。就在今儿个。你们稍许儿等等,等等吧。我再也不需要啥了。柳夏!还有你,伊利亚!等一等。我对你们说呀,我要死了,就要死了。”[4](514−515)然而,俄罗斯人那种固有的直接的心灵的沟通在他们之间没有了,他们无法了解老太太的心愿,也就听不懂老太太话的含义:没有他们她就会马上死掉。“标准的俄罗斯人家庭就是那种充满了和谐和爱的家庭。”[6]但在这部小说里,显示的只是分裂和不幸。到《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分裂则扩散到全社会,“富人和穷人相隔万里,住在两个世界。富人甚至有自己的太阳,与穷人不一样的太阳,是从天堂里抢来的太阳。……这两个世界的人不仅是贫富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还有贫富带来的本能差异。……谁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世界的人才能相互适应,成为一个民族整体;或者永远也不会融合,最后其中一方被迫逃离”。[7](59)
也有自我的内在分裂。拉斯普京所显示的自我内在分裂并不是心理学式的人格分裂,是指自我缺乏连续性。其命题在于生活变动尤其是城乡变迁对自我造成分裂,这表现在一系列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身上。阿历克塞(《给玛丽娅借钱》)从农村走向城市,便断掉了与农村的情感联系,过去与现在截然阻断;柳夏(《最后的期限》)进城久了,对农村的一切已经陌生,她与家人也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所以她“丝毫感觉不到她和他们之间的那种特殊的骨肉之情”,[4](374)致使她觉得谁都厌恶,只想离开,既无法体谅兄弟姐妹,也听不懂母亲的召唤;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塔马拉的哥哥和弟弟也是这类型人物。这种缺乏连续性的人,必然与人疏远分离,表现得亲情淡漠。
还有人与自然的分裂。一方面体现在人对大自然的破坏,在《告别马焦拉》《往返》《故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与故土疏远,家园意识淡薄,《火灾》最为明显。在拉斯普京看来,破坏自然,疏远故土,没有家园意识,也就意味着失去生存根基,人们也难以在新的环境中开创新的美满生活。松树镇(《火灾》)的人们过着不以新迁地为家的生活,混乱无序,无所依存,得过且过,在一场火灾面前不是抢救家园,而是趁火打劫,尽显丑态。因为他们对自然、故土没有感情,随便丢弃原有一切奔向新生活,而当新生活并不如意时,他们自然会索性胡乱生活。之后,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再次激愤地写道,“人们似乎不曾有过去,似乎是乘着巨型交通工具飞驰到了一块没有人烟的土地上,一个没有法规、没有风俗、也没有信仰的地方”。[7](137)故土意味着家园,当人失去家园意识,失去与他人共同的东西,注定会与他人可悲地疏远,阿历克塞、柳夏便是如此,甚至会成为道德败坏者,就如《火灾》中的无赖们。
分裂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情感的丧失,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之一。拉斯普京早就强调:“文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感情教育……感情也许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东西,而这正是科技革命存在的问题之一。”[8](110)人没有情感,这将是灾难性的,道德无从谈起,一切随利益而动,这样的人怎么能把生活安排好?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又怎么能安定和谐?但拉斯普京不是悲观者,其揭示各种形式的分裂,为的是追求聚合统一。
(二) 追求聚合统一
拉斯普京曾说:“在西方人居于首位的是外在的生活建设,在我们当中居于首位的是心灵和与其他民族亲近的感情。”[9]他对西方的判断并不准确,但对俄罗斯精神的描述颇能抓住核心。俄罗斯精神强调聚合统一,他欣赏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就认为,俄罗斯宗教观念中坚持以爱、以与邻人融为一体的集体性或共同性为出发点。[10]拉斯普京的聚合统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城市和农村,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和代际的延续上。
拉斯普京的创作始终在追寻聚合统一,他在《告别马焦拉》中美妙地描述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统一,“这时你真不知你是在哪儿,你是何物了,你仿佛渐渐觉得,你正静悄悄、飘飘然地在大地上空滑翔,微微地颤动着翅膀,飞向为你敞开的幸福的坦途,敏锐地觉察到身下掠过的一切;还有这不知从何而来的深深的隐痛,你所痛心的是,在这一刹那之前你竟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你是何物:你不仅是你身心中所具有的一切,而且是存在于你周围”。[4](134)《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塔玛拉的回忆也常呈现出以上的统一。小伊万形象则综合体现了作家的聚合统一思想:小伙子懂得外祖父,也理解父母亲,对遭遇不幸的姐姐深有关爱,他作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二代,虽然早已远离故土,但热爱自然,对外祖父和母亲的曾经的生活抱有敬意,他欢迎改变不排斥新事物,又愿意追寻俄罗斯传统,认真钻研俄语及传统文化,毕业后服兵役,又从事科技工作,还去修建教堂……总之,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科技与宗教聚合统一之路,这正是作家一直追寻的希望之路。
怎样实现聚合统一呢?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中,我们可寻出如下几条途径:
1. 强调记忆
俄罗斯文学具有重视记忆的传统,拉斯普京同样强调记忆,他说:“真理存在于记忆之中。谁失去了记忆,谁就失去生活。”[11]又借达丽娅之口强调:“记忆呀,它记得一切,保存一切,点滴不漏。”[4](158)拉斯普京的作品就是用记忆使人与他人同在,克服分裂,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让传统与现代聚合统一。
首先,怀念故土。“古老的乡村是我们的老妈妈,它必然要离去,但是应该为它送行,还要懂得:它曾经为什么活过,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8](109)拉斯普京质问:“为什么他们不在临别时对在漫长岁月里,在马焦拉村所度过的生活表示惋惜呢,为什么不用惊异而悲伤的眼光看看四周存在过什么呢?”[4](357)怀念故土、家园,是人对所在环境爱的表现,与周遭环境融合,人才能得以安身立命。但这正是走向现代化,走向城市所缺失的,现代人与人疏离,与环境相间,对所从事的工作缺乏热情,这是现代人的不幸。所以,拉斯普京在乎的不仅是故土,更在乎的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人生存的根基,失去这种关系和否认这种关系价值的人,在新环境中也就难以开创新生活。因为深爱故土,尽管明天就要离开,达丽娅(《告别马焦拉》)仍要细心地刷洗住过的木屋,对祖先及神圣的记忆作最后的祭奠;同样,《火灾》中那些认真生活,积极救火的脊梁(叶戈罗夫们)却正是那些对旧农村怀抱深情的中老年人。这并不是作家一定要抓着故土旧农村旧道德不放,而是显示着只有珍惜旧有的,才会积极面向新生活,立足故土,善待自然,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会好好生活下去,这是在彰显爱的价值,有爱的人才能更勇敢,更认真地生活,更能面对荒诞和人世的不幸,如果失去这种情感,人到哪里都不会生活得好,因为不在乎这里,也将意味着不在乎那里,故土都不在乎,那他(她)会在乎另外的地方吗?海德格尔也强调故土的意义:“故乡最玄奥美妙之处在于对土地的亲近,绝非其它。所以,惟有故乡才可以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12]这种说法在俄罗斯作家那里变成了一种长久的经验,拉斯普京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就成为其追求聚合统一的途径,把道德、信仰、故土联为一体。
其次是对祖先的记忆。拉斯普京非常珍视俄罗斯精神群体性思想和人与世界、宇宙、家族融为一体的思想。他说:“人,不是个体,他身上融合着许多彼此不同的乡亲,他们聚集在同一个躯壳中,同舟共济似的从此岸划向彼岸。”[4](135)拉斯普京通过达丽娅建立起与过去精神传统的联系,并用了一个隐喻:家族就像一根打着很多结的线,一些结松开了,一些人即将死去,但另一端又打起了新结。达丽娅在惜别马焦拉岛之际去了祖坟,站在祖辈的墓前,她想到祖辈对自己的嘱托与自己肩负的责任——把这土地,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道德习俗交给晚辈,让其一代一代传下来;《下葬》中的巴舒达,生活再艰难也要把母亲接来照顾,母亲去世后,她没有能力把母亲安葬在城里的墓地或回乡安葬,只能偷偷地安葬在郊外的树林,因而内疚极了,感到对父辈有罪;《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塔玛拉时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教训,想起过去,所以她能更勇敢,更有力量承担家庭变故带来的不幸;而小伊万作为拉斯普京中的理想人物,更集中体现了用对祖先的记忆来实现聚合统一的途径。
2. 代际对话,以达沟通
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拉斯普京作品中充满着代表不同观念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给玛丽娅借钱》有年轻人和老年夫妇的对话;《告别马焦拉》有达丽娅、巴维尔与安德烈的对话;《女人间的谈话》有维卡与奶奶的对话;《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也有几代人大量的对话。设置这些对话有其特殊意味,他们不是激烈论辩,相互否定,而是相互渗透,对话的双方都没有取得话语权力的意愿,不是要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他者,正如巴维尔所说:“那可不是为了说服儿子,却只想知道儿子怎么个回答法。”[4](126)安德烈也不赞同达丽娅的说法,却想听听前辈的声音,了解她们的想法;库兹马在火车上碰到的年轻人对同卧厢的两位相亲相爱的老人抱有异议,但却因为他们的话语陷入沉思和“不自在,心肠软起来”[4](649);维卡嫌奶奶没文化,不能接受奶奶的许多话,可谈话过后却又不觉说起:“奶奶,你这个人真逗。”[13]对话采取代际并置的样式,不是训诫,为的是拉近代际距离,追求相互融合。
在对话设置与追求代际融合过程中,拉斯普京作品的内在结构体现出来:以三元向度方式展开——过去、现在、将来,具体呈现于老年、中年、青年。《给玛丽娅借钱》老年夫妇、库兹马、年轻人;《告别马焦拉》达丽娅、巴维尔、安德烈;《最后的期限》安娜、安娜的子女、小宁卡;《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老伊万、塔玛拉、小伊万,等等。在拉斯普京笔下,不仅有善恶,还有庸俗与懦弱,形成“善——庸俗、懦弱——恶”、“生——死——不朽”、“男人——女人——圣灵”等一系列三元向度模式,这种模式深得俄罗斯东正教精髓,追寻“三位一体”,这是聚合统一的最高体现。于是,我们以往研究中认为拉斯普京把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农村、新与旧、年轻人与老人、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进行二元对立,贬斥前者眷念后者是不准确的,其所追寻的乃是聚合统一,强调连续性。
3. 皈依东正教
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世俗化,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的发展路径难免因利益冲突发生诸多纠纷,在理性的鼓励下,各以为是,于是分裂无可避免,而宗教执着地寻求合一,制止分裂的扩大,这就是宗教的当代意义。东正教一方面对世俗化和物质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对理性的绝对价值进行反思和批判,支持对聚合统一的追寻。
早在苏联时期的创作中,拉斯普京就在暗显东正教价值。他所塑造的老人们无一不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达丽娅对安德烈说:“孩子,谁身上有灵魂,谁身上就有上帝。不管你多不相信,可上帝就在你身上。不是在天上。他祝福你,保佑你,为你指路。希望你生来是人,永远是人。让你心地善良。谁要是糟蹋了灵魂,谁就不是人了,不是人!”[4](155)在《最后的期限》里,则潜藏了深厚的东正教意识。安娜老太太是受洗的基督徒,她企盼小女儿塔乔拉能来送终,可一直没能见到女儿的身影,但她不是责怪女儿,她想:“一个做母亲的不能这么久看不见自己的女儿——……对女儿是有愧的。弄到这种地步:既然她能忍受这种长别离,她又算得上是什么母亲呢?”[4](452)我们通常认为这是道德谴责,而没有注意其宗教内在。这是东正教罪感意识,罪感乃是对自我欠缺的认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走耶稣基督之路,在此世勇敢担当苦难,以宽容和爱待人。与之相对的便是否认自我罪性,为自我开脱,把责任推给他人,正如安娜的几个子女。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母亲不错,有所疏忽也是情有可原,却拼命指责别人,这样的人无法理解他人,更无法爱人。意味深长的是,安娜并未责怪他们,死前惦念的还是盼望他们和解。小说通过对比,显示出当人把人当成自足体,否认自我罪性,就会处处为自我开脱,却把指责抛向别人,就会制造更多纠纷,人与人也就越发分离,难以沟通。在这部小说里,上帝虽不临场,但并未缺席,它显示的是现代人背弃上帝,把自我当自足体,当中心,否认有限和罪性,从而造成不幸的家庭伦理悲剧,这部小说道德批判深植于基督宗教罪性考量之中,显示出浓厚的东正教意识,从反面显示东正教对聚合统一的价值。
在新时期,拉斯普京更明显地彰显东正教价值,《在医院》《下葬》里的主人公都有向东正教寻求救助的举动。拉斯普京重视东正教价值,一方面推崇其对人有限性的规定,以限制现代理性主义的恶性发展以致走向人类中心主义或虚无主义,高扬善的价值,拯救人脱离于邪恶;另一方面则是对苦弱人的关怀,在神的怀抱中,使孤独的个人能得到慰藉,摆脱冷酷现实给个体心灵造成的创伤,表现其对具体生命存在的关怀。最根本的则是对东正教实现统一聚合寄予厚望,他说:“除了东正教,我尚未发现如今有别的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人民经受住苦难。只有东正教高于党派团体利益,而在今天各种党派团体的利益几乎使任何社会运动四分五裂。最重要的是,宗教从精神上拯救人,赋予人生活的意义,使之成为非‘市场’的,而是历史的俄罗斯的公民。”[14]正是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使拉斯普京在探寻民族之根的时候,表现出了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于善之本源的基督的不倦渴求,他让其理想人物小伊万去修建教堂并不是随意的。
三、结语
基督教反对人对神的僭越,认为把人立为神这将是人类的灾难,事实上近代驱逐神非但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基督教关心个体,神降生为耶稣走上十字架,显示的便是承担每个人的苦弱,在此世揩干每一滴眼泪,把爱注入人心,让人更勇敢,更能承担,活出人生价值,制止人与神、人与人的分裂,重新走向合一,以达救赎。③东正教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作家和宗教哲学家在这一传统基础上不断追索,形成对西方理性主义有力的反思和批判。拉斯普京的创作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创作直面现代化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分裂,不断呼吁重视根基。他对乡土、传统的重视,高扬东正教价值,都是为了消弥现代化所伴随的撕裂,追寻人类聚合统一。正因此,那位东正教神甫才会认为拉斯普京是“真正懂得东正教思想的俄罗斯作家”,也无怪乎在他70大寿时,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也发去贺电,并高度评价他的创作成果。
解读拉斯普京作品,如果不从东正教传统及其影响下的聚合统一思想出发,就无法进入拉斯普京作品的世界,也就理解不了作品中对乡土和传统的赞美,对现代理性的批判真正所指。用历史理性主义解读拉斯普京作品,只能在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方面不断重复絮语,还以为人家陷于价值迷失和价值取向的悖论之中,或者仅视之为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④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有:王培英《论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宗教意识》,载《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宫月丽《从俄罗斯文学透视俄罗斯的宗教哲学理念》,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王烨姝、许适琳的《拉斯普京创作中的“东正教救世”意识》,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王学、权千发《拉斯普京生态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救赎意识》,载《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这些研究重在通过对情节、人物形象、思想观念等与东正教观念进行对照,揭示出拉斯普京作品东正教因素的存在,但未深入分析俄罗斯东正教的深刻内涵,那么拉斯普京作品的深义也就处于某种遮蔽之中。
② 王培英的《论拉斯普京创作中价值取向的“悖论”》(载《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1期)、张建华的《拉斯普京“寻根小说”的文化取向及价值迷失》(载《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4期)持此论。认为借少数特例来描写社会是对历史进程的否定,看不到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在批评浪漫主义时就说过:“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做法紧密联系着的……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艺术》)但在今天看来,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的革命诉求和社会进步价值观使他忽略了浪漫主义对于个体具体存在关怀的价值。
③ 救赎的本义就是“使事物合一”。
④ 许多研究持前一观点,孙玉华、王丹丽、刘宏最近出版的《拉斯普京研究》一书则归纳为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1]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Ре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 лучш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 [M]. Палея, 1996.
[2] 任光宣. 我与拉斯普京[J]. 俄罗斯文艺, 2006, (3): 70−73.
[3]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ина Правословия.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г запо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зкзархата. Париж, N.11,1952. C. 4.
[4] (俄)拉斯普京, 王乃倬, 沈治, 石国雄译. 拉斯普京小说选[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5] 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6] Воробьев В.В. Ли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M].1997.
[7] (俄)拉斯普京, 石南征译. 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 (俄)拉斯普京, 程正民译.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9] (俄)拉斯普京. 立场、文学论争(二)[M]. 莫斯科: 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 1990.
[10] Розанов В. Возле “русскойиде”……Сочинения· М·,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0.
[11] 转引自彭克巽. 苏联小说史[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12] (德)海德格尔, 郜元宝译. 人, 诗意地安居[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3] (俄)拉斯普京, 任光宣译. 幻象——拉斯普京新作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4] 夏宗宪. 拉斯普京访谈录[J]. 俄罗斯文艺, 2001, (3): 59−60.
Abstract:Ruspukin is an intellectual who loves the Russian traditions very much,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moral and nature in his novels, but the inner purpose of the attention is searching for Sobornos and Unity of all, and this thought is deep influenced by the Eastern Orthodoxy and Russian spirit. Ruspukin would have succeeded in carrying out this tradition, so his novels have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features: There exists God the novels and he emphasizes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s;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and his/her life experience; the novels reveal separation and search for Sobornos and unity of all.
Key Words:Ruspukin; Eastern Orthodoxy Church; separation; Sobornos and unity of all
Separation and search for Sobornos and unity of all——The implication of Ruspukin’s novels
YANG Shiha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I106
A
1672-3104(2012)03−0204−07
一、聚合统一思想的东正教基础
2011−12−27;
2012−04−12
杨世海(1980−),男,湖南芷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辑:胡兴华]
目前,国内对拉斯普京的研究已充分展开,相关成果很多,研究多着力于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方面。其实,拉斯普京作品还具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当代俄罗斯作家邦达连科曾说:“拉斯普京是属于俄罗斯宗教作家之列的。”[1]任光宣先生在《我与拉斯普京》中也提到:一位东正教神甫指出,在俄罗斯惟有拉斯普京是真正懂得东正教思想的俄罗斯作家。[2]当然,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方面①,但相关探讨多流于表层,并未深入把握“真正懂得东正教思想”所指,更没有把它与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联系起来,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对拉斯普京作品的理解。综观拉斯普京的全部创作,笔者发现在其道德探索和生态关注的表层下,隐藏其中的是对于聚合统一的执着追寻,而这一追寻又深植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这正是拉斯普京作品的深层意蕴。
俄罗斯民族文化蕴含深厚的东正教传统,与西方基督教的历史道路不同,俄罗斯东正教没有经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外部和内部的重大震荡。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通过知识和理性走向最高境界,形而上学色彩浓重。东正教倾向于拒绝这种形而上学道路,更重生命体验和直觉之路,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3]因而开掘出另外一条路,形成独特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以其人文性、完整性、理想性而独具特色。从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开始,他们借鉴早期教父思想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力图从人的完整存在出发,克服抽象思想,转向具体性,要求认识不仅要用理性,而且要用情感、意志、信仰,追寻“聚合性统一体”。聚合统一思想,是俄国哲学家以东正教观念为基础提出的对自由与统一问题的思考方式,以信仰为前提,强调完整性,重生命体验,把内心的充实性,多样性有机统一,统一、爱、自由是其基本特征。循着聚合统一思路,费奥多罗夫发展出“共同事业”哲学;索洛维约夫通过对西方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从普遍综合的观点论证完整知识,提出“万物统一”哲学;布尔加科夫则通过经济过程来证明人类的统一性;弗兰克通过对知识与对象之结构本身的深入分析来探究人的认识的统一基础,提出“活知识”,强调存在与知识的统一,肯定人精神的实在性;别尔嘉耶夫高扬精神自由,把生命嵌入哲思之中;舍斯托夫则把哲学作为一种生命探索,高扬东正教价值,关心具体的人,以苦难通达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吻苦难,通过“宗教大法官”彰显自由的爱和爱的自由以揭示“聚合性”的秘密,渴望全人类的团结和普世的综合;托尔斯泰执意坚持爱,主张不以暴力抗恶,认信暴力革命只会带来分裂。这一切哲学、文学运思都深植于俄罗斯传统之中,体现出典型的东正教色彩,强调聚合统一是其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