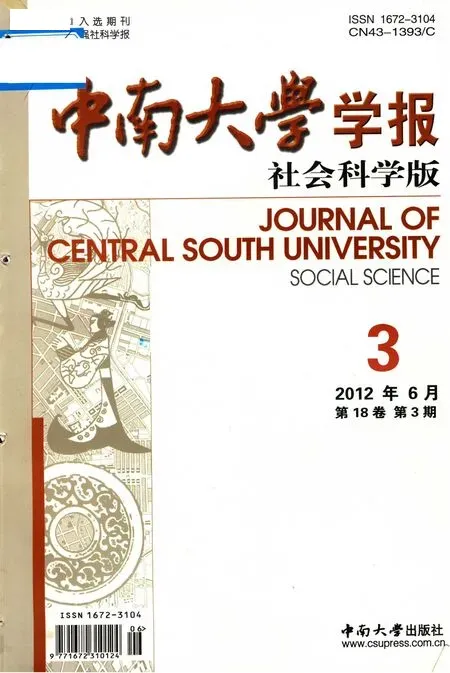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对我国基层司法模式改革的启示
2012-01-22李洋
李洋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中心,上海,200063)
一、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其特色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治安法官制度滥觞于治安维持官(Keeper of Peace)这一称谓。自12世纪末始,王朝统治者为了抑制社会动荡、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其统治的安定,在原有的联保治安制度的基础之上,任命地方骑士协助郡长(sheriff)维持治安,借以弥补原有机制的不足,这便是治安维持官发起的源头。而每个百户区内的这4名骑士,就被称为治安维持官。它最初只是临时的,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而且职能也主要在行政上和军事上[1](286)。而随着政治局势和社会治安的相对稳定,治安维持官在被赋予审判重罪犯的司法权力的同时,称谓也就随之变更为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这一称谓首次出现在1361年[2](168)。这一年颁行的《爱德华三世三十四年法》第一章赋予了治安维持官审判重罪犯的权力,于是他们拥有了“治安法官”这一更受尊敬的称谓[3](386)。治安维持官转变为治安法官,带来的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治安法官与它的前者相比享有更为广泛的司法职能。在都铎王朝时代,治安法官的发展进入巅峰时刻,亨利七世上台伊始就很重视利用治安法官的支持来维护他的统治,不断赋予他们更广泛的职能。此外,中央还颁布了大量刑事立法以提高治安法官的地位,到15世纪时,治安法官组织成为地方上最有效率、最有权力的司法行政机关[4](274)。在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中,随着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颁行,治安法官的行政职能逐渐交由新设立的各级地方委员会行使。与此同时,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也归入经改造后的郡法院①行使,使得治安法官最终蜕变成为纯粹的司法官员。同时,警察制度的改革剥夺了治安法官的治安管辖权,使治安法官的职责更集中于简单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组成的治安法院也相应地成为刑事案件的最基层管辖法院。综上,经过司法改革,治安法官的行政权随着一部分归入中央机关,一部分则由改革后新设的地方各级委员会行使而归于消灭。
面对19世纪改革中治安法官的行政职权的萎缩,梅特兰曾说:“他们的前途一片黯淡。如果治安法官被剥夺了政府的职能,他们还将继续成为法官吗?”[5](669)现在我们看来,治安法官行政功能的消退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法官的能力,反而使得他们更成为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他们俨然成为英国司法活动的身体力行者,如今进行民事诉讼的英国公民通常接触到的不是坐落于伦敦的高等法院,而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治安法院或者郡法院[6](305−306),它们主要处理简单刑事案件(可速决犯)的审理,同时治安法官在案件的预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治安法官将案件移交上级法院即皇室刑事法院②后,它还担任着皇室法院法官的次要责任。对于移交的案件以及来自治安法院上诉的案件,治安法官就成为皇室法院的一部分,一名职业法官与不少于 2名不超过 4名的业余法官一起开庭[7](305)。在当今英国,治安法官不论从人数上(接近30 000名③),还是在处理案件的数量上(约占刑事案件的97%④),无疑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源于基层人民,担当着英国最低审级的案件裁判者,掌握着职业法官所不具备的地方性知识,在处理简单案件中能够灵活运用有普适性的观念、地方习惯、道德观念以及社会经验来灵活处理纠纷,它们主要以解决纠纷为价值目标。
对于治安法官的价值,学者们都有赞誉。17世纪初期,大法官柯克说:“如果恰当运行,治安法官制度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8](9)而 Thomas Skyrme说:“没有哪个国家能设计出比英国治安法官制度更明智、更温和的制度,使用这种更人道的方式来统治人民。”[5](238)基于治安法官承担了 97%以上的刑事案件的简易审理或者预审,以至于有学者称:“如果仅由职业法官来支撑英国刑事审判制度,这种制度准会即刻陷入瘫痪状态。”[9]治安法官制度以其独特的性质和组成结构成为英国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自治之间的调和剂,一定程度上既起到对王权进行监控,又能保证地方上很大程度的独立,进而形成英国颇具特色的地方自治统治。同时,它也对维护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实现“人们看得见的正义”提供了参照。治安法官处理案件的快速便捷,也为现代社会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模式的构建“出谋划策”。
二、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与我国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
鉴于人口与疆域面积的巨大悬殊,英国行政区划的设置自古与我国相异,数百个郡的设置使得各个郡之管辖范围比较狭窄。而治安法官的职权范围主要在郡内,他们在任职时也被要求必须是居住于郡内。而且,英国法院体系的设置除最低一级的基层法院(在刑事上是治安法院,民事上是郡法院)设置在郡内之外,上一审级的法院(刑事上是皇家刑事法院,民事上是高等法院)均为全国性法院,管辖包括全国性的刑民事案件。因此,在进行由于地理条件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此基础上的人为差异比较之时,笔者将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界定为与我国县一级及之下这样一种层次。在此种意义上,笔者所言的基层司法模式是指县级特别是县级以下、最贴近于广大群众社会生活的这一层级司法状况。在我国传统社会,行政官僚制度只是到县令一级。国家的政权统治在最基层乡土社会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法律在乡土社会中难以有用武之地,由此也产生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野。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一方面是依靠州县自理下委任的里甲、乡保来调处,而在更普遍程度上是由民间的调解完成。
我国现行的基层司法主要是在县级人民法院即乡镇人民法庭以及其他具有纠纷解决功能的机构中完成。就农村基层生活中易于发生的许多纠纷类型来讲,乡镇层级的行政机构中如司法所、公安派出所等经常有可能介入其中……从最容易与法律服务发生直接关系的角度来讲,乡镇层级的纠纷解决主体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作为法院派出机构的人民法庭或司法助理员(或司法所)。[10]司法所的出现及其运行,正是国家权力与农村基层社会的交汇点。一方面,它是现代法律意识形态在基层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又兼有传统政治模式的色彩。司法助理员兼有基层地方行政官员和初审司法人员的双重身份,他们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并能够基于其经验而熟练地运用这些资源参与和主持解决地方各种纠纷。
基层司法所属于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实际上附属于乡镇政府,其工作人员除了完成其职权范围内的法律服务、普法、为乡镇政府以及乡镇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管理指导法律服务所和公证所等工作外,还实际参与乡镇政府的各项日常工作。[11](393)由此可见,它实际的功能仍是传统的以行政职能为主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职能也仅仅限于为当事人(主要是乡镇政府及乡镇企业)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以及对一些简单纠纷进行调处。在纠纷化解后制作司法协助书,然后为协议书办公证。而现在,司法助理员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已经转向为乡民提供法律服务,称为“法律工作者”。[12](304)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它的基本职能也仅仅是协助司法助理员调解民间疑难纠纷,为普通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而在实践上,在乡镇这一级,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司法助理员同时是法律服务所的所长。在处理纠纷时,法律服务所同样具有官方政府色彩。
据喻中教授研究的“乡村司法”[13](17−19),他认为驻村干部同样是我国目前基层相当盛行的纠纷解决机制。驻村干部,具体而言是乡政府的干部,驻于村内,以乡干部的名义解决村民纠纷,既反映乡政府的愿望,又满足村民们纠纷的解决要求。驻村干部处理纠纷的规则并非国家颁布的正式法律法规,而是乡村社会中沿袭已久的“情理”。这种司法模式与民间调解不同,民间调解的当事人、调解人一般都是在一定地域内生活的居民,他们同处于共同的传统习惯之中,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调处时没有国家法律规定的限制,完全是社区自治的景象;而“乡村司法”则是在这一区域之外的第三人参与之下,作为政府机关中的一员参与到村民自治的模式之中。对于村民而言,驻村干部是外人,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却又与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不同。因为即使是最基层的派出法庭,它们依然是国家司法的组成部分,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受理和审理案件。当事人诉讼时依然需要缴纳诉讼费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即使是简易程序亦或是法庭调解——以及法律规定处理纠纷。而乡村司法模式的基本形式是调解,依据的处理规则是所在村的地方习惯以及“情理”,价值目标是解决纷争,它不拘泥于形式,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与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相比较,我国目前的基层司法模式呈现出更为庞杂的情形。首先,作为最基层的司法体制,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与我国目前的基层司法制度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前者在其发展中已经褪去行政色彩。治安法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表现为:有权处理那些轻微的、通过简易程序加以审判的犯罪。主要包括交通安全犯罪或轻微的刑事犯罪,如 1988年《道路交通法》规定的未能适当注意的驾驶罪,1968年《盗窃法》规定的盗窃自行车罪等都由治安法官管辖。在民事方面的职能表现在:他们向婚姻当事人发布赡养令,并鉴于家庭的儿童颁发监护令;他们在附带程序中认定儿童的父亲血缘;此外,他们被列入到青少年法庭中。虽然公民个人不能向治安法官请求民事债权,但郡法院做出的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却由治安法官行使。而反观我国基层司法机构,则仍然保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其定位仍未摆脱半官方的限定。据笔者所知,相当程度的基层司法局还负有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等职能,而这种颇具有行政色彩的职能设置实际上既与现代社会中权力细化与分制相违背,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在各方面的实际功能。作为司法机关的主要功能应该放在纠纷解决上,其他事务完全可以交付于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等基层行政组织完成。
其次,与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相比较,我国目前基层司法制度呈现出定位不明确,造成各机构重叠、未能形成完整体系的现象,从而导致效率不高。英国治安法官作为独立的基层司法组织,其与基层行政机关并不重叠,而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属于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基层司法所却是隶属于行政机构——司法局的一种组织,驻村干部本身便是行政官员的一份子。这样一种层级交叉与行政涉足司法并管的体制设计对于纠纷的解决并非有益而只能是起到消极的作用,更不利于其司法职能的实现。
三、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对我国基层司法模式进路选择的启示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在起步之初与我国传统及当前基层司法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在近代的发展中完成了职能与定位的现代化转型,这对于我国的基层司法制度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当然,借鉴西方经验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制度的设立往往会有更深厚的文化地域、配套的社会结构相支撑,而文化的土壤亦是最难塑造的。譬如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效法法国民法典编纂本国民法典之时,不加选择地将法国的“身份证书制度”⑤引入,与日本的“户籍制度”⑥对抗而不可调和,导致民法典的编纂流产。对西方经验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是否具有普世的价值观念,是否能够适用于现代的社会。借鉴,最重要的是获取启发,在本土现有的资源之上设计一套适用于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既要考虑兼容,又要考虑成本。在这种意义之上,理想的借鉴或许并不是移植或者嫁接,而是在吸收经验之后的对现存制度的改观。基于我国目前基层司法图景的考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借鉴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经验,实现我国基层司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1. 法官分流是实现基层司法模式转变的要求
治安法官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贯彻司法权在基层的行使,合理解决地方简单纠纷,达到高效便民的目的。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经验⑦告诉我们,治安法官制度的借鉴并不是全盘吸收,即也在本国建立同样的无薪的、业余的非职业法官。相反,利用治安法官制度的基本理念设计出适用于本国具体国情的基层司法制度实为上策。治安法官可以是有薪的,甚至是职业的,如意大利规定治安法官的任命是从法科毕业生中选任,按照工作量计算报酬[14](362−363),他们的性质可以界定为“准职业法官”(虽没有职业法官的选任资格严格,但同样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与经验),这也未为不可。
基层法院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公民方便、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诉讼,因此,法院在设置上不能完全按照高等法院的模式进行,而应当更多考虑到在距离和习惯上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及根据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而制定合理的诉讼费用标准。我国目前借鉴西方经验最重要之处在于对现有模式的改造。法院的基本职能是落实或形成规则,还是解决纠纷?[12](176)规则之治无疑是法治的高远境界,但是目前解决纠纷仍是基层法院最主要的任务。如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设立自始至终贯穿着实现最有效管理的理念,它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国现存的基层法院的问题在于无法处理好法官精英化、职业化与数量、成分繁杂之间的关系,在法官的整体职业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满足职业化、精英化需求的情况下,将法院法官进行分流以实现法官的分层次无疑是解决办法之一。对于基层法院中为数众多的非法律专业法官,将他们划归为一个统一的司法部门,或者对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以及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进行改造,将其改造成为简易法庭。将其司法职能限定为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诉讼标的较小、案件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以纠纷解决为价值追求,在诉讼费用上实行低收费标准。而专业法官仍作为普通法院的法官,将其职能界定为处理案件争议大的、诉讼标的额较高的民事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并且享有对于简易法庭提起上诉的案件的审理权。这既能实现高效便民解决纠纷这一法院功能,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职业法官的司法压力,为实现法律职业化、精英化进而实现法治的现代化提供了条件。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普通民众与法律职业者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不可弥合的间隙。对基层法院法官的分流使得在处理解决民众纠纷时往往效果明显。非专业法官虽法律知识稍欠,但他们往往是当地居民(据调查,本地法官的数量与法院的审级呈反比,即审级层次越低,法院中本地人的比例就越高[15](183)。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问题;但同样地,他们也占有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熟谙当地风土人情,在处理纠纷时即使法律知识缺位往往也能游刃有余,妥善解决纷争。
2. 职能分化是实现基层司法模式转变的出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治安法官逐渐被赋予了现代性的职能,在发展初期,英国治安官明显带有行政甚至军事色彩,它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基本职责,充当地方行政长官的角色。在法治发展程度不高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往往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为一,同时掌握在行政长官的手中。而在将法治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分工与职能的分化已经成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仍旧混同的局面显然有悖于这一要求。英国的治安法官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褪去其行政色彩,转而成为地方基层的专职司法人员的经验尤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人们在谈及对治安法官制度的借鉴时,往往会想到建立中国的治安法官制度,或者只看到了这一非职业法官制度的公众参与司法的模式,而笔者认为着眼于行政职能转变为司法职能的过程更为重要。如果在我国建立一套治安法官制度,因为文化与习俗不同,治安法官制度所需要的士绅传统以及英国传统的骑士荣誉观念在我国并不存在,虽说我国传统社会中也具有士绅这一群体,但他们在基层地方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品格令人汗颜。[16]因此,笔者对于那种试图效仿英国治安法官制度而建立我国“太平绅士”制度[17]的做法是并不认同。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在现代转型的经验揭示:实现法治的现代化,不能仍旧保有传统的行政与司法混同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这也是自启蒙思想家以来所一直极力呼吁和倡导的。为此,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司法体制,即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行政与司法职权分工。
在现代化社会中,作为居中裁判者的司法机关保持其中立和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考察我国现有的基层司法模式,无论是驻村干部,抑或是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的司法助理员,他们仍旧是兼具司法与行政双重职能的政府工作人员。实现基层司法模式的改造,就应当将基层司法机构作重新定位,尽快明确其司法职能,使之转变成为基层司法的中坚力量。为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司法体制,应着眼于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应以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为核心,涵括基层司法所等基层组织,将其改造成为基层法院体系中的一部分,将其职能界定为服务于司法性质的纠纷解决,处理基层简单民事纠纷。这无疑是今后基层司法模式努力的方向。
3. 明确基层司法职责范围是实现基层司法模式转变的内容
基层司法制度的本质就在于为满足基层人民的需要,解决基层人民的诉讼纠纷。而明确其职责范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发挥职责,避免造成与上级司法机构行使司法权时出现重叠或者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明确基层司法职责范围更有利于当事人对纠纷的申诉,更便捷地行使基层司法职能。英国治安法官在最初的形成时期,其职能范围不甚明了,多为临时性职能,而在现代转型后其司法职能范围逐渐稳固、确定,主要包括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审判权、严重刑事犯罪的预审权以及涉及家庭事务、青少年等民事案件的审判等。治安法官的审理程序简单、高效,不需要陪审团的参与,一般的简单案件大约只需半小时便可得到圆满解决。
而反观我国基层司法机构的设置则略显繁琐,一方面,其宗旨在于更好地服务于群众,解决群众诉讼困难。另一方面,却在机构的设置与分工上不甚明了,简单纠纷往往更难得到及时高效的解决,或者被置于高级别的法院系统中,对原本稀缺的司法资源造成浪费。驻村干部、基层司法所的调解虽然便捷,但对于其无法调解或者调解无效的纠纷没有更好的救济措施。而且即使在调解完成之后,往往会因为这一调解并没有强制力,使得整个过程最终失败,不得不重新启动县基层法院审判程序。因此,借鉴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经验,在保有驻村干部、基层司法所等机构的同时,赋予他们一定的司法职能,将行政色彩转化为司法色彩,规定一定的职责权限和职责范围,使之更为全面和高效地履行职权,从而与乡镇人民法庭紧密结合,与县基层法院形成梯级的两级司法体系。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也是在目前法官职业化尚无法全面推行的现实状况之下的解决举措。
但应当注意的是,英国法院系统依照案件的性质分为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英国治安法院是英国刑事案件的基层法院,治安法官的职能范围主要集中于刑事案件的管辖权方面。而传统中国重刑而轻民,将“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看作细微之事,而对于刑事案件则甚为谨慎,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严格掌握在国家手中,不能调解。中英两国关于刑事案件的界定也存在差异,在英国,轻微的刑事案件包括酒后驾驶、轻微斗殴等,由治安法院管辖,这在中国则属于治安处罚法的调整范围,由公安机关管辖。也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我们不能完全依照英国经验来划定我国基层司法的职权范围。
因此,在县级法院之下,以人民法庭为核心,将基层司法所、驻村干部等各种机构整合,赋予其明确的司法职能,授予其清晰地处理简易民事纠纷的职责范围。同时,明确其定位,发挥其贴近群众、占有地方性知识的优势,配合其上级职业法官的司法活动,实现基层司法的现代转型,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四、结语
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形成与完善的地方司法模式一直是行政与司法混同模式,而这也是为当时东西方所通用。虽在中央有三法司等专职司法机构的存在,但在地方却二者合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手,在县以下的基层地方,普遍推行的是以乡土自决为主,辅以政府的监督,这种模式以清末的乡保制度最为典型。撇开学者们认识上的差异,这种调解性质的基层司法模式沿用至今,现代特色的基层司法所、驻村行政干部等都是行政元素涉入司法模式的体现。
而横向地将西方列入视域之中,以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为例的基层治理模式,同样在封建社会时期是地方的代表,总揽包括治安管理等行政职权与刑事审判等司法职能,身兼中央与地方双重色彩。而梳理它的发展历程后得知,在19世纪司法改革中成功地实现司法行政职能的现代转型,进而成为基层司法的主力军,在基层诉讼纠纷解决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职业法官可以专注于规则之治的营造。
借鉴并不意味着移植,在笔者看来,借鉴的主要含义应当界定为理论制度上的经验总结,重在吸收经验为己所用。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在现代转型的经验应当为我国借鉴。我国目前处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之中,更应关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英国的国情虽与我国迥异,但在基层治理模式上都存在着行政与司法混同的现象与制度设置,不同的是,英国现已走上二者相分离的道路,而我国仍在探索。因此更应当借鉴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成功经验,实现我国基层司法模式的现代转型。当然,在两国国情相异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当看到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对于我国的不适用之处,更应当对其作出取舍或者灵活变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国所用,这才是借鉴西方经验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 郡法院是根据1846年的制定法设立的, 英格兰有400多个郡法院, 由一名巡回法官主持审判. 参见[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 潘汉典, 米健和高鸿钧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307−308.
② 皇家刑事法院, 也可简称为刑事法院, 是根据 1971年法院法建立的, 取代原来的巡回法庭和季审法庭, 是高级刑事法庭.
③ 2010年治安法官(Magistrate)人数为29270人. 英国司法部政府网站中关于 2010年治安法官的统计数据: http://www.judiciary.gov.uk/publications-and-reports/statistics/magistrates-statistics/?wb c_purpose=Basic&WBCMODE=Presentation Unpublished,2011−11−17.
④ 英国司法部政府网站中关于社区司法体系的介绍: http://www.judiciary.gov.uk/about-the-judiciary/judges-magistrates-and-tribuna l-judges/judiciary-within-the-community/?wbc_purpose=Basic&W BCMODE=Presentation Unpublished, 2011−11−17.
⑤ 身份证书制度承认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地位, 是个人权利的公证制度.
⑥ 户籍制度是国家把整个家族作为对象编成户籍登记在簿的公式制度, 它把家作为社会生活的单位, 是家长制的一种体现.
⑦ 俄罗斯的治安法官也是有薪酬的, 由联邦最高院的司法财政局发放. 参见: 张寿民. 俄罗斯法律发达史.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334−335.
[1]Sir William Holds 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M]. Methuen& Co Ltd and Sweet & Maxwell Ltd, I, 1956.
[2]西奥多·F·T·普拉克内特. 简明普通法史(英文影印本)[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3.
[3]威廉·布莱克斯通. 英国法释义(第1卷)[M]. 游云庭, 缪苗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马克垚.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Sir Thomas Skyrme. History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 [M]. Barry Rose and 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Chichester England, 1994.
[6]K·茨威格特, H·克茨. 比较法总论[M]. 潘汉典, 米健和高鸿钧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7]约翰·斯普莱克. 英国刑事诉讼程序[M]. 徐美君, 杨立涛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8]Esther Moir. 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9.
[9]马塞尔·柏宁斯, 克莱尔·戴尔. 英国的治安法官[J]. 李浩译.法学译丛, 1990(6): 57.
[10]王亚新. 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一)[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3): 7.
[11]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2]苏力. 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13]喻中. 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4]何勤华, 李秀清. 意大利法律发达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5]贺卫方. 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A](夏勇. 走向权利的时代[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6]陈亚平.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第三领域——基于巴县档案史料的考察[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72.
[17]姚秀兰. 香港太平绅士: “源”与“流”[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