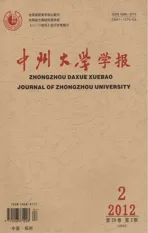评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
2012-01-21王影
王 影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00)
库切的每一部新作都会不同于他的先前之作。他往往能够涉入读者极少涉猎的领域,以有限的篇幅带我们走进无限的感受之中。2009年的《夏日》被称为继《男孩》(1997)、《青春》(2002)之后库切的又一部自传体小说,只不过这一次,他以一个研究已故作家库切的传记作者身份展开作品,给我们罗列出若干的日记记录片段以及对几个在库切生前与之有所接触的人的访谈记录,不同于作品中告知我们的关于约翰性情的拘谨,库切在小说创作中一直都是极为大胆的,他“似乎敢于做任何事”。自《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到《凶年纪事》,再到《夏日》,他在小说的形式方面频频出新,“敢于把小说写的像论文集,敢于把小说写得支离破碎,敢于把小说写得像回忆录”。但是,如果说写作旨在唤醒并展现我们内心深处相互碰撞的多种声音——关于自我、关于外部世界的声音,那么无论小说的外部形式怎样变化,它终究都会回到一个问题上,即通过这些文字,它要讲述给我们什么?
库切正是以此种方式一次次带我们深入到人内心的隐秘之处,引导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身体和意识”,甚至带我们“深入到非洲的内部”。在《夏日》里,他使用一种较为松散的拼贴方式来完成这种探索,而这种方式更适宜于他的自我表述,或者说对自我内心多角度的深度反思。同时,使用他人的话语而不是个人的直接表述又达到另一种保持距离的效果,这种距离感使他在谈及自己时颇感自然又很动人。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一个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添加进去的虚构成分,而将关注点集中于库切即是约翰的身份,集中于他多少会有将自己放进去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这些记录片段和访谈对话具有一种客观真实感。于是,通过这部作品,结合他鲜有保留的剖析,我们便有了对于库切更为深入的认识——他写作的目的和意义,他时时拘谨的性情,他反激进又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保守政治态度,他个人身份的的两难境地……
一、关于写作——何以永恒?
在茱莉亚的眼中,《幽暗之地》是以“种种征服的形式对残酷的揭露”,并且“这种写作的方式是一种自我执行的疗法”,“一个自我改造的计划,他下决心要阻止自己生活中每一个活动场所的残酷和暴力冲动,”“写作成了某种无休无止的净化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库切的声音。有关“净化”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出现三种不同观点:一种基于医疗的模式;另一种基于道德完善的思想;第三种是对戏剧中能引起怜悯和恐惧情感的事件的澄清,使观众从这种澄清中学到东西。归结起来,这些净化、澄清,都是对于观众或者戏剧本身的情感事件而言。但到了库切这里,“净化”成为了作家本人的净化过程和升华过程,为支撑起个人生活甚至改造个人生活的手段和方法,他需要写作,需要通过写作来拯救自己。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非荒唐境遇的见证者,他动用自己敏感的神经,在让读者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安慰他自己在残酷现实中早已深陷无奈之境的道德良心。
由此可见,那些批评库切只是粗浅地诊断出西方社会的弊病却并未给出任何治疗处方的言论,其实是不对的。正如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中指出:“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这个孤独之人已不再会用模范的方式说出他的休戚,他没有忠告,也从不提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库切用《夏日》实验着这种极端,并在这种极端中流露他孤独本性之中的谨慎、惶惑以及担忧——对自己身上的局限性、对自己的未来以及对自己爱恨交加的那片土地。但他终究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凭借个人经验和强大的想象力为社会构建蓝图的幻想家。当茱莉亚以不同的声音提出:一本书应该是一把斧头,劈开人们内心的冰海,约翰将其视为面对时间的一种拒绝姿态,面向永恒的努力,超越人的肉身存在的永恒。可见,作家的犀利有很多种,而库切更愿意像大多数注重感知同时又注重思考的人一样,通过靠近自我和内心挖掘来展现人性,展现一种社会情境,乃至一种时代状况。至于作品能否对读者和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不是他所能掌控的问题。
二、关于性情——何以拘谨?
约翰闯进了茱莉亚的生活,或者说被带入茱莉亚的生活,而且以一种很不恰当的婚外情的方式。当然在茱莉亚看来不是完全因为爱情,甚至根本一点儿都没有爱情的成分,文中使用“友情”一词来形容两人的关系。但如果说他们之间真如茱莉亚所说没有丝毫的契合,那么也应是约翰紧闭自己内心的结果。“他就像是一个玻璃球”,“他的那颗心通常都是裹在铠甲里面的”。在约翰身上,我们自始至终都能感受到一种拘谨——凝结到性情里的拘谨,一种羞怯于表达极度敏感之心的小心翼翼。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与茱莉亚的接触中,还有在玛格特的心目中,约翰也一直是一副未展开的模样。他紧紧地保留着自己,保留着他对于家人、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爱与恨。但对于读者,他的孤独清晰可见。从《青春》中“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到《夏日》中“很少也很难敞开的心怀”,约翰使茱莉亚、玛格特困惑……而且还将会继续困惑以后接触到他的人。他们彼此认识、理解都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们却不能牢固地契合。
这些与约翰有着交集的女人们,都异常一致而且坚定地认为他的生活中需要一个人,一个可以照顾他的人。而他真的需要吗?在评论戈迪默时,库切说:她作品中的南非白人“都生活在萨特所指的不诚实中,骗自己说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库切笔下的约翰也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沉湎在对舒伯特的幻想之中,茫然于与周遭的人和事的平常而基本的交流,他以想象的方式理解女人,并将自己构想出来的浪漫意象安放到他遇到的人身上,甚至为此暗自欣喜,直到被想象的对象逼迫其清醒起来。茱莉亚是讨厌其紧闭的不愿敞开的内心,还是看到了他的这种不真实?
阿德瑞娜也一样不理解约翰关于爱情的幻象。但是,“如果我们认同某个人们以理想之名行事的世界,在伦理上要比这个人们以利益之名行事的世界更优越。”约翰头脑里诗意的世界或许并不适合认同现实里的人们,但对于他自己,那是另一种真实。在这种幻化的真实里,他的性情得到舒展,他的生命得到自由。
三、关于自我——只身向何处?
“对于这个具有百年的剥削暴力以及令人心寒不安的贫富悬殊之历史的国家,他极为厌倦,厌倦它每天对他们的道德良心提出的要求。”《夏日》开篇1972年至1975年的笔记中,首先就记录了他回到南非看到报纸报道的惨绝人寰的枪杀,对此他愤怒,又觉得“一回来就得沾惹上这东西,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但激愤和憎恨之后也只能陷入木然和无奈了。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陷在这种特殊环境造就的道德里,他被一种冲突折磨着,一方面作为不公正的目击者,谁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他在不能熟视无睹之后深感无力,他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在茱莉亚、阿德瑞纳不理解甚至厌恶约翰种种不合时宜的性情之时,与之有着很多相通之处的玛格特表姐对于表弟约翰的这种不真实则更多表示一种挥之不去的同情和怜惜。因为他们之间有过相互坦诚的童年,还以为可以天经地义地跟对方结婚。她和约翰不仅有着相通的地方——血脉、亲情、友谊,还有着共同需要面对的人和问题——库切家族、默韦维尔、卡鲁地带乃至整个国家。“是谁想出这主意来,在这儿修建公路,铺设铁路,建造城镇,引来人群居住,然后又把他们困于此地,往他们心里铆上钉子?”“我们在世界的这一角不毛之地干什么?如果说生活在这儿的人生毫无意义,如果人类在这儿的整个生存一开始就是一场恶作剧,我们为什么还要以枯燥的劳役在这儿消耗生命?”这不仅仅是玛戈特和约翰的问题,更是库切的问题,接下来还有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又该怎么办?
马丁提到自己和约翰这类人的存在“根植于一种罪恶,即殖民征服,通过种族隔离而被永久固定下来”,而在自己的感觉之中,他们只是“寄居者”,是“临时住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没有家的”,“没有故土”,而这种在自己的情感中所培育的“临时观念”,使他们“不愿意对这个国家投入太深”,因为他们的投入是“白费功夫”的。传记作者由此追问库切的这种临时观念是否已超越了自己的出生地与自己的关系?显然库切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受其影响的。当他疑惑于心里的这份不安定,当他不认可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所属关系,所有的情感处理中也都夹杂上了这些不愿完全投入的成分。于是他即便愤怒于眼见的暴力和不公正也终究在无奈中平静下来;即便对人怀有某种真情却也只愿意在某一刻流露之后便仓促收回,汹涌的情感只能在写作中得以宣泄,并成为自我延续的方式。
沉迷于幻象的约翰,在政治立场上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觉得“政治激发了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也“把社会最坏的一面表现出来”,于是他期待着“有一天政治和国家都走向消亡”,在人与人之间他倾向于一种老派的原始的安宁和睦关系。
作品最后,一切都以父亲的形象幻化出来。回来之后,令他吃惊的是发现父亲大有变化,他想去握住父亲颤抖的无助的手,想要父亲借往昔的享乐而变得心情愉悦、重拾丢失的青春,可他们不能一直住在一起,体验所谓的相濡以沫,他不属于这里,不属于父亲所在的这个世界,犹如父亲和南非并不能理解他一样。于是,当面对身患重病的父亲,他需要放弃自己的一切事务去担当一名护士时,他突然变得焦虑万分——“我做不来这个”,他说,“我不能面对日夜看护你的前景,我要扔下你了,再见了。”从南非到英国、美国,再到澳大利亚,库切真如他之前所说,最好与自己相爱的一刀两断,切开自己伤口愈合的希望。而回想起拘谨的约翰所沉迷的舒伯特蓬勃向上的幻象,这种决绝的背后又藏着多少的悲哀与绝望。如今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被病痛扼住了咽喉,他一个合法却不合理的单薄之人能做些什么?他在那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看来又如何呢?
他同作家迪戈默一样苦苦挣扎在泥潭之中——这就是“为一个民族写作、为他们而写和代他们而写、被他们读,意味着什么?”约翰带着库切,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主宰着,犹如放弃想象的堂吉诃德不再寻求行侠仗义而回到单调的生活中,最终“走向黑暗,沉入他内心的苦井”。
[1]库切.内心活动[M].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2]库切.异乡人的国度[M].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3]库切.夏日[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4]先刚.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J].学术月刊,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