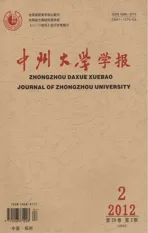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构成及文化意涵
2012-01-21张月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构成及文化意涵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最早的木版年画,其造型独特,形式多样,主题鲜明,意义厚重。本文首先追溯其历史及发展进程,随后对其制作工艺及构成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其主题的文化意涵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年画与模仿巫术及自我实现预言的内在关联及意义所在,并对其艺术风格的内源性宗教指向进行了说明。
朱仙镇;木版年画;春节;模仿巫术;文化意涵
过春节,贴年画,一直是中国人的风俗。自北宋以降,时逢春节,人们便在自家的门上和屋内贴上年画,以欢度新年,增加喜庆气氛,同时表达自己对未来的企盼。这种风俗延续至今,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年画,是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与内涵的艺术形式,其间蕴含着丰富的生命观念与意蕴。
年画俗称“喜画”,在不同地方有着殊异的称谓,北京叫“画片”、“卫画”,苏州称其为“画张”,浙江叫它“花纸”,福建称作“神符”,四川把它叫作“斗方”,河南称之为“花货”、“码子”。在历史上,年画的叫法也因朝代不同而各异,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关于年画,《辞海》上的定义相当简明:“年画,中国画的一种,夏历新年时张贴,故名。”[1]1044《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比之稍详:“年画系欢庆春节时装饰环境的绘画。为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因产生于农历春节的喜庆新年和除凶避邪的活动而得名。”[2]2926在中国,出产年画的地方比比皆是,“据有关专家统计,全国年画产地多达50余处。”[3]23其中有四川的绵竹、河北的武强、陕西的凤翔、湖南的滩头、山西的临汾、广东的佛山、福建的漳州等,不过最为出名的产地主要有河南开封的朱仙镇、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山东的潍坊等地。年画也随之以地名著称,依次为朱仙镇年画、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潍坊年画及绵竹年画等,在所有的年画中,朱仙镇年画的历史最为久远,被誉为中国年画的鼻祖,与此同时,朱仙镇年画也是传统文化内蕴最为丰厚的年画品类。
一
作为中国年画的源头,朱仙镇年画始于唐,兴于宋,在明朝达到鼎盛时期。其源远流长,传承有序,自诞生至今已千年有余。朱仙镇年画是一种统称,泛指开封地区的年画,其中主要包括作为朱仙镇年画前身的开封年画与狭义的朱仙镇年画。关于朱仙镇年画,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见,述及朱仙镇年画,人们多喜欢引录北宋时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上的记载,说明年画当年的繁盛。据孟元老记载,当时的东京(开封北宋时的称谓)每“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版、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4]。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年画的制作与销售的盛况。在当时的北宋,制作年画的民间作坊四处林立,宋廷官室同样也开办官家的年画作坊,在民间与官方竞相开办年画作坊的过程中,年画行业映现出繁盛的景象。
年画亦称为木版年画。起初年画的确是用笔绘制的作品,但由于民众对年画的需求数量巨大,仅靠手绘难于满足市场的要求,遂将活字印刷术引入,运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来批量制作年画。自此开始,年画便由用笔绘制转向刻版印刷,手绘年画也变成了木版年画。木版年画虽是刻版印刷的画,但首先还是要用笔绘制,随后刻版印刷。
木版年画的刻版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制作程序相当复杂。首先是选料,用来制作年画印版的选料全部是上等梨木,第一步是将梨木的表面刨平,尔后使用枣核状的穿钉,将其并合而成待刻的版料。为了使版料便于刻制,并确保以后不开裂、不变形,刻版前还需在版料表层涂上植物油,并晾干,这一程序要反复重做三次。接下来,刻工使用专用的刮刀把版料表面刮毛,使之现出毛绒绒的面相。随后拿出与版料尺寸相适宜的画稿比对,“再把画稿反贴在木板上,干后用手指反复均匀揉撮,直到画稿最薄、清晰为止,刻时木板既不夹刀,又与画稿完全一致不走样”[5]103。
前期工序完成后,即进入雕刻工序。确保与画稿完全保持一致、不走形是对刻工的基本要求。在雕刻过程中,雕版师要做到“人物面部刻线要分阴阳,衣纹线要刻出笔锋,衬景要逼真,并根据画师提供的分色稿刻出色版。镂刻每根线都要用好几种刀法”[5]103。这些刀法皆有特殊的称谓,如“伐”(紧贴线条垂直下刀)、“支”(靠外斜刻一刀)、“挑”(顺势向上起刀)、“跟刀”(沿第一刀补刻)等。待样稿的线条刻毕,便需用所谓的“文章锉”进行定版,并把碎木屑除去。制版的最后一道工序称之为“净底”,即是使用巩锉将无线条的底面锉平,使之尽量平滑,所雕刻出的版线皆要保持20.5mm的深度,所镂刻出来的线条经打磨手感要顺畅、光滑。
印版制毕,下一步即是印制。朱仙镇年画印制使用的颜色是天然颜料,由矿物、植物制成,制作极其考究,全部用手工研磨而成,其研磨出的颜料色彩十分纯净、鲜艳、明快。朱仙镇年画印制的用色多达九到十种,使用最多的是青(蓝)、黄、红三种原色,这与年画表现主题的需要、风格样式及旧时中原人的审美偏好有着内在的关联。
水印套色、木板与镂版相结合,是朱仙镇年画的基本制作方式。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题材与内容多取材于表达人们的精神诉求、内心企盼的神话传奇、民间故事、历史戏曲、风俗演义等,其生活气息浓厚,乡土意味浓烈。从画面上看,其整体构图饱满,画中人物造型既古朴又夸张,线条简洁凝练,色彩明丽鲜艳,风格粗犷而厚重,深为那时中原人所钟爱。
艺术的命运总与历史的变迁相关,朱仙镇木版年画也不例外。这一艺术形式在北宋虽盛极一时,但至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京城,为数众多的年画艺人为躲避战事而逃离京城,流落他乡,当时京城开封的木版年画业也迁至距东京有20余公里之遥的朱仙镇。时至明清时期,朱仙镇水路通畅,河道通往四面八方,遂成为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商业重镇,朱仙镇木版年画业一度兴旺,从业者超过300多家。到了清朝末期,因河道淤塞,商业活动受阻,年画业随之变得凋零。民国时期,朱仙镇上仍有40多户人家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由于对外交易日益增多,临近省份如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的客户纷纷前来从事木版年画的交易,年画业再度兴旺,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字号如天义德、天兴德、天成德、德盛昌、德源长、万盛、万通、大天成、二天成、三成义、晋涌泰等。抗战前,朱仙镇木版年画业再度迁往省会开封,年画作坊多聚集在中山路、书店街、东大街、西大街、大前门等区域,其著名的作坊字号有振源永、天福利、汇川、鸿记、云记、福盛大、隆昌等。
解放后,尤其是1966年以后,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极端的意识形态氛围及僵滞的经济政策与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载体——朱仙镇木版年画也曾一度处于濒危状态。所幸的是,有张廷旭、郭泰运、刘金录、张连生、张继中、尹国全、尹国民等传统年画艺人矢志不渝的坚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守护着这一领地,才使朱仙镇年画这一传统技艺得以传承下来,其中张廷旭在年画传承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所倾注的心血,超过了其他人,而今他也是掌握从刻版到印制全套技艺的水平最高的工艺大师。随着国家政策转好,传统艺人的坚守变得不再那么艰难,认识到传统技艺传承的重要性后,地方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给传统艺人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通过有效的方式打造文化市场,这一传统工艺再度繁荣兴旺。
二
作为古老的传统艺术样式,朱仙镇木版年画与中国传统农历春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逢农历新年,人们除了扫尘、守岁、放爆竹、蒸年糕、拜年等活动外,还要贴年画和春联。从表面上看,贴年画和春联只是为了增加节日喜庆的色彩,平添欢乐的气氛,而实际上这一活动有着积淀于底层的深意,它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而且彰显着生活的信仰,投射出生命的价值观,透过具象形式,贴春联展现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乐等民俗与文化观念,且是一种具有浓重的社会无意识的仪式化活动。其间蕴含的意义有待深入开掘。
年画最早源自远古宗教祭祀仪式,意在驱邪禳灾,迎新纳福。年画中的门神有两个重要种类——门神与灶神。依据唐代杜佑的《通典》及元代马临端《文献通考》记载,可追溯至殷商时代人们对此类神明的崇信。在商周时代,与门神、灶神有关的祭奠已成定制,并被纳入“礼”——典章制度的理论核心之中,包括门神、灶神在内的“天子七祀”的祭奠活动,遂成为上至君王诸侯、下至黎民百姓膜拜的宗教祭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的说法较此稍晚:“年画最早约萌芽于秦汉之际,时逢除夕便于门户上画神荼、郁垒及虎以驱鬼魅不祥之物。”[2]2926到了汉代,门神、灶神的艺术雏形已具,初时大多直接画于门上。至隋唐,门神题材和内容开始变得多样化,儒、道、释等宗教观念与形象融进年画,世俗生活中的主题与内容亦成为年画乐于表现的东西。到了宋朝,年画的体系业已形成,作为中国年画最早的完备形式的朱仙镇年画,足以用来表达人们的精神诉求与世俗企盼。
朱仙镇年画的体系是庞杂的,但经梳理仍可分辨出主要的几种类型构成:一是寻求佑助与保护,二是追逐尘世生活的成功,三是注重宗族的延续,四是寻求世俗欢乐,五是重伦理教化。但无论是哪一种,几乎都与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通常是某种类型的神、仙、圣、佛、皇、帝、王、将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力量或现身或隐形,始终在背后起着支撑作用。就具体形式而言,各种形态多种多样,不同的年画作坊有各自擅长的表现题材与表现形式,辑录者有自己的偏爱,加上各自的局限性,作为朱仙镇年画大全的完整汇集通常难于看到。据统计,朱仙镇年画总共有2000余种,可通常人们看到的不超过50余种。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收录约近60种,谢瑞祥的《朱仙镇年画七日谈》中收录年画有40余种,而由开封县文化局、文保局天义德年画作坊编辑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锦》,仅收录16种,即“和合二仙”、“刘海战金蟾”、“钟馗”、“加官进禄”、“步下鞭”、“马上鞭”、“火塘寨”、“柴王推车”、“三娘教子”、“福禄寿三星”、“麒麟送子”、“五子登科”、“岐山脚”、“凤香兰”、“长坂坡”、“妈祖”等。
这些辑录虽品种有限,但类型齐全,且多蕴含着某种形态的恒常主题与观念。依据吕品田的表述,中国民间艺术(朱仙镇年画为其中一种)通常皆表达驱邪禳灾、纳福招财、祈子延寿等几大主题,而在大主题类属下,又囊括着一些子题,如在祈子延寿主题下,他又列出四个子题:情恋婚嫁、阴阳媾合、生子继嗣、延年益寿等,针对每一个子题,他分别给出了对应的具体艺术表现形式。不过,他也承认,有些艺术表现主题很难合适地归类。“有许多恒常的主题,是难于将它们按单一功利倾向划归的。”[6]40他言及的这类主题通常具有多义性与综合性。按照他的解释,这类恒常主题带有抽象意味的吉语加以标示,如“吉”、“祥瑞”、“洪福”、“双喜”、“龙凤呈祥”、“如意”、“和合”等。虽说这是一种解释,但若从另外一种维度来看,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规划在趋吉纳福的主题之下,尽管它们没有具体实体指向或具体情境方面的喻指,如规避何种灾难与不幸,获取何种功名利禄,喜得什么样的子嗣等等,但它们在总体上皆指向凶险的规避,指向对吉运、人生在世如愿、适意、万事顺利等的期待,实际上它们依然与诸多具体形态的带有实际功利取向的追求完全一致,只是更为抽象而已,因而适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三
就种类与表现形式而言,朱仙镇木版年画虽多种多样,但经合理的分析与归纳,依然可以做某种形式的抽象、归并与综合。以上五种类型划分,即“神明佑助”、“追逐成功”、“宗族延续”、“世间欢情”、“伦理教化”,大体上可将所有的年画表现的主题容纳其间。从源头上说,朱仙镇年画的主题来源于生活本身,来源于中原地域的人们在和自然、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观念与意想,源自他们的现实实践与精神实践活动。从微观的意义上看,人们的生活千差万别,彼此之间的境遇各不相同,有各自殊异的选择与生活方式,但从整体上来考察,人们的生活依然有着无法否认的同源性与类同性,有着明显的原型意味。
人之在世首先是为了生存,威胁人类生存的力量既来自内部,更来自外部世界,人们在其生存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狂暴的自然力:洪水、干旱、火山、地震、霹雳雷电,以及由此引发的瘟疫、饥荒、灾难与死亡。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首先与这类自然力达成和解,通过某种形式的活动,让其远离人类的世界。依照古代人的认识,天地之间存在着掌管这类自然力的神明,膜拜这类神明,并向他们祭献,祈求神明佑助,即可避免灾难的发生。
继生存问题的解决,人们即追求生活的质量,满足自己的欲求,与生活质量高度相关的是一生的命运(厄运与吉运),以及在其一生能够获取的功名利禄。尽管人的努力与获得这一切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仅靠人自身的努力仍然不够,还需天时、地利、人和,需和合之力,需要某种强大力量的佑助,方能有人们期待的圆满结局。
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另一类要素,是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这是人生在世的根本价值与意义所在,没有快乐与幸福,就失去了生活在世界上的理由。因此,追求欢乐与幸福一直是人们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幸福和快乐有显在的表征与具体形态,而这也是木版年画艺术家乐于表现的主题。
人的幸福与快乐既与人的能力有关,与成就人的隐形的力量相关,也与成为至善者、成为代表正义的勇者有关。善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神明的某种品格,由于自身的各种不适度的欲求和弱点,人们极易误入歧途,容易堕落,因而伦理教化的功能与价值始终为人们所重视,尤其在人成长的过程中,教化的力量通常是使易于接受诱惑、偏离正道的人成为善者、圣者、能者、智者、强者、勇者等的关键。
生存与繁衍是所有永恒主题之中最为重要的主题,繁衍是人类种系得以存续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育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意义。生育力成为判定一个人的价值的重要指标,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是不合格的人,甚至是废人,因为他/她打断了其族系存续的链条。这就是为什么民间艺术总刻意表现繁育与子嗣主题的根本原因。
时间的推移造就各种各样的变化,但生活的主旋律却始终未变,积淀在一再变化的艺术形式之中的主题却依然如故,显示出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反复体验着这种生活,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感受这类主题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与地位,这类主题永不过时,因为它们始终与人们的基本生活经验类型、与人们最为重视的生活内容、价值与意义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对应性。
从具体的木版年画现象上看,我们特别容易看到这种关联性与对应性,“驱邪禳灾”、“纳福招财”、“祈子延寿”等,总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重视的主题,事关人们在世的幸福、欢乐、价值与生存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魅力,这些年画能以形象的方式表现人们生命的企盼,从生命深处拨动人们的心弦,令他们感动。年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卫着他们的梦想与希望,诉说着他们的心声,展现着他们的追求。
神荼与郁垒是最为古老的的门神,有驱鬼避邪之功。古时在木版年画出现之前,人们把他们画在门上,用作自己的保护神,已达到驱邪禳灾的功效;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喜欢把他们的像贴在门上,左扇门上贴神荼,右扇门上贴郁垒,以期其佑护。与他们相比,钟馗更为知名,钟馗是中国民间驱鬼除邪的神,是赐福镇宅的圣君,在所有种类的年画中都有钟馗的画像,虽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其功用则完全一样,即镇宅辟邪,护卫平安。
木版年画“福禄寿”是囊括人生内容最多、也最具原型意味的年画之一。人在世之福形态多样,人们在生活中所具体感受与体验到的福千差万别,但统称为福。在年画中,所有之福皆由位于画面中央、手指如意的“赐福天官”所赐。禄在《说文解字》中解义为福,禄是福的一种,通解为官俸,意为在世为人成功而获取的收益,其喻双重的收获:一是为官(才学、能力获得承认的标志),二是为官的收益(财富、权势、功名等),由画中怀抱婴儿的“禄星”所给予。寿是国人最看重的人生之福,历来为人所重视,在人的一生中,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有了生命,才有可能尽享尘世的欢乐,这一人生之福在年画“福禄寿”中由手指拐杖的南极仙翁所代表。
“财”为人们的生活之本,物质生活的满足离不开“财”的支撑,过年时人们相互间说的最多的祝语之一即是“恭喜发财”,朱仙镇年画中的财神型作品有“刘海戏金蟾”、“岐山脚”、“柴王推车”、“摇钱树、聚宝盆”等多种表现形式,表达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
家族的延续是传统中国人的神圣使命,生育是家族延续的必由之路,但仅靠人力似未必能够如人所愿,还需有其他力量的佑助,要仰仗主生育的神仙及与之相关的神兽,“麒麟送子”、“送子观音”是朱仙镇木版年画中人们表达这种心愿的最为典型的形式。
至于表现功名、世间欢乐、伦理教化等题材的木版年画,数量多,形式变化多样,如要具体说明需要大量的篇幅。但所有这一切皆来源于人们的生命实践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总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展开,集中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力与超自然力的敬畏,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安泰、人马平安、功成名就、财源滚滚、欢乐幸福、子嗣满堂等意愿的表现上面。
四
作为年画的一种,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有着特定的时效性。年画总是在过新年时张贴,这其中有着一种深意,新年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是充满希望的生活的起点,此时张贴年画标志着为未来的生活进行意向性的筹划,对新年的生活做一种先行的建构。
在一般人看来,贴年画是过春节时一种约定俗成的惯常行为,其实这一行为是有着深意的仪式化的活动。仪式活动涉及赋义与授权(获取合法性),缺少仪式,其正当性就得不到承认,其内涵的意义与价值也同样不被承认。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年画曾被作为“四旧”破掉,贴年画被剥夺了合法性,年画中蕴含的主题的正当性同时遭到否定。所以,贴年画这一活动绝非像它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仅为一种简单的娱乐形式,一种游戏性的装饰活动。
从文化分析的视阈来考察,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活动,贴年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赋义活动,事关生命活动的动向、价值与意义。仪式活动是一种先于现实的观念实践与精神实践,以这一实践作为先导,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构未来的生活。古时的人们根据自身经验,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了自身的努力外,皆需外力的佑助,方能达成所愿,因而通常举行多种形式的祭拜仪式,希望借助多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建构自己的未来。年画原本即是神符,人们通过画神符、贴神符来驱邪禳灾、佑护平安。古时人们使用神符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精神诉求,与巫术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神符的使用原本就是巫术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对生命深处的声音最为确切的表述。古人有关神符的使用类似一种模仿巫术,以相似事物为代用品来求吉避祸,通过某种神秘的关联形式,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联通,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使自己的意愿最终得以达成。那时人们对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活动的效力深信不疑,如同今天的人对科学的效力一样相信。就其精神努力的过程而言,两者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巫术实践与科学实践的效力在结果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对世界运行的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人自身的力量在生活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越来越感到人与神明的关系不那么靠得住,在意识上甚至不再相信神明真的存在;在生活中,人更愿意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然而在无意识之中,在心灵深处,人们还是感觉到存在着高于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始终对人类生活产生着作用,有时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从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人们对这种力量还是心存畏惧,同时也心存敬畏。人们喜欢吉言,希望吉言成真;畏惧咒语,害怕咒语变成现实。开车的人最害怕有人提车祸之事,乘坐飞机的人严禁说飞机失事,只要是在飞机上言说飞机出事,无论是何人,肯定要被撵下飞机。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表面上看,人仿佛越来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相反的事情经常发生,自然不是变得越来越驯服,而是越来越狂暴,越来越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与高于人类之上的存在和睦相处,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年画中表达的人对高于自己之上的力量的敬畏与信任值得我们留意,年画中显现的主题对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值得我们深思。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贴年画有着非常积极的建构意义。它不仅可以增加欢乐喜庆的气氛,美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以形象的方式为未来生活提供目标与实践的导向,对来年的生活进行筹划,并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进行先期的意向性的实践。在看似游戏娱乐的活动中,让生命的真意、生命的追求及生命的理想具体地显现出来。贴年画,事实上是一种无意之间的对未来生活的积极建构,无形之间做了预言自证实践的第一步。
预言自证实践是这样一种实践,它首先进行情境设定,这种设定为人们提供实践的动力与实践的动向,随后人们开始根据情景设定进行实践,当实践的时机到来,实践行动到位,预言就会变成现实。
预言自证实践也称之为自我实现预言或托马斯定理。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言称,在人们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无论是社会领域或公共领域,还是个体或私人领域,都有自我实现预言作用的痕迹。人们只要把情境当成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因为人们不仅对情境的客观一维产生反应,而且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同样产生反应。一旦人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随后的行动及行动的结果将受所赋予的意义的决定。年画中的情境多是神话或传奇式的情境设定,但它们皆有很明确的尘世生活的意义指向,尽管具体的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指向“神明佑助”、“追逐成功”、“宗族延续”、“世间欢情”,“伦理教化”等几种基本的极具原型意味的情境定义,为人们的现实努力提供了动力与方向,给人们以希望与梦想,为人们的理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形象性的观念创造生活,创造人们的未来。
五
与其他地区的年画相比,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最早的木版年画在造型、风格与色彩方面皆独具特色。以往的研究者曾有不少研究,其基本观点大致相同,表述大同小异。他们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古朴夸张,构图饱满,色彩艳丽新鲜,线条粗犷简练。具体来说,即是其造型强调头部的重要性,头大身子小,人物形象在比例上给人感觉有点古怪,具有喜剧效果,脸部少着色,看上去和谐自然。在用色上,朱仙镇木版年画用矿物、植物作原料,使用水色印刷,色彩纯净,明快鲜艳,其使用的颜色有黑色、大红、槐黄、铜绿、葵紫、章丹以及苏木红、金色、银色等。朱仙镇年画的构图很满,画面留下空白的地方,显得密实、紧凑,空间大的地方加一些吉祥花草,增强画面的紧凑感,整体上主次分明,有着一种特殊的美感。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在谈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点时,除了在设色上提到了五色相生的用色理念外,在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单纯地谈论其风格的外部特征,几乎没有涉及任何与木版年画内在构成相关的内容。事实上,风格是内在观念构成的外在显现形式,如果能够从内部观念构成来考察其艺术风格,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处的一些意味。
显而易见,朱仙镇年画与其他木版年画相比,看上去更具有传统的风貌,其造型风格古朴,色彩凝重,人物造型方式奇特,与其他种类的年画形成了鲜明对照。其风格的样式显然与文化有关,与传统紧密相连。在此,我们必须思考其艺术风格与原始宗教的内在联系。
年画起源于原始宗教与祭祀仪式,作为祭祀用品,自然要符合其内在的需要。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可以感受到敬天或敬拜掌管命运的力量的深切意味,其人物造型,尤其作为神明的人物造型明显具有神性的特征。就身体的各部位而言,头部或面部是最具表现力的,尽管雕塑家罗丹言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具有完美的表现力,也许他的观察力让他得出这样的观点,但在一般的观者看来,脸部的表现力始终是最强的,因此着力表现面部或头部能够获得最佳的表现力。假如人们稍加留心,即可注意到,朱仙镇木版年画上面的人物不仅头部明显较大,而且眼睛也很大,在人的身体上,头部最具表现力,而在头部,眼睛也比其他的部位更具表现力。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人们的感受是雷同的,这可以用欧洲中世纪拜占庭教堂壁画作为佐证。中世纪崇尚灵魂生活,贬低肉体生活,为了表现精神的重要性,拜占庭教堂壁画将画中人物的眼睛画得奇大。
色彩与观念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朱仙镇木版年画在用色上使用五色相生的理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古人看来,黑白青黄赤的五彩世界是由日月天地昼夜更替、四时转换的自然时序染触的,他们要依据观天象来从事耕作,自然会格外关注这五种作为时令变换征候的色相。从刘熙《释名·卷四》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释义:“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无须说,古人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与这“五色”有着显在的利害关系,因此在画中巧妙地使用这种观念浸染的色彩有着深层的含义。通常的研究皆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色彩鲜明艳丽,但我个人的感觉却并不一样。我个人的感受是朱仙镇木版年画色彩凝重,与其他种类年画相比,尤其是与杨柳青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相比,后两者要艳丽许多。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人物与其他物象的塑造上主要用线,加以套色,其风格极为简练,这与宗教祭祀与仪式的要求完全相合。古时创作此类作品时,要求简洁,富于表现力,清除一切多余的、不必要的修饰,否则会妨碍主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达。无论是从远古的岩石壁画上,还是从远古时代的雕塑那里,人们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证据。与之相比,世俗意味浓烈、注重表现市民生活快乐的杨柳青年画与桃花坞年画的画法显得繁复、艳丽、装饰性强,用色明快。
本文只是试图提出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宗教祭祀及仪式的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其艺术风格,有关朱仙镇年画这一方面的较细密的探索与研究有待于进一步进行,以便找出两者之间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更为巧妙的内在联系。但无论如何,从这样一种角度来探讨朱仙镇年画的艺术风格,或许能够找到真正揭示其内在关联的、更具合理性的解释。这也正是本文提出这一研究角度的意图所在。
[1]舒新城,等.辞海[Z].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中国大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3]谢瑞祥.朱仙镇年画七日谈[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4][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M].王永宽,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5]冯敏.新春吉祥画:中国木版年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6]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2012-03-25
张月(1959—),男,河南开封人,社会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艺术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
G127;J607
A
1008-3715(2012)02-0001-06
(责任编辑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