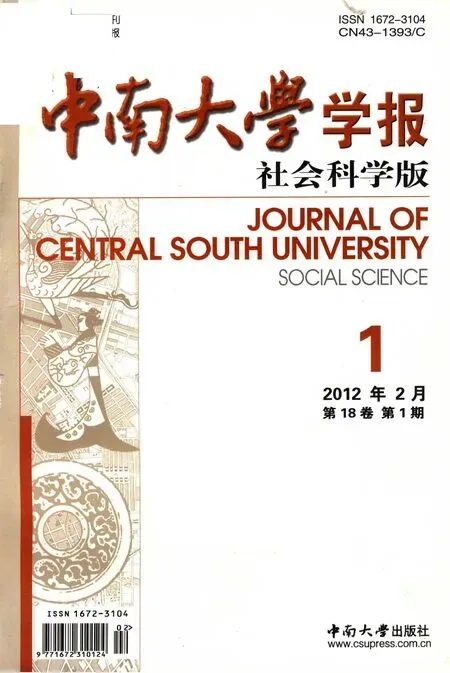都市麦田里的乡土守望者——从赵本夫《无土时代》的小说主题说起
2012-01-21许心宏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230030)
赵本夫以《卖驴》《天下无贼》等作获得了读者的关注。其小说创作主题一直关注现实问题并有着自己的思考。新世纪以来的“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与《无土时代》共计80余万字。如作者所说,《黑蚂蚁蓝眼睛》写的是文明的突然断裂,《天地月亮地》写文明的重建,而《无土时代》写的则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追问。但《无土时代》(2008年)实难归纳为乡土文学或都市文学,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在文学体裁上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有着神似之处,即它是一则文学寓言。不过,就《无土时代》而言,关注的是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叙事者文化心理根植的问题。
一、“无土时代”的城市化隐喻
赵本夫《无土时代》中的“木城”只是一座寓言化的城市。小说标题为“无土时代”,而小说中的城市却叫“木城”,在此意义上,如果“木”没了“土”,那“木城”只能是枯萎的“死城”,因而“无土”的寓意所指,即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人类越来越远离土地与自然的事实。城市皆为人造,而“人造”却与“自然”相对。小说中的木城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记忆,花盆则成了他们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木城人对季节、夜晚、方向的感知麻木,这与贾平凹《怀念狼》《白夜》的叙事主题非常一致。小说在虚与实、抽象与具体、城市与乡村的构想中,“木城”指向的是文化生态的理想之城,否定的是纯粹的人造水泥森林。小说中写到“大地是城市的本源,是城市的祖先”。在对大地宗教感的原始崇拜中,作者认为“关注大地,就是关注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关注大地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关注文明对大地的影响和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变异”。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9−10)“乡土中国”是对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总体概括。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促发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心灵的阵痛与调适。就《无土时代》而言,“无土”离“乡土”与“故土”渐行渐远,在都市的喧哗与躁动中,乡土故园似乎成为边缘的沉默风景。不过,就《无土时代》的文化价值诉求与定位而言,显然与“寻根文学”有着文化心理的潜在共通性,其“向后看”的心理动机是“未言明的反城市情绪”,理论资源是“农耕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说”,小说叙事形式上的空间与时间的“置换”,使得“‘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虚化’的前提,因而具有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2](16)小说通过草儿洼方村长由乡进城的“乡村见证者视角”与“城市访客”的“陌生化视角”,一方面叙说了乡村社会正在失去“地气”与“人气”,另一方面,叙说了木城郊区苏子村正在“被城市化”,因而草儿洼与木城的时空意象的并置,在时间的“回望”中存有农耕文化的怀旧情怀。
《无土时代》叙述主题与王安忆的《华舍住行》及《上种红菱下种藕》颇多一致。后者在抵抗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际,营造了古典诗学的乡村时间,继而在时间的对抗中寄寓着人类永恒的乡愁。不过,她也很无奈的“自我解构”到:“文学忒虚无了,我只能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3](243)同样,与贾平凹的《土门》相比,后者的“仁厚村”被城市化吞噬了,主人公梅梅虽然理智上认同了现代文明,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城市化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只能在“母亲子宫隧道的尽头”才看到“神禾塬”。“神禾塬”只是重返“玄牡之门”的诗学构想,因而“土门”不过是乡土之门、家园之门的代言词。从词源学上说,“门的最原始的意义是家园”。“门”又称“户”,户即“护”的本字,因而家园的“门”意味着“防卫”与“保护”之意。[4](154)它与“人造之城”相比,“土门”存有农耕文化的自然胎记。其实,“土门”意象并不新奇,陶渊明《桃花源记》云:“从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在隐喻性解读中,“桃花源”的“便舍船,从口入”何尝不是重返“母亲的子宫”呢!因为“世上的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5](7)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以《无土时代》为代表的“无土时代”家园主题的叙事,从“无土”转向“有土”的重返大地自然,其实是在敬畏自然的心灵法则中,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意栖居地。
二、“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话语
从叙事学角度说,无论叙事者如何伪装自己,但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话。巴赫金指出:“艺术家为形成确定的和稳定的主人公形象而进行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与自己的斗争。”[6](57)在“离乡—进城—返乡”的空间迁徙中,“木城”的天易已不再是“草儿洼”的天易,作者将其分裂成天易、柴门、石陀三个人物面影的扇面,但在精神血脉上都还是草儿洼的后裔。小说在扑朔迷离的“探秘”过程中,石陀这位“木城隐形人”的真实身份最终得以解蔽,即“天易=石陀=柴门”,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种植情结”,因而,寻找“石陀”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农耕文化记忆的美学历程。
(一)石陀的精神面影
石陀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拆除高楼,扒开马路”,如是话语无非是“反城市主义”的集中体现。进城后的天柱和天易,他们都有极强的“种植情结”,这无疑是眷恋农耕文化的体现形式。特别是石陀深夜身穿蓝布长布衫,在僻静幽暗的城市街道开凿水泥路面,俨然是木城的“文化守夜人”。从认知叙事学上来说,石陀为什么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开凿路面种下谷物呢?实际上,行动时间的“黑夜”与地点的“僻街”之选择,无不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激进与行动上的退却,因而“反城市主义”终究还是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当然,石陀身为政协委员,其政治身份的“边缘”与“游离”,就已在权力话语的罅隙中表明他只有“建议权”而无“主导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石陀的做法是否就具有普世价值呢?“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城市化难道就是社会发展的歧途?人类真的错了?其实,在小说文本中,叙事者是以“介入叙述”的方式担当了社会“立法者”角色,因而石陀、天柱、方全林等人物设置,不过是其心灵镜像的一个个投影。以小说文本为中心,从叙事者到作者,内中则始终存有一根未剪断的“脐带”,它的母体就是作者,作者在《天地人》一文中有着这样的心理自白,即“因为和城市生活保持着距离,不是不能进入,而是根本不想进入”。[7](59)细想起来,“不能”和“不想”是两码事,前者是“他者”因素的限定;后者是“自我”因素的心理排斥,体现的是“城市梦魇”与“乡土根植”情感对立的难以调和,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在《培植一种城市美学》中指出:“工业社会的城市,到处都是缺乏特征的办公楼、商业区、市郊住宅和购物广场。这些地方并不生产标准化和无个性的居住者,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8](82)
在人物意象塑造上,小说中的“天易几乎一出生就属于另一个世界,早慧而又愚钝、早熟而又懵懂,喜欢在夜晚追赶星星,在蓝水河里和奇形怪状的鱼们嬉戏,喜欢伏在地上谛听大地的呼吸”。因而他的“寡言”“木讷”“孤僻”“犯傻”“既是天才又是白痴”等人物性格的雕刻,内中存有道家哲学“大智若愚”与“大巧若拙”之美。另外,天柱去龙泉寺拜佛,佛说天易与草儿洼的大瓦屋家没有俗缘,只有生身之缘,巧合的是,天易娘也认为儿子的出走是“天意”。根植在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如果说道是“修身”,佛是“治心”,那么天易在“身心双修”的佛道情怀中,无疑则是“身心分离”的颇具文化寓言意味的人物符号。小说中通过梁朝东的跟踪“探秘”,发现他深夜拿着玫瑰潜入了象鼻山,而不是公园、茶馆、酒吧等现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因而,空间选择的别样,旨在叙说他在逃脱“城市白夜”的文化重压,向往的则是乡野自然的宁静与安详。特别是在城乡时空“交叉蒙太奇”中,天易娘的死、扣子与刘玉芬的出走、草儿洼的千年神龟的消失,以及以草儿洼为代表的“即将消逝的村庄”等意象,都具有文化寓言意味,因而在农耕文化的哀伤与巡礼中,隐喻的是一个时代的远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土时代》的叙事主题与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外祖父的死与白塔的坍塌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虽为城市化时代的寓言,后者虽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寓言,但总体上都给人一种莫名的文化失落感和坍塌感。
(二)天柱的精神面影
木城的城市化将“方圆几百里的地方给毁了”,天柱认为“木城修造那么多的高楼是造孽”,于是他对进城的方全林村长说:“有一天我要把整个城市变成庄稼地。”在天柱眼里,城里人种花、种草其实是对祖先种植的记忆,就是木城的城里人,在他看来三代以前都是农民,因而“种植情结”不过是农耕文化记忆的一种本能。不过,天柱却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天柱的木城绿化队也是由草儿洼的农民工所组成。在“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将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小说叙事中,他们最终在木城种下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在这场窃喜、尽兴、刺激的种植劳作中,石陀就是其中的一员。小说的结尾,木城种上了高梁、小麦、玉米等作物,在双休日,木城的马路上行走的也是马车而不是汽车。其实,农耕时代的“器物”与“作物”的空间移植只是思想表现的感性形式,而作者所极力表现的恐怕则是农耕文化的心灵移植。小说中的“木城”是虚构的,《木城晚报》则是虚构的虚构,但就是在《木城晚报》上却刊出了两条惊人的消息:“其一:据一赶毛驴的老汉称,昨夜凌晨三时,数万只黄鼠狼在子午大道上集结,毛驴惊惧不敢前行。半小时后,黄鼠狼又突然消失了。其二:据网上报道,在中国的其他十多个大城市中,也相继发现了玉米、高梁和大豆……”因而,小说中的“城市田园”无疑是敬畏与亲近大地自然的文化心理表达。
(三)谷子的精神面影
自从天易失踪后,通过谷子的“探秘”视角得出,他曾去过小镇、山村、海岛、码头、沙漠、荒原等地方。基于自然景观与人造之城的对立,谷子的西行之旅,其实是石陀精神血脉的代理人。谷子在玉门关巧遇“女巫”与在阿坝偶遇“白衣老人”,他们似乎很清楚谷子在寻找石陀的踪迹,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其实,这只是叙事者在“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中所虚构的文学场景,旨在突出柴门作为农耕文化幽灵的存在形式。西部景观如阿坝、黄河第一湾、九寨、羌寨、敦煌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玉门关、戈壁荒滩等,虽说地理景观虽有差异,但内中却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是远离喧嚣的、人造的都市社会,从而在都市逃离的远观中荷载古典气息的隐逸之心。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社会中,谷子心灵镜像的对西部的乡野、旷野的迷恋,特别是西部边地风景的高山峡谷、原始深林、积雪和冰川、大草地等,在叙事者“去粗取精”与“去陋取纯”的心灵淘洗后,业已成为“心灵避难所”的文化诗学空间。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一体两翼”发展,现代化为“一体”、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两翼”,在“无土时代”的城市化发展中,人类却越来越远离大地、自然、乡村,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处于悬空的家园漂泊中,《无土时代》的小说标题显然是城市化进程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有“城市化”就有“反城市主义”,这是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不过,根植在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在文化心灵还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反城市主义”都突出表现在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否定上,不过在否定之后又表现出对大地、自然、荒野的向往。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精神家园似乎永远“在路上”,或者说“生活在别处”。“无土时代”中木城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生存和谐,不过也正是在不和谐中,人类有了家园意识的觉醒与复归,因而小说中“寻找”意象与乡野、荒野意象的“重复”,成了“过程美学”心灵净化的仪式。在纵向比较上,西方工业文明起步比中国早,但西方学者却认为“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9](520)不同的是,在乡土中国,积淀在文学之乡中的儒释道思想,山水诗意情怀、人格境界象征等,虽经五四以降的“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等审美现代性批判,内中有其“恶魔性”“迟滞性”与“劣根性”等文化陋习因子存在,审美主义“大用”使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托身得所”。
三、叙事者“城市”书写的文化心态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自现代乡土文学伊始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师陀等,到当代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作家张承志、铁凝、王安忆、史铁生等,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再到“后乡土文学”的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以及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中“后乡村文学”作家的刘亮程、韩少功、迟子建等,在城乡情感结构上,身在都市而心系乡野成为其文化心理的惯常表达,文学镜像中的乡土故园、女性大地、自然田园等意象,几乎成了抵御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线希望,成了澄明人性、挽救社会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小说家不是都市的颂扬者,相反却是其批判者。不过,在纵向比较上,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通过对伦敦城的长期研究,倒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按照一种荒谬的逻辑,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大,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也越多”。[10](160)
在《无土时代》的文学寓言中,置身木城的石陀认为“城市把人害惨了,城市是个培育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城里人没有满足感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没有闲适没有从容没有真正的友谊”。并且石陀假借柴门的话说“人类在发展史上最大的失误是建造了城市,那是个罪恶的渊薮”。因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离开乡野已经太久了,为什么不重回大地,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特别是石陀在政协会议上说:“木城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的产生都源于不接地气。”因为在水泥森林的城市中,“人和大地隔开了,于是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11](11)源于木城不接地气,又远离自然乡野,因而作者构想了三百六十一块“城市麦田”。实际上,这种构想并不新奇,因为早在1983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就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写到:“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2](6−9)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和“城市——乡村”(Town-City)实则是城乡文化整合后的理想之城,将城市社会与自然美景有机整合起来。在中国城市化进城中,文学叙事不乏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文学构想,如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神禾源”其实就是一座“田园城市”,内中的社会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城乡区,它是城市,有城市的完整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它是农村,但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那里的交通方便,通讯方便,贸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但环境优美,水不污染,空气新鲜。”[13](107)因而,《无土时代》中的“城市麦田”与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无疑都带有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思想印迹。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呢?实际上,石陀的文化心理并不奇怪,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由“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蜕变中,即“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之变形,在基调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14](30)然而社会形态的转变,并未带来文化观念的“与时俱变”,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乡村高于城市”。[15](4)因而对都市工商业社会产生了“抵抗情绪”。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16](2)然何谓“中国文化传统”?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17](15)费孝通先生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实质上是“五谷文化”与“土地文化”。[18](33)因而,在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地基上,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最重,确为中国的事实。”[19](17)根植在农耕文化传统中,重义轻利观念,再就是对人的文化身份的“士农工商”的惯有划分,如章太炎所说“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入劳身苦形,终岁勤动”。[20](314)这使得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业文明进程中的“恐变症”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群体现象,因为“小农心态往往认为都市生活是‘腐化的’,而农村的愚昧则是‘民风淳朴’,因此一切都得还原到原始状态”。[21](427)以农耕文化的道德依据为制高点,城市是万恶之源,因而,猜疑,有时是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经常表现出文学的“反城市主义”的思想倾向。反观“五四”以降的中国乡土文学,无论是沈从文式的乡土抒情,还是鲁迅式的乡土批判,乡土作家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心理紧张关系,使其惊骇与梦魇的,并非“城市”本身,而是叙述者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心理厌恶与恐惧,用作家莫言与刘醒龙的小说创作来说,就是“血脉在乡村一侧”是其文化心理的最终依据。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史上,很多作家标榜自己是“乡下人”“农民”“地之子”。问题是,既然那么痛恨、诅咒城市,那何不“返身回家”成为乡野村夫一员呢?对于此项疑问,西方学者萨缪尔·约翰逊的观点倒是有借鉴意义,即“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离开伦敦的,一个对伦敦厌倦的人,对生命也就厌倦了;因为生命能付出的一切,伦敦皆有”。[22](336)在此意义上,《无土时代》中叙事者文化心灵向度上的“重返自然”与“重返乡土”,恐怕更多的是在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与家园归依感。不过,在对城市持有“敌意”与“质疑”之际,不妨看看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如果(城市)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深的漩涡”。如果要避免“地狱”带给人的痛苦,其解决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23](166)《无土时代》中对“城市文明病”“丑陋的城里人”“城市暗娼”“烂街”等都市镜像的描摹,无疑是为石陀的“反城市心理”找到坚实的现实依据,用石陀的话说,那就是“城市错了,从垒上第一块砖墙就错了。城市是人类最大的败笔,城市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其实,如是文化心理的再现,是叙事者农耕文化心理根植所带来的心理惊恐与文化伤怀。不过,“寻根文学”作家阿城曾说过:“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因而,处于文化转型期的“恐变症”,用加拿大学者保罗·谢弗的话来说,就是“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地方在坚持这种或那种方式的认同和文化认同时没有经历过惨痛遭遇。虽然就长期来说,这往往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就短期来说,这往往是极为惨痛的经历和一个痛苦的过程”。[24](69)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2]吉尼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3]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4]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的文学原型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齐美尔.桥与门[M].涯鸿等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1.
[6]巴赫金.巴赫金集[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7]赵本夫.大地人[J].时代文学,2003,(4).
[8]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M].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9]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5.
[10]ROY P.A Social History [M].London: Har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1]赵本夫.无土时代[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2]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13]贾平凹.土门[M].广州: 广州出版社,2007.
[1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上海: 三联书店,1998.
[15]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6]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8.
[1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
[18]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北京: 知识出版社,1985.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7.
[20]章炳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2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北京: 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
[22]包斯威尔.约翰逊传[M].罗珞珈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3]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宓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24]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