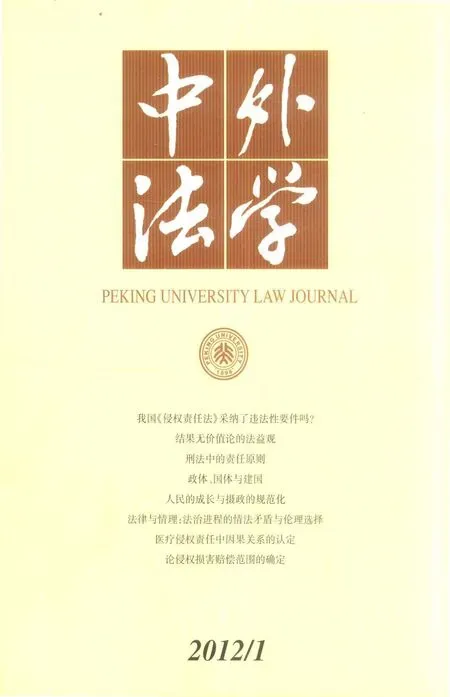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
2012-01-21简资修
简资修
前言
科斯对经济学拨乱反正,意外地也为法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J.L&Econ.1(1960),in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 95-156(1988).一文中说:资源使用冲突的场合,一旦法律定了分,不管权利归属何人,经过市场交易,资源最后总是归向最高价值者,社会产值因此最大了。法律与经济因此有了连结。他又说:但由于现实世界的市场交易有其成本,阻碍了有些交易之达成,为了最大化社会产值,法律在定分时,可直接将权利归属于使用价值最高者。法律与经济如此又有了进一步的辩证关系。
身为经济学家的科斯,其说法严重冲击了经济学。经济学一向认为若有未经补偿的损害存在,是市场失灵,若无政府介入,社会产值即非最大,而科斯却说,只要权利确定了,即使损害未受补偿,社会产值仍是最大的。法律经济分析往往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但科斯此一说法,反而有些法律帝国主义的味道——因为法律权利之确定,决定了社会产值是否最大。不过,就法学而言,将经济后果纳入法律界定权利的考量,已非依法言法,则法律是否也丧失了其防止恣意之本质?
甚多论者质疑所谓“科斯定理”的有效性,〔2〕See e.g.,Robert Cooter,The Cost of Coase,11 J.Legal Stud.1-33(1982).但无成本交易之定理化并非科斯本人的发明,也非其理论之核心。科斯的说法是经验性的。权利的确定是有助于市场交易,而市场交易必然导致了外部效应的內部化,则从社会产值最大观点言,权利确定而非损害补偿才是其关键。反观,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并无现实经验的內容,因为人与生俱来有交易的倾向,市场交易是一定存在的,而且甚为活络,则外部性安在哉。
从资源使用冲突角度看,科斯将损害相对化了,有法学论者因此质疑其非法律真实,但这是混淆了法律概念与法律价值(或目的)。在法律概念(准则)的操作上,损害、因果关系或财产权是有其一定的意义,但此无碍于衍生这些法律概念的价值有其独立性。社会产值最大化也许不是法律唯一的价值,但绝对是其中之一,则损害相对化即是法律价值的一部分。
法学论者或许更担心的是,将经济后果纳入法律界定权利的考量,是否会造成法律的恣意,从而导致法律自我矛盾?长期上,非也。科斯此一主张,是延续其公司理论而来,则法律仍受市场及其他公司的竞争约束。科斯在《公司的本质》〔3〕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1937),in supra note 1,at 33-55.一文中指出,由于市场交易有成本,公司以其较低的管理成本取代了市场,因此公司的规模不会无限制扩大,而是要受限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另外公司管理成本的制约。同样地,法律一如公司,也必须受到这个约束,但由于现实经验之不同,约束会有不同。但不管如何,现实法律视其所在法律系统为何,或多或少都呈现了此经济结果考量的特征。
法律经济学虽然蓬勃发展,但以庇古为范式的经济分析——假设不切实际(尤其在市场与政府间之不一致)或案例报道不实──并非绝迹了。科斯援引现实法律,批判福利经济学,促成了法律与经济学的联系。科斯的本意是,经济分析若未将现实法律考量进来,其结果是空的,所谓黑板经济学是也。如今的法律与经济学之结合,恰好相反,是以经济方法分析法律。这原本也无不可,甚且应该是学术发展之必然,但庇古式经济学经此转折,反而在法律经济分析上大行其道,而科斯比较制度的经济学却被埋没了。或许当法律研究者不再惑于经济分析的技术而正视法律本质时,一如科斯正视公司的本质时,科斯经济学既是相关的,而且也才法学化了。
本文分六节。第一节前言。第二节将说明为何为世人熟知的科斯定理并非科斯本意,并对照于现实法律。第三节将讨论法律人对于损害相互性观念的质疑,此可从法律概念与法律价值的区分来解决。第四节将探讨在科斯的公司架构下,作为市场替代的法律是无恣意性的。第五节将从科斯的比较制度观点下,检讨现行法律经济学发展的一些缺失。第六节是结论。
一、市场交易与损害权利化
科斯的经济学往往被人化约为无成本交易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但这违反了科斯本意。此定理是由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提出的,其说:“在完全竞争下,私人与社会成本等同了。”〔4〕R.H.Coase,supra note 1,p.14.换言之,在无交易成本下,资源的分配会是最有效率或社会产值会是最大,是为科斯定理。但史蒂格勒又说:“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一如无摩擦力的物理世界,非常奇怪。在此,独占者经由补偿,其行为不会不同于众多竞争者,而且保险公司也不会存在。”〔5〕R.H.Coase,supra note 1,p.14.张五常甚至说,在无交易成本下,“即使不存在私有财产权的假设,科斯定理一样成立。”〔6〕R.H.Coase,supra note 1,pp.14-15.科斯本人也说,“在交易不需花任何成本下,此意味了加速交易不会增加任何成本,则瞬间就是永恒了。”〔7〕R.H.Coase,supra note 1,p.15.科斯一再陈言,无交易成本的“科斯世界”不是他(科斯)的世界,世人多所分心在此,是浪费了。真实经验才是科斯关心所在!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是要证明福利经济学如下一命题是错的:造成他人损害,使得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政府必须介入强制改正之。科斯证明了不管是在市场机制下还是在法律直接界定权利下,该命题不一定为真。首先,在市场机制下(此意味了法律界权了),损害,或者更精确地说,资源使用之冲突,对于冲突双方都是成本——只是一个是直接成本,另一个是机会成本──因此也无所谓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8〕R.H.Coase,supra note 1,p.112.其说“It is one of the beauties of a smoothly operating pricing system that,as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the fall in the value of production due to the harmful effect would be a cost for both parties.”以该文第三、四节的农人与牧人之例,科斯证明了:如果是牧人须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其会将赔偿支出视为成本,但即便牧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农人可经收买牧人多养牛的权利以减少其农作损害,则此笔收买金额对于牧人而言,也是成本,机会成本是也;可见不管牧人负责任与否,其养牛的成本都是一样的,则所谓私人与社会成本之分离,即是无稽之谈。次之,在市场交易困难之时,科斯在该文第七节引用了判决及立法,显示了法律直接将权利界定给了最高价值者,损害根本未受赔偿,但其私人与社会成本也未分离。
森穆荪(Paul Samuelson)说,由于市场交易盈余的分配在数学上是未定的,其质疑市场交易之存在。科斯回应道,经验上未达成交易的比例是低的。〔9〕R.H.Coase,supra note 1,p.161.科斯说:
替代物品的竞争,一般而言的确大大缩小了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期待的差距,但买方或卖方无视于交易成功的获利而玉石俱焚,则是很少的。现实里,原料、机器、土地及房产,买卖频繁,甚至教授也找到了秘书……那些无法与人达成协议的人,将发现其既不买也不卖,从而也多无收入。这些特质不利于存活,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当然我是如此假定),正常人不是如此,而愿意“化异求同”(split the difference)。〔10〕R.H.Coase,supra note 1,p.162.
市场既有如此之功能,但有其局限条件。科斯在先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即指出:权利确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奏。〔11〕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R.H.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2 J.L&Econ.1,27(1959).换言之,权利之确定减少了交易成本,因此促成了市场交易。甚多论者将科斯定理理解为:无交易成本下,不管权利界定给何人,其最终结果并无不同,而且社会产值都是最大。如此一来,仅见交易而不见交易基础,从而漠视了使权利得以确定的法律。柯华庆认为权利确定的法律是意识形态,指责阐释此最给力的张五常“借‘定理’吓唬外行”,并评以不客观、不科学,甚至底气不足。〔12〕柯华庆:“科斯命题的博弈特征与法律实效主义”,载黄少安、史晋川主编:《中国法经济学研究(2003-2007)》,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631。他显然未读过《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不知此市场交易前奏说法是科斯自己说的,张五常将之发挥而已。〔13〕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45。观察角度之翻转,使得法律变得重要了。只看到不管权利何属,其结果并无不同,令法律判断有如丟铜板射幸之轻易——因为自有市场会去交易调整。另一个角度,权利确定系市场交易之前奏的说法,则使得法律安定性成为核心,法学方法从而大有功用矣!
法史学家辛普森(A.W.Brian Simpson)将市场交易往前推至纷争和解阶段,其以科斯援引的Sturges v.Bridgmen案为例,从历史档案发掘了纷争双方为何未能达成和解而诉讼。〔14〕A.W.Brian Simpson,Coase v.Pigou Reexamined,25 J.Legal Stud.53,85-87(1996).但问题是,科斯所强调的,正是权利必须界定了才有市场交易,因此权利未界定前,纷争若无法和解,即不令人意外。〔15〕在现实上,即使权利未经法律界定,很多纷争还是未经诉讼而和解了。See Yoram 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96-98(2nd ed.,1997).至于诉讼所造成的后遗症,此即在权利的界定判决后,双方情绪上仍无法平复,从而不去交易,的确是有可能,但其影响应不大。一者,此仅限于第一次同类纷争,因为往后纷争已有前例可循,无须再为权利何属而争执,则情绪也无了。〔16〕如果权利是由立法而非法院界定(参见下段文),则无诉讼,因此也无情绪。二者,诚如科斯说的,如果是营业厂商,其基于营利目的,这些情绪会降至最低。〔17〕R.H.Coase,Law and Economics and A.W.Brian Simpson,25 J.Legal Stud.103,109(1996).
科斯认为,经济学家将生产因素限于实体数量(physical unit),是其不见“损害”可以在市场交易的另一原因。〔18〕R.H.Coase,supra note 1,p.163.相对于此,律师的交易考量往往是非实体的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19〕R.H.Coase,supra note 1,p.11.的确,现实法律一直是将“损害”权利化了,使之可在市场交易。例如台湾《民法》第851条规定:“称不动产役权者,谓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这些役权是定限物权,因此限制了供役地所有权的行使,但同时也增加了需役地(所有权)的价值,则在土地买卖时,买卖双方一定不会只考量到实体交易的数量,例如坐落地点及面积,而必然还要考量其上是否有定限物权,例如不动产役权,这是非实体的,是权利扩张或减缩构成的。对于供役地人而言,需役地权利人在其上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作其他便宜之用,的确是对其权利之减损,但这是在市场交易过的。火车经过引起农作物受损、邻人畜养之牛践踏农作物、邻人建楼遮蔽光线等损害,如果有不动产役权的设定,其私人与社会成本是不会分离的。外部损害(external harms)──这是我们可初步观测到的(来自受害者或政策者的主张)──并未导致外部性(externality),因为其已经是交易过了的结果。
有人质疑,法律界定权利会引起财富效果,因此即使经过市场交易,其最终的社会产值会是不同的。科斯以两个层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权利类型可得而知的情况下,例如养牛与农作冲突之例,农人与牧人可透过其给付地主的租金,来因应谁承担损害,而地主也可透过其取得土地的地价,来因应其地是否承担损害,因此权利界定不会造成不同的财富分配。此命题之成立,甚至适用于界定权利的法律之改变,因为牧人、农人以及地主可将此一法律变迁列入契约条款,调整租金与地价,则其财富分配仍是不变的。〔20〕R.H.Coase,supra note 1,p.171-173.在权利类型不可得而知的情况下,上述租金与地价的确无法以契约调整,但此财富分配之可能不同,会因此影响了“损害”的需求?科斯说,经验上,除了废奴此类重大法律变迁外,其影响应是不大的。〔21〕R.H.Coase,supra note 1,p.173-174.的确,农人或牧人谁承担了损害,影响了世人对于牛肉及农作的需求?医生或糕饼店谁承担了损害,影响了世人对于医疗及糕饼的需求?答案应是否定的。有人因此误解了科斯,认定其主张法律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无关。〔22〕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页104、119。此是无视于科斯指出,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而此非法治莫办,更何况科斯在此强调的是,个别权利界定的法律而非法律整体(例如从共产体制转至私产体制),其单独多不足以影响相关资源的需求,则岂能以偏概全!
二、损害相互性与法律概念
以庇古为范式的经济学,以定理式或推定(prima facie)认为造成损害的人应负责任,〔23〕R.H.Coase,supra note 1,p.95.但科斯说:(物理行动上)造成损害的人,不一定要负赔偿、缴税或禁止活动等法律责任,因为这是两个不相容活动之冲突,若是造成损害的活动价值高,则造成损害之人并无理由要负不法责任。〔24〕R.H.Coase,supra note 1,p.96.科斯此一损害及因果关系相对化的说法,引来习于个案法律适用之法律人的质疑。辛普森即说,纷争当事人及其律师所争执的是,依照现有的财产权及因果关系法律,权利应归己方,根本不主张经济效果之考量,而法院也是如此,因此科斯的说法在法律是无根的。〔25〕A.W.Brian Simpson,Coase v.Pigou Reexamined,25 J.Legal Stud.53,60,88(1996).但诚如科斯所说:“法官必须决定赔偿责任是否成立,但经济学家不应迷糊而看不到所涉及经济问题的本质。”〔26〕R.H.Coase,supra note 1,p.112.辛普森混淆了法律系统结构与个案(严格)适用法律。〔27〕在英美普通法的讨论中,“效率”作为法律价值,已不是问题。See e.g.Ian Ayres,Valuing Modern Contract Scholarship,112 Yale L.J.881(2003);Richard Crasswell,In That Case,What Is the Question?Economics and the Demands of Contract Theory,112 Yale L.J.903(2003).
为了减少思维负担,法律概念被创设了,但也诱引其自价值剥离。〔28〕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北植根法学出版2002年版,页91、99。在适用法律的一般个案解决,法律三段论法的函摄即可处理,法律概念无须去处理內部价值问题,从而辛普森的个案因果关系或财产权之理解,当然不同于科斯以整体法律体系为评价之理解。黄茂荣说:“鉴于外在体系并不建立在法的內在价值(规范意旨)上,也不以探求法之意旨上的关连为其职志,因此外在体系并不尽符法律科学的要求。”〔29〕同上注,页607。其又说:“利用法律解释及补充以发现或认识应适用之法律,可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看法,在此情形,到底以哪一个看法为当,必须从功能的标准判断,以符合规范经济的要求,用最低的成本,最有效率的达到规范目的。”〔30〕同上注,页637。即以台湾《民法》为例。《民法》第184条规定了因果关系而《民法》第765条也规定了物权內容,因此有法律函摄的要求,但这无碍于损害相互性在整体民法的理解。《民法》第148条第一项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就是表明了权利之行使,往往附带了对他人的损害,而他人只能容忍了。这是损害相互性。《民法》第184条采取过失而非严格赔偿责任,这也是损害相互性。《民法》第793条有关气响等侵入禁止的侵入轻微、地形或习惯例外等,〔31〕该条文如下:“土地所有人于他人之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气、臭气、烟气、热气、灰屑、喧嚣、振动及其他与此相类者侵入时,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当者,不在此限。”也是损害相互性。这些法律规定显示了:造成损害之人无须负法律责任。至于损害权利化而可在市场交易,例如不动产役权,〔32〕参见上一节文。则更是损害相互性的另一表征。
财产权之保护,绝对是法律系统的重要功能,此可从民法、行政法、刑法以及宪法的规定看出。又法律对于财产权的保护,的确是以划分疆界为始,因此侵犯疆界就构成了损害,则依法言法,为何有相对性?症结在于一方面疆界可能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在疆界未清楚前,所谓损害只能是客观可观测到但不具规范意义的现象。因此虽然在纯粹法律逻辑上,这些法律保护的对象,必然是已经确定归属的财产权──行动人或受害人择一──但为何应如是分配,此即法律如何定分,依法言法是无法回答的,因此在此“前法律”(或法律漏洞)阶段,损害归属必然是相对未定的,否则也不会有权利未定。科斯损害相互性之提法,最初是用于频谱分配,〔33〕R.H.Coase,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2 J L.&Econ.(1959).此即财产权的归属尚未确定,则考量损害相互性,毋宁是个好标准,因为其体现了平等原则。至于在财产权为法律确定后,个案的造成损害,已无任何损害相互性可言,行为人必须负故意侵权的不法责任!〔34〕参见简资修:“故意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兼评Landes&Posner模型”,《中研院法学期刊》2007年第1期,页191-212。问题是,世事多变化,法律不可能是封闭的,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等事由,还是阻却了不法责任──损害相互性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是一直存在的。
损害相互性是资源竞争使用的本质,其规范的意涵是中立的。因此所谓帕雷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与可能帕雷托效率(potential Pareto efficiency)或凯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在规范上,由于条件不清,并无优劣之问题。当损害来自已经界定的权利,帕雷托效率的要求是必要的;当损害并非来自已经界定的权利,则满足凯尔多/希克斯效率即可。换言之,此二效率并无指导法律的功能,因为其决定于法律是否界定了权利与否。反之,科斯的法律建议是可操作及验证的:当市场交易成本低,界定权利以利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成本高,直接界定权利给最高价值者。虽然市场交易成本的探求的确也要成本,往往也可能甚高,以至于法律无从判断或判断错误,但毕竟是有验证可能的。
三、作为市场之替代的法律无恣意性
基于损害相互性,除了以界定权利在市场交易外,科斯又说:当高市场交易成本阻碍了权利重组,法院应考量及其裁判即决定了经济后果,在不太危及法的安定性下,将权利直接判给可创造社会产值最大的一方。〔35〕R.H.Coase,supra note 1,p.119.原文如下:“In such cases,the courts directly influence economic activity.It would therefore seem desirable that the courts should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ir decisions and should,insofar as this possible without creating too much uncertainty about the legal position itself,take these consequences into account when making their decisions.Even when it is possible to change the legal delimitation of rights through market transactions,it is obviously desirable to reduce the need for such transactions and thus reduce the employment of resources in carrying them out.”换言之,科斯主张以法律直接取代市场交易,令最大社会产值一步到位。
凌斌认为科斯忽略了其所谓的法律“界权成本”,令法院过度介入了市场。〔36〕凌斌,见前注〔22〕,页104-121。但这曲解了科斯的原意以及其整体论述。首先,法律的安定性考量已经排除了很多法院的恣意。次之,在脉络上,科斯此一说法是针对经济学家仅知造成损害即要负责的偏见而来,其证据是现实的(英美)法院在有些裁判中的确考量了经济后果,将权利判给了造成损害的一方而非受害的一方。不过,最重要的是,从科斯的公司理论来看,法院应如何界定权利,绝对是受到市场以及其他界权制度的制约,例如立法或行政。
科斯是知道法之所以为法的道理,因此如果既有法律已经明确了权利,他是不主张法院应该再去考量其经济后果,这是其所言法律安定性的意义。当然在法律安定性的具体操作上,总是有模棱两可之时,权利可确定也可不确定,若是如此,法官岂仅是享有界权的权力而已,而是更往前的“后设界权”判断余地。但诚如科斯一再陈言的,他是经济学家,其注重的是“给定法律”下的经济后果,至于法律安定性的线应划在何处,已非其研究范围。换言之,如果法院认定系争权利尚未确定,则其在界定权利时,考量其经济后果,毋宁是可欲的,毕竟求得最大社会产值在法律上是可欲的,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
科斯是一个经验论者,其在《社会成本问题》的第五节与第七节引用法院判决以及法学论著,其用意是以经验论据来证明经济学家的“外部性”论证系空想而无事实支持。当然不是所有的法院判决都是结果考量,但有些的确是的。例如科斯引用了Prosser on Torts:“只有经过利益与损害的比较后所认定的不合理的行为,才属扰邻。”〔37〕R.H.Coase,supra note 1,p.120.原文如下:“It is only when his conduct is unreasonable,in the light of its utility and the harm which results,that it becomes a nuisance.”其引用的英格兰法院的一个判决说:“我不知道普通法有规定说,建物妨碍了他人的视野,就是扰邻。如果法律真有此规定的话,伟大的市镇即不可能有,而且我还必须对所有的新建物签发禁建令。”〔38〕R.H.Coase,supra note 1,p.121.原文如下:“I know no general rule of common law which…says,that building so as to stop another's prospect is a nuisance.Was that the case,there could be no great towns;and I must grant injunctions to all the new buildings in the town.”科斯指出法院在具体适用例如合理(reasonable)或一般使用(common or ordinary)等标准时,虽未明示但大多是潜意识到其经济后果的。〔39〕R.H.Coase,supra note 1,pp.123-124.科斯引用了一个判决,其中法官甚至将损害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了——不是被告造成了损害而是原告造成了自己的损害!在Bryant v.Lefever一案,法官说:“原告在这么靠近被告墙壁的烟囱生火,以至于烟灰无法排放而灌回自己屋內,这是咎由自取。”〔40〕R.H.Coase,supra note 1,p.109.原文如下:“It is the plaintiff who causes the nuisance by lighting a coal fire in a place the chimney of which is placed so near the defendants'wall,that the smoke does not escape,but comes into the house.”科斯引用这些判决与法学论点无非是要说明:法院是有作经济结果考量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的。
认为科斯以“法律/市场”取代“政府/市场”的框架是误解。科斯在《公司的本质》一文中指出,由于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公司以由上而下的管理避免了此一成本,系其存在的理由。他又说,公司的规模是受限于其(边际)管理成本不得高于市场交易成本或另一公司的管理成本。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六节,科斯称政府是一个超级公司(super firm),因为政府的行政强制(包括管制与公课等)一如私公司,其具由上而下的管理关系,但更强而有力,其目的在于因应市场交易成本取代市场,是勿庸置言了。但科斯指出,在实证上,政府强制往往被滥用(超过了政府的最适规模),〔41〕R.H.Coase,supra note 1,pp.114-119.而经济学家以“外部性”理论推波助澜了。必须再强调的是,科斯从来不排除政府强制是一个取代市场的选项。此外,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七节的后半部,〔42〕R.H.Coase,supra note 1,pp.126-133.科斯指出立法取代了市场,而且也取代了法院。如同评价政府,科斯也指出立法的可能问题,例如过度保护了造成损害的一方。〔43〕R.H.Coase,supra note 1,p.133.
科斯批评了政府与立法,是否就独厚了法院?非也,因为从科斯的公司理论来看,法院既然是市场的取代,其即必须受到制度竞争的约束。换言之,法院的(边际)“界权成本”不得高于其因此取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但科斯似又未深论之,何也?首先,从研究旨趣来看,科斯既然是以庇古传统的经济学为批判对象,则其对于以庇古税为典型的政府强制多加著墨,毋宁是必然的。他说,其之所以引用法官的话,不是在赞许法官,而是在显示经济学家的无知。〔44〕R.H.Coase,Law and Economics in Chicago,36 J.L.&Econ.239,251(1993).次之,这是司法的本质,相对于政府或立法,法院拒绝介入(审判)余地是少多了。从经济分析来看,若无权利的界定,即无市场的交易,则法院即使判错了,也总比悬之不决任令双方武器竞赛强多了。三者,科斯其实也认为法院可能会犯错,如果其采取了庇古式的经济分析。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八节,〔45〕R.H.Coase,supra note 1,pp.138-141.科斯举例说,从理想的最大社会产值观点言,铁路经营者应只开一列车,但现实可能是,若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其会开两列车,但若其负损害赔偿,其则会停驶,虽然两者都不是最大的社会产值,但前者的产值高于后者,则法院若判铁路经营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即是犯错了。另外一个例子是,科斯不认为法院可以完满执行“与有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的机制,因此有损害无赔偿仍有必要,如此才可以令受损害人采取比较低成本的避免损害的措施。〔46〕R.H.Coase,supra note 1,pp.177-178.
科斯基于其公司理论,一定是会承认所谓的法律界权成本,但其又自我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学家而非法律经济学家,因此其不会去实质探讨个别的界权成本。即便如此,此并不意味科斯对于法律毫无所知,因此即以经济分析之名任意操纵法律。本节前述的法律安定性作为法院直接取代市场的前提条件,即是一例。上段文提及的铁路经营者开多少列车,又是一例。按铁路经营者到底是开一列车、两列车或停驶,是取决于法院(或法律)是否有足够能力鉴别出开第一列车是好的,但第二列车就是不好的,而科斯在此是认定(真实上也应是如此)法院是做不到的,法院因此只能在有责任与无责任择中其一,则既然停驶的社会损失显然高于开两列车,法院两害取其轻,就应判铁路经营者无须负责任。〔47〕George Priest即认为,当时芝加哥大学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接受损害无须补偿的说法,即是未能考量此是多个不完满制度间的比较,而非仅仅是一个不完满制度的理想改正。George Priest,The Rise of Law and Economics:A Memoir of the Early Years,in Charles K.Rowley and Fransesco Parisi ed.,The Origins of Law and Economics:Essays by the Founding Fathers 350,356-357(2005).科斯是知道法律的系统性的,他强调说:“当经济学家比较替代的社会安排时,正确的程序是比较这些安排所产生的全部社会产出……问题是设计出实用的安排,其可改进系统內的一部分而不会在其他部分造成更严重的损害。”〔48〕R.H.Coase,supra note 1,p.142.他举例说,在半夜无人车的交叉路口,驾驶人因为红灯而停了下来,显然社会产值减少了,但因此就认为废掉闯红灯须罚款的法律是在增加社会产值,则是错了。
布肯南(James M.Buchanan)另从宪政经济学观点质疑科斯的此一法律替代主张。布肯南认为,客观的社会产值并非法律(或经济学)追求的目标,因为法律是来自人们同意此一形式,因此法律一旦界定了权利,其交易是否因成本过高以至于失败,从而导致所谓社会产值无法最大,并非法律(或经济学)应与闻之事。〔49〕James M.Buchanan,Rights,Efficiency,and Exchange:The Irrelevance of Transaction Cost (1984),in Steven G.Medema ed.,The Legacy of R.H.Coase in Economic Analysis II 175-190(1995).如同科斯,布肯南认为法律在经济分析中是不可免的,甚至更有过之。布肯南几乎将经济学等同了法律的形成过程。布肯南完全以同意为基础的合法性来判定效率与否,此诚严肃看待了法律,但不够现实,至少在其质疑科斯此一部分是如此。法律安定性是科斯主张的前提,此应包括了法院或立法应受宪法原则的拘束,例如权力分立及基本人权。但这些原则应不致完全排除了法院“造法”或立法裁量,因此判决或立法考量到市场的交易成本,决定避开市场直接界定权利,即非不合法。科斯在比较英国与美国法制时,即指出后者有前者所无的公益征收补偿之宪法限制,〔50〕R.H.Coase,supra note 1,p.128.但此不妨害后者的法院也考量经济后果。以社会产值及市场交易成本等这些客观因素为法律制订或适用考量,的确是以结果取代了过程,但这仍是在法律程序下为之的。有些法律系统可能过度限制了法律取代市场的功能,有些法律系统则可能过度促进了此功能,但此无损于科斯所主张的法律/市场取代功能,一如有些公司必然解组或失败消失,而无损于公司的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之本质。
强世功所举陕北石油产权归属之例,可说明宪政法治下,科斯此一制度间竞争仍为之展开。强世功质疑国家以宪法与资源矿产法垄断了石油等矿产,造成了地方的虚与委蛇、环境破坏以及民生凋敝,因此他不无嘲讽地说,“科斯对自由主义社会秩序(充满)幻想”,不够诚实。〔51〕强世功:“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收于许章润编:《法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样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3-58。但这是由于他只看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前半段(此即科斯定理),而未看到其后半段一步到位的功能,而此是受到竞争拘束的。当国家垄断若是如此不堪,此即意味了社会最大产值并非最大,则从科斯市场/公司竞争架构来看,国家已经超过其最适规模,从而矿权必须回归私人或另外公司(地方政府)!科斯相对于布肯南,其研究取向还是比较经验客观的。〔52〕关于主观与客观之区分,参见James M.Buchanan,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Buchanan v.6:Cost and Choice: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1999)。
另一法律经济分析名家卡勒布列西(Guido Calabresi)也从科斯所言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推导出:法律不应仅是考量社会产值最大,而应包括分配问题(distribution)。其认为,交易成本之存在,法律若有不足,也是此局限下之结果,因此任何改进现状的法律,并非无分配问题的预设帕雷托疆界(Pareto frontier)之到达,而是该疆界的外扩或其上的移动,必然涉及了有赢家有输家的分配问题。〔53〕Guido Calabresi,The Pointlessness of Pareto:Carrying Coase Further,100 Yale L.J.1211-1237 (1991).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结论,引发奈特(Frank Knight)如下一段话:福利经济学最后必然是美学与伦理的探索。〔54〕R.H.Coase,supra note 1,p.154.科斯显然是不反对法律可考量非社会产值最大的因素。重点是,法律制度之分化与分工,有些法律必然是以追求社会产值最大为目的,例如以平等主体交易为原则的私法(自治),则科斯的说法依然是成立的。
四、法律的规范系统性与经济分析
科斯虽然公认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他本人对于经济学之用于别之学科,即便是法学,也是兴趣缺乏,而且持怀疑的态度。除了他认为研究对象而非研究方法是划分学科的标准外,更深层的理由恐怕是,现今经济学过于注重数学演算以及计量分析,以至于忽视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导致其所谓的黑板经济学,因此无助于世事之了解。〔55〕科斯此一以了解及经验为中心的经济学方法论与英国传统之关系,参见Zerbe Jr.,Richard O.and Steven G.Medema,R.H.Coase,the British Tradition,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Method,in Steven G.Medema ed.,Coasean Economics: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9-238(1998)。推动法律经济分析最力的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即批判说,科斯自绝于数理方法,〔56〕科斯认为波斯纳说其反数学模型与统计分析是几近于捏造,参见Ronald H.Coase,Coase on Posner on Coase,149 J.Institutional&Theoretical Econ.96-98(1993)。使其影响受限了,而且也仅能适用至如他及史密斯此等孤独的天才。〔57〕Richard A.Posner,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in Overcoming Law 406-425(1995)。波斯纳最近软化了其批判科斯的立场,参见其Keynes and Coase,J.L&Economics(forthcoming),http://iep.gmu.edu/paper/keynes-and-coase。但此个人化了科斯此一具普遍性的坚持。科斯论证了,无交易成本之考量,无以了解公司;无交易成本之考量,无以了解法律。波斯纳认为法律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其几视法学理论或法律的规范性与系统性为无物。〔58〕See Richard A.Posner,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eets Law and Economics,in Overcoming Law 426-443(1995).但科斯说,经济分析若如研究血液循环而无身体,可乎?〔59〕Ronald H.Coase,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40 J.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29,230(1984).布肯南说“好经济学,坏法律”,〔60〕James M.Buchanan,Good Economics-Bad Law,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Buchanan v.18: Federalism,Liberty,and the Law 327-337(2001).更是直指要害。
近年物权外部性问题之发生,即导自法律规范性之漠视。法律经济分析者往往将法律视为隐而不显的价格(implicit price),但多强调其诱因层面,因此可任意操控,〔61〕Robert Cooter&Thomas Ulen如下说道:“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惩罚有如价格。人们对于变贵的物品的反应,是减少其消费,则人们对于法律惩罚变重的反应,也应推定其会减少从事违法的活动。”参见Robert Cooter&Thomas Ulen,Law and Economics 3(4th ed.,2004)。而忽略了其系交易形成的产物,因此应受其拘束,此为法律核心的规范性。按物权之所以存在,在于其促进了交易,因此是內部化了,而非如庇古论者所说的,其创造了外部性,因此须要法律改正之。米瑞尔和史密斯(Thomas W.Merrill&Henry E.Smith)在《财产法的最适标准化——物权法定原则》一文,〔62〕Thomas W.Merrill and Henry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110 Yale L.J.1-70(2000),in Robert Cooter and Francesco Parisi ed.,Recent Developments in Law and Economics(I)214-283(2009).即陷入此內外颠倒之中。〔63〕本文以下对该文的批判,参见简资修:“物权外部性问题”,《中研院法学期刊》2011年第8期,页227-257。
米瑞尔和史密斯认为,由于物权的对世性,其创设对于第三人以及欲为交易但不欲负担此类物权的人(以下简称第二类交易人),即造成资讯外部性;其说法是,第三人必须花成本去取得此资讯,以避免侵害此物权,而第二类交易人也必须花费成本去取得此资讯,以避免交易到有此物权负担之物;其开出的药方是,作为庇古税的物权法定主义。但事实是,除了初始的所有权分配外,往后的所有权移转或其上的负担或限制物权之创设,根本不会增加第三人或第二类交易人的讯息成本。就第三人而言,其只要知道此物非我所有,无须知道究竟为何人所有,再多的移转或设定,根本与其无关,何来资讯外部性;就第二类交易人而言,其只要知道其交易之物上的所有权或设定为何,非其交易物上之再多移转或设定,也与其无关,因此也无资讯外部性。至于初始的所有权分配,的确需要公示制度避免侵权与促进交易,公示制度成本因此限制了物权发展,但此是众人(交易)內部化之结果,而非引入立法限制物权的外部性基础,否则就因果颠倒了。
从事后观点言,物权创设人、第二类交易人与第三人间的确是可区分的;但从事前观点言,这三种人利益一致或根本无法区分。天下之物若非一人所有,则物权创设人与第三人是轮换的,其为何要损己不利人,制造资讯外部性?在无公示制度下,物权创设人与第二类交易人根本无法区分,何来资讯外部性?而一旦公示制度设立了,又使得此一区分可能了,但同时也使得此资讯外部性消失了。
此外,公示制度可由市场提供,也可由政府提供。有人将由政府提供之公示制度算入物权创设的外部性成本中,好似政府的财政支出都是无法无天的浪费或贪腐。但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因此其已內部化了,何来外部性?另外,物权创设也影响了其他法律,例如税法,有人也将之算入外部性成本中,如此又意味着任何法律的变动,都是不好的。没有一个法律系统是如此的,如果其存活至今的话。
实用主义(pragmatism)或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也不能毫无节制地被援用至法律规范系统性之漠视。的确,“实效主义的立足点是一切思想和制度都是服务于人,不关心本源只关心效果,对过去和现在的关注是为了未来”,〔64〕柯华庆,见前注〔12〕,页634。但注重法律规范系统性,正是关心了本源从而才有了效果。科斯说,在不太危及法安定性下,法院可以考量经济后果为权利界定之判决。科斯是不主张,法院可以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系统之拘束,而单以向前看的“效率”为判决基础,而且他应该坚决反对才是,毕竟其是比较制度分析最坚强的支持者。道理很简单,漠视了法律规范系统性,即意味着每一个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每案都必须从头做成本效益分析,一者,错误难免而且成本极高,二者,法律向前看也无所附丽了,因为每个判决都是独立判断,也就没有了拘束对象,则何来判决先例?
主张实用主义最力的波斯纳,在Indiana Harbor Belt案,〔65〕Indiana Harbor Belt Railroad Co.v.American Cyanamid Co.,916 F.2d 1174(7th Cir.1990).以巨细靡遗的分析,说明为何此案不应适用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而应适用过失责任(negligence),但这些说词是完全浪费了。〔66〕See David Rosenberg,The Judicial Posner on Negligence versus Strict Liability:Indiana Harbor Belt Railroad Co.v.American Cyanamid Co.,120 Harv.L.Rev.1210(2007).
波斯纳认为,侵权普通法是以过失责任为基准点,严格责任只有在过失责任无法吓阻过度损害活动时,才可启动。则在本案,丙烯酸泄漏原因的油槽车底部阀门破损,既然是有人为疏失,即可以过失责任来防制,无须诉诸严格责任。除此而外,波斯纳也认为,在本案,加诸被告严格责任并不会改变被告的活动层级。他说,由于美国铁路运输网路的特征是“集中转运”(hub and spoke),被告改道只有加长运输旅程,增加危险发生机率而已。他又说,公路运输比铁路运输更不安全,也非可取之道。他甚至想象,是否可生产较不具危险性的同功能产品以取代丙烯酸。对于何谓危险活动,他也大胆猜测,也许是那些居民不应住在铁路转运站附近,而不是铁路不应运输有毒化学物品,因为损害具相互性,不是单方可成的。总而言之,透过他非凡的法律外知识,波斯纳得出了:在本案,加诸被告严格责任并不能改变被告行为,也因此本案被告不应被课以严格责任。
若按照波斯纳上述的论证法,严格责任此一法律准则根本不可能存在,每一侵权案件都应以个案为成本效益分析,而此是有害于侵权法的整体效率的。其主张:严格责任只有在过失责任无法吓阻过度损害活动时才有适用余地。但这是立法理由,不是个案裁判时应依循的步骤。在本案,波斯纳认定丙烯酸本身不具强烈腐蚀性,因此其从油槽车底部阀门漏出,必然是有人为疏失,然后他又认定严格责任不足以改变被告的活动层级。此系完全从该个案的事实出发,并以若被告负损害赔偿责任,是否改变其行为,来决定被告是否负损害赔偿责任。在如此的推理程序中,所谓过失责任与严格责任之分,已是名存实亡,结果才是重要的。
何谓异常的危险活动,因此应适用严格责任,容或有模糊之处,但在个案,巨细靡遗将全部成本效益计算程序走完,则是矫枉过正了。暂时撇开本案也许应以契约而非侵权处理此一质疑,在本案,伊州环保局命令原告清理漏出的丙烯酸,并非基于原告的过失,而是其严格责任,则原告主张被告应负严格责任,也是理所当然,同一事件要相同处理!如果丙烯酸不是那么具毒性,伊州环保局也不会强制原告清理,虽然可能非其过失所导致。波斯纳不惜篇幅分析转运站附近居民是否自愿承担危险、是否应改道运输、是否应改为公路运输、以及是否应生产不具毒性的同功能代替品等,在伊州环保局强制命令而原告已花清理费用下,不管其对错,已不重要了。转运站附近居民不是自愿承担危险,否则伊州环保局的强制命令就师出无名。至于是否应改道运输、是否应改为公路运输、以及是否应生产代替品,勿庸法院越俎代庖,行为人负赔偿或清理责任,将使得这些成本內部化,最适选择自在其中矣!
当科斯说,若市场的交易成本高时,法律可取代市场直接将权利界定给最高价值者,其是在比较制度条件下说的。又此制度的比较,必须是真实而非理想制度的比较,而且是全部而非部分(边际)效应的比较。〔67〕R.H.Coase,supra note 1,pp.153-154.可叹的是,甚多的法律经济分析,重蹈了庇古的覆辙。〔68〕See e.g.,Robert Cooter and Thomas Ulen,Law and Economics 44-46(4th ed.2004);其批判见,Pierre Schlag,The Problem of Transaction Costs,62 S.Cal.L.Rev.1661-1700(1989);其建设性分析见,Neil K.Komesar,Imperfect Alternatives:Choosing Institutions in Law,Economics,and Public Policy(1994)。
五、结 论
对于法学而言,科斯是一位意外的访客。科斯一再陈言,其关心的对象是经济学,而且是限于经济制度研究的狭义经济学。他引用史蒂格勒的话说,只有经济学家才懂经济学家。〔69〕R.H.Coase,supra note 14,p.103.他极少批判法律,除非那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改进社会福利之手段。吊诡的是,相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有意入侵,科斯的意外卷入,反而才有法学意义。科斯经济学之所以对法学有吸引力,并非如法律思想史家杜克斯贝瑞(Neil Duxbury)说的:其给予了法学家避开严谨数理分析的借口;另一个理由是,在各出奇招恶性竞争的法学界中,科斯这种不随流行转的姿态,反而成为清流救赎。〔70〕Neil Duxbury,Ronald's Way,in Steven G.Medema ed.,Coasean Economics: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86-192(1998).诚如史瓦柏(Stewart Schwab)说的,政治正确也非科斯经济学在法学盛行的原因,而是其认真看待了法律。〔71〕Stewart Schwab,Coase Defends Coase:Why Lawyers Listen and Economists Do Not,87 Mich.L.Rev.1171(1989).科斯力主学科的划分最终在于研究对象之区分而非研究方法或理论,因为研究必有实体,则最终研究对象的本质即决定了研究方法或理论。法律的本质是界定权利,其一方面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另一方面却也可取代市场而直接分配资源。科斯的比较制度,比较的是系统全部的成本,而非仅是部分(边际)的成本。因此将比较视野从特定经济活动之产值大小转至全部法律系统的产值大小,则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法律,必须有安定性的控制,而作为市场取代的法律,则必须有防止恣意的程序控制,否则就是无法无天的自然状态。这是科斯经济学的市场/政府/法院/立法竞争之法学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