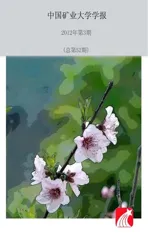颂父与渎父:自审亦他审
——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的双向理路
2012-01-21彭娟
彭 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颂父与渎父:自审亦他审
——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的双向理路
彭 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一方面基于父辈的忧思,肯定传统父性文明的正面价值,呈现颂父倾向;另一方面,以子辈的叛逆视角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在父子冲突中呈现渎父倾向。这种颂父与渎父并非二元对立的形态,而是父与子的对视、“他审”和“自审”的互审式结构形态,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
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颂父;渎父;自审;他审;互审
传统中国是父权社会,颂父一直是固有的文学传统,而明清以来,传统的家庭伦理在冲突和融合中开始了向近代的嬗变,新的文化思潮的涌动使知识阶层对传统的父权文化开始了一种新的审视。明清家族小说一方面基于父辈的忧思,对传统父性文明进行正面的思考,呈现颂父倾向;另一方面,以子辈的视角视父辈为专制与僵化的象征,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在父子冲突中呈现渎父倾向。这种颂父与渎父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自审与他审的交互作用下,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
一、父性光辉与颂父:回归儒教,对传统秩序合理性的确认
明清家族小说中的颂父母题是对父亲形象、父权文明的正面思考,面对家族文化的危机和传统价值的衰微,叙述者寄寓强烈的淑世之心。
李绿园于清乾隆年间创作长篇家族小说《歧路灯》,苦心塑造出堪称德行楷模、老成典型的父辈形象系列;清代满族作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塑造出具有醇儒品格的安氏家族的大家长安学海;清代嘉庆初年的《蜃楼志》描写了开明通达的广州十三洋行商总苏万魁。才子佳人小说如《麟儿报》等也展现出婚姻问题上父辈的民主姿态。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明清以来的传统文人面对迅速衰落的社会现实和颓败的家族命运,当他们难以在社会思潮和政治局势的突围中寻觅到一线生机之时,总会追忆父辈的力量、回顾父性的光辉,认同父权对于世道人心的保障与维系,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传统理念的父亲形象,构建起回归儒教后的美好幻境,从而获得安定和睦的心灵慰藉。这些小说往往在父亲出场之际细致描述其正直人格与出众人才。《歧路灯》中谭孝移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就暗含了为人处世标准:力求忠孝双全。他信奉程朱理学,诚意正心,家庭中不置姬妾,家居雍和;待人处事细密珍重。《儿女英雄传》中的安氏家族的大家长安如海亦是恪守忠孝节义的孝子忠臣,他出身于正黄旗汉军的世族家庭,家道中落、读书仕进的他熟谙孔孟,满腹经纶,为官也清正自守。《蜃楼志》中作为洋场商人的父亲有商人的精明,苏万魁“口齿便利、人才出众”,是在清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大行商。他虽未选择科场和官场作为人生价值的皈依,但在主观意识上仍保有传统印记。
家族小说情节发展往往是父辈的本心与社会现实发生龃龉后选择急流勇退:《歧路灯》中谭孝移上京候选令他见识了政治的黑暗,于是奉身而退,治家为务。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强化了治家的重要意义,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人人亲长而天下平”(《夏峰先生集》卷二《与杜君异》)。《儿女英雄传》中安如海因不屑与贪官为伍,被冤收监。在儿子奔救后,他弃官不仕,亲率全家去寻访曾搭救安骥的恩人十三妹,凸显英雄至性。这些父辈有着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对子女有着严明的教育理念。谭孝移专注于治家,以理学为育人良方,自己言传身教,“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希望儿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他的教育动机含有反荒废、反堕落的良苦用心,代表了传统文化指导人生的合理性因素。《儿女英雄传》中安如海自安家大团圆后着手指导儿子埋头读书,以成功名,又指派金凤、玉凤两媳掌管家计内务,支应门庭。在商人之家中,《蜃楼志》中精明务实的苏万魁一心想在经济上大展鸿图,却惨遭勒逼,家庭变故令他深愧平生,“利名都淡,仁义顿生”(第二回);为儿子择严师,为女儿择佳婿,结束洋行生意,不做官、不为商,“归乎农圃,以了此生。”
在家族兴衰的模式中小说构建出家族与子辈命运的变易与转化情节,并以家业复兴、笙歌重奏的结局表现出对于传统儒教的皈依。第一种模式,家族命运的变易是通过浪子回头来实现,对父辈是否定之后的肯定:《歧路灯》中谭孝移的早逝让谭绍闻失去管束,慈母的溺爱,歪师的影响,浮浪子弟的引诱令他沾染骄奢习气,放纵邪行、荡尽家财。小说强调了家风恢复、礼法重建对于家族传承的疗救意义。这主要有赖于子弟的“自立为贵”,承教继志。小说还多次强调家谱、家法祖训、祠堂主拓、修坟祭祖等实物及仪式,以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着礼法在家庭、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种模式是父慈子孝、承教继志的理想状态,子辈对父辈自觉认同、互相扶持[1]。这在《儿女英雄传》中有着生动的表现,安家父子都充分地实践了臣忠、父严、子孝、妻贤的伦理价值和传统美德,在安如海的影响下,父子、夫妻、妻妾、主奴之间各守本分,和睦相处。安骥金榜题名,官运享通,青云直上。安氏家业兴旺、书香不断。《蜃楼志》中的苏吉士出众的经商才能、机敏的头脑正是父亲开明教育、言传身教的结果。苏吉士最初沉湎于少年情欲,偷情追欢、疏懒逃学,后来经历了家庭变故,于是散财积福,进而继承父业,锐意经商,受命招抚义军,为国建功;又从军征讨摩剌,功成身退,安享天伦之乐。可以说,在维系千年的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危机的时刻,颂父母题是作家对于传统价值的坚守。
二、父性颓败与渎父: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和社会体制的衰败
渎父母题是明清家族小说区别于以往之处,小说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小说在父子冲突中宣告着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和父权维系的社会体制的衰败。
首先,明清家族小说往往以无父书写隐喻对父权的颠覆。在父权中心伦理体系中,父亲处于主位,子辈处于从位,父亲在子辈面前拥有绝对的的权威;父亲的缺席令子辈们摆脱束缚,呈现出财色、权力欲望的膨胀[2]。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陈经济,《红楼梦》中的薛蟠等,颠覆着既有的传统和秩序;《林兰香》中的勋臣子弟耿朗齐家无道,和势利酒肉朋友多所宴饮,与任香儿、平彩云二妾谑浪狎游,终致酒色过度,精神散耗,一病不起。《金瓶梅》中西门庆有着异于传统的亲族俱没的家庭格局,他父母早亡,兄弟俱无,以金钱来自由建构关系圈;他无亲可奉、无孝可行,摆脱了传统的孝悌重负。自始至终,西门庆为聚敛财富,伤天害理,恶德败行,颠覆着封建社会的全部伦理道德。这样的无父书写,从深层意蕴上暗示了子辈与传统父权文化的精神断裂,表现出商业文化下的人欲横流对于儒家父权文化的颠覆。《金瓶梅》以一系列无子嗣的绝后家庭,如李瓶儿前夫花子虚、蒋竹山家、潘金莲前夫武大及潘姥姥家、孟玉楼前夫杨某家以及陈经济家等,强化了子辈欲望的喧嚣,以及与传统家族文化的悖拗[3]。
其次,权威、完美的父亲形象被大量负面的父亲形象所代替。小说将父亲正面作用弱化,父亲性格、能力或道德的缺陷成为审视的重心。负面的父亲形象、父教的缺失,揭示了父权的颓败与尴尬[4]。《醒世姻缘传》中的地主乡绅晁家、狄家即是负面父亲形象的典型。晁思孝靠高价买官、搜刮民财发家,其忘恩负义、好色荒唐,更无国无君。他对儿子晁源欠缺管教、一意溺爱,更因上行下效,儿子无德无行。狄员外自己才学荒疏,对儿子百般溺爱,以致顽劣异常、性格乖张。《金瓶梅》中西门庆也扮演父亲的角色,但他纵欲乱伦、家反宅乱,令性饥渴的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以致女儿西门大姐自杀身亡;他与李瓶儿所生的官哥儿因妻妾争斗而死;吴月娘遗腹子孝哥儿是为赎他的罪而生。《红楼梦》对贾赦、贾敬、贾政、贾珍这些贵族父亲形象寄予了深刻审视,表现了整个上层社会的痼疾。贾赦不仅自己为老不尊、荒淫无度,还不顾父子伦常将自己染指过的丫鬟秋桐赏赐给儿子贾琏。贾敬一心烧丹炼汞,整日“和道士们胡羼”,对家事子女不管不问。贾政为人清肃,却庸碌古板,不通庶务,对宝玉的教育古板专断。贾珍不仅直接与儿媳秦可卿有染,而且与堂弟贾琏、儿子贾蓉一起,与尤氏姐妹鬼混。
再次,具有渎父倾向的明清家族小说将溺子不孝的亘古主题着意表现,父子冲突成为推动情节的动力,子辈已蜕变为恶棍流氓、纨绔子弟、甚至是叛逆者,宣告着家族传承的断裂和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拍案惊奇》卷13《赵六老舔犊丧残生,张知县诛枭成铁案》中的赵六老、卷35《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警世恒言》卷17《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过善、《型世言》卷15《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中的沈阆等等都是溺爱不明的父亲,导致儿子悖逆败家。成书清末的《跻春台》之《巧报应》中陈维明虐待父母致死,中年得子溺爱非常,结果夫妻双双饿死。《雅观楼》之钱是命对贪财的妻子言听计从,昧着良心私吞下盐商的十万两盐本,将盐商活活气死,后来在儿子被恶人引诱之时,一味以宿命态度放弃责任,只是躲在楼上忏悔己过。《初刻拍案惊奇》十三卷《赵六老舐犊丧残生》中赵家夫妻求神拜佛中年得子,对儿子百依百顺,为其读书娶妻而家道中落,儿子却无视爹娘,身无余物的赵六老为还债,只能夜盗儿子家财,却被儿子劈为两半。笔炼阁主人《八洞天》卷六《匿新丧逆子生逆儿》中晏敖灭弃先人却溺爱儿子,父子嗜赌家道中落,晏敖被子所误入监,奇郎自私恶毒到将父亲抛尸卖棺、惨遭狗食。尽管不少小说亦将溺子不孝纳入到果报框架,但对父子冲突的表现早已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红楼梦》中贾宝玉更是精神与思想上的叛逆,他背离传统的科举正途,把须眉男子作为“浊物”,对整个父权社会、上层社会的思想和道德都彻底厌弃。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富贵联姻的功利婚姻,传统的家族与社会机制,他统统动摇、怀疑和拒绝。这正是新兴的社会思潮对于僵化的体制和文明的反叛和颠覆,以贾宝玉和贾政为代表的父子冲突承载着新旧文化冲突的寓言。
三、自审亦他审:父子对视互审的深刻
在人的生命延续中,任何儿子又必然会是父亲,反之亦然。因此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体现出“他审”和“自审”的互审式结构形态,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这种结构形态很难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表述,是父与子的对视,是人生不同阶段的艺术沉思[5]。
那些具有颂父倾向的小说常常萦绕着父辈自审的情结,沉淀着理性反思。《歧路灯》中谭孝移承认:“论我的生平,原不敢做那歪邪的事,其实私情妄意,心里是尽有的。”对子辈传统教育的反思也贯穿在小说中:谭孝移出于对恶劣社会风气的忧惧,对儿子实施了“严防”策略,但“严正处多圆融处少”。他能控制儿子的行动,却无法控制儿子的心思,如此教育的儿子欠缺抵御诱惑、分辨是非的能力;他能意识到劣师的教育失策,但面对儿子的急转直下,没有任何良策;他能严格要求年幼的儿子,但是无法改造愚昧的妻子。而逆子的回头也是情感与理智的回归,对父辈的重新认同。当谭绍闻改过后,由儿子变为父亲的他常以自己平生遭遇训戒其子篑初,让他明晓事理,秉持孝心,用心读书,和自己一同承担起延续书香之家的重担。《蜃楼志》中苏万魁汲汲于利、精于算计,他靠特许垄断在洋行经纪中获利颇多;他对土地投资和高利贷投放更是精于盘剥:“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激起了民众的怨恨。小说中不仅令他自己深愧以往,领悟到“富不足恃,贫大可为”(五回),更借其子之口指出其“一生原来都受了银钱之累”。
在渎父倾向的小说中同样交织着对父辈的正面思考,包含逆子自审式的忏悔。尽管在明清短篇白话小说中逆子形象多流于特征化或符号化,缺乏完整细致的性格表现和内心的挣扎,但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往往凝聚着父子对视下情与理的冲突。《红楼梦》中兼容着贾政作为父亲的深情与宝玉作为逆子的忏悔,寄寓了对父辈复杂的家族记忆与审视。作为人父,贾政虽昏庸蛮横,但他人品端方,言行不敢有违纲常;在贾母面前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是标准孝子;在子侄面前,他不苟言笑,规训正路;他治家仍有法度,其子女如元春、探春,宝玉、贾兰,风度人品俱为贾氏别门所不及。脂砚斋对贾政的“大家严父风范”大加赞赏。贾政对宝玉严格管教,嘱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乏希望他人情练达、精通世务、光宗耀祖的良苦用心,毕竟这是当时贵族子弟的人生“正路”。刘敬圻先生说,贾政对宝玉经历了“嫌恶”、“绝望”和“妥协”三个阶段的变化和转折[6],往往于“不动情处十分运情”,令脂砚斋读至“几乎尖声哭出”。以往评者对贾政“痛打宝玉”的指责,多忽略了贾政复杂的内心感情波澜。《红楼梦》借贾宝玉形象在痛恨之余仍寄寓了个人的忏悔:忏悔自己“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纵给之时,饮甘膺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忏悔自己“风尘碌碌”、“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浸透着诚挚的情感和孝亲的情怀,表现了个人与家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在宗法社会里,‘父’对‘子’而言,绝不是‘养育’与‘依赖’这样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它可以说是‘根源’与
‘生长’这样的关系”[7]。所以,面对传统价值的衰微,明清家族小说的颂父母题不仅是天性情感与血缘伦理的温情依恋,更是对于传统价值的皈依与退守。然而,超强稳定的父权家族与社会体制的控制下,作为新变的社会关系和思维动力的主体——子辈的生命力被遏制,只有父亲在子辈的生活中隐退后,子辈才能轻装上阵;而一旦维系传统家族和社会正面价值的父亲完全被消解,缺少道德监控的子辈会因为精神滑坡而丧失道德指向和价值指归,陷入迷乱虚无甚至滑向罪恶和死亡的深渊,其负载的家族很容易走向败落[8]。
[1] 彭娟.《歧路灯》对家族命运的关注与对家族文学的开拓[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25.
[2] 楚爱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10.
[3] 霍现俊.对西门庆家族模式的文化审视[J].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51-52.
[4] 段江丽.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J].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08(秋之卷):67.
[5] 杨经建.论明清文学的叙事母题[J].杭州:浙江学刊.2006(5);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90-97.
[6] 刘敬圻.贾政与贾宝玉关系还原批评[J].北京:学习与探索.2005(2).
[7]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39.
[8] 转引自李安民.漂泊的大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44.
Ode or Blasphemy to Father Generation:Examination of Self and Others——the Mutual Direction to“Father on Trial”Motif in Saga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NG J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China)
There is an intensely observed history of“father on trial”motif in saga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n the one hand,i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father generation’s worry,and aims to affirm the positive values o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ivilization,which symbolizes the ode to father generation;on the other hand,i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son generation’s rebellion,and aims to let the father generation retreat and to weaken their positive roles,or even to uglify them,which leads to the blasphemy to the father generation in“generation gap conflict”.The motif of ode and blasphemy to father gene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binary opposition,but mutual examination between father generation and son generation,as well as between examinations of others and self-question.During the process of negative positiveness and positive negativeness,hopes and dreams are rebuilt.
saga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bservation of father generation;motif;ode to father generation,blasphemy to father generation,self-question,examination of others,mutual examination
I207.41
A
1009-105X(2012)03-0129-04
2012-03-0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院级课题: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研究(编号:XYS09527)
彭 娟(1980-),女,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