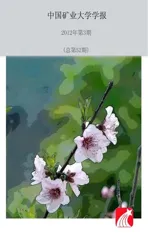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二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比较谈
2012-01-21高淮生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二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比较谈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既有相同之点,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将二者对曹雪芹的思想艺术成就、《红楼梦》本旨论、人物论、结构论、笔法论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研讨,应当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鉴赏,有助于读者对当代《红楼梦》评点的感受和评价。“周评”与“冯批”各自在《红楼梦》评点原则、政治历史说、思想艺术超前说等方面有着值得言说的话题内容和话题价值,比较研究其优劣得失,将有益于进一步探求《红楼梦》“四家评”的学术意义和鉴赏学价值。
《红楼梦》评点;四家评;周汝昌;冯其庸
当代《红楼梦》评点究竟有没有生命力?如果有的话究竟能否持久?这是研讨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这一学术话题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周策纵在谈及红学流派发展时说:“评点派自清末以来便已衰微,但其内容却提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新评点者像王蒙的尝试还是值得做,读者也许还会有不少,这要看将来如何发展。”[1]7-8周策纵的意见较为中肯,他所谈及的譬如“提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和“读者也许还会有不少”这两个方面,已经在“四家评”评本出版之后得到证实了。譬如“四家评”评本均已成为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评点者各自首肯的对《红楼梦》独特理解的代表著作,由于他们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较大,这些评本也就成为当代学人红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成为红学史研究尤其当代红学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笔者在研讨《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这一“学案性质”红学史研究课题过程中已将“四家评”评本作为必备参考文献,所撰述的论文已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连续刊发11篇(2010年第6期至2012年第5期),其中包括“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综论”、“冯其庸的红学研究综论”、“蔡义江的红学研究综论”、“王蒙的红学研究综论”等,已经受到红学领域学人的广泛关注。“四家评”评本已经拥有“不少的读者”,这可从其不断被重印出版方面印证,譬如《〈红楼梦〉王蒙评点》继漓江出版社出版刊行了10年之后,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笔者以为,“四家评”是有生命力的,评点这一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是有生命力的。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读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才能延续它的经典地位[2]。如果童庆炳的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仅就“四家评”评者作为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学者型作家以《红楼梦》评点的形式延续它的经典地位这一方面而言,其生命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那么,究竟“四家评”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如周策纵所说“将来如何发展”,这就涉及到两个方面:一则“评本”的价值,二则“读者”的兴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评本的价值(包括鉴赏价值、学术价值等)很高,并且读者总有阅读的兴趣,那么,“四家评”将不言而喻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将主要关注“评本”的价值这一方面的研讨,尝试将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的优劣得失作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探求《红楼梦》“四家评”的学术意义和鉴赏学价值。
一、评点原则
“辨伪存真”是周汝昌《红楼梦》“校评”的基本原则,如周汝昌在《红楼梦》80回回后评中说:“辨伪存真为本书主旨,一切取舍以此为根本,不容混杂而蒙蔽读者也。”[3]949这一“辨伪存真”基本原则也是与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总原则和根本目的相一致的,即还原曹雪芹原著的真貌,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信的本子,目的就在于避免充斥坊间的一百二十回程、高伪本的“误导读者”。这一“还原原著真貌”的终极目的即在于“恢复原本《红楼梦》真正的伟大”,而《红楼梦》的“伟大”则如周汝昌所说:“《红楼梦》是一部以重人、爱人、唯人为中心思想的书,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以小说的通俗形式,向最广大的人间众生说法……真正的意义也在于她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一个‘唯人’的高度。这与历代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归的。我所以才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以上就是我称《红楼梦》为‘文化小说’的主要道理。”[4]9周汝昌提出“还红学以学”的命题也是为他所倡导的“中华文化之学”张目,而“中华文化之学”的特质即体现为真、善、美或文、史、哲三者结合并相得益彰的品质,这才是红学的真学所在,也是“假学”或“无学”以及“非学”所难以具备的。可见,周汝昌的“辨伪存真”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并非不可取,即“辨”程、高“伪本”的歪曲中华文化精神之“伪”,而“存”曹雪芹《红楼梦》所倡导的中华文化精神之“真”。如周汝昌所说:“曹雪芹的真《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项特异瑰宝,是一部体真、感善、悼美的文史综合撰作的民族精神奇迹。我们为之校勘,正是要尽可能地保存她的真、善、美,对一切破坏、歪曲、改篡这种真善美的做法表示抗争。”[5]5-6当然,周汝昌用刻薄语言攻击高鹗以及后四十回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强烈的不满,这是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总原则和根本目的本身所难以避免的。可以说,即便周汝昌的“评点”文字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并不妨碍周汝昌“辨伪存真”这个原则的运用和发挥,便不会构成对其红学体系的威胁。
那么,周汝昌的“辨伪存真”原则有没有值得商榷之处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高鹗伪续”说至今还并非就是一桩铁案。譬如有学者认为:“可以看出,把《红楼梦》后40回认定为高鹗所续,证据还很不充分,故强作‘定论’。太过勉强。因此,此前把《红楼梦》一书标注为‘曹雪芹、高鹗合著’,实际上是对广大读者的一种误导,而且这种误导的影响至为深远。造成误导的原因,固然在于从以胡适为开端的红学界大家、权威所统驭的红学界(当然也包括俞平伯先生在内)制造出来的‘共识’,同时,一些红学家的迷信、盲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6]157如果这一认识是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新红学”集大成者的周汝昌不仅接受了高鹗“续书”说且将其发挥到极致的缘故了。胡文彬在《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中指出:“新红学考证派不论是其开山泰斗还是其集大成者,在《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上和所谓程伟元‘书商’说的论断,确是无法让人苟同和称善的。他们的错误论断和某些偏见被一些人无限放大,其影响之深之广,简直成了一种痼疾,达到一种难以‘医治’的程度。这种‘痼疾’不仅成了新红学考证派自身的悲哀,也是整个红学史上的一种悲哀。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红学研究者应该以一种自省的态度,把以往的史料、论断加以重新审察。”[7]8那么,作为读者的阅读鉴赏而言,也应该在阅读鉴赏过程中保持接受的开放圆通心理,以避免受到“错误论断”和“某些偏见”不必要的误导。最大的“误导”应属因全盘否定续书而引起的对120回本《红楼梦》价值评价的不够客观和准确的,进而影响读者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红楼梦》价值的“误导”。胡文彬不无痛切地说:“然而,胡适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追随者和集大成者,却把他的‘大胆假设’恶性放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遗症’——全面否定后40回,将程伟元‘定性’为同高鹗‘串通’一气与乾隆皇帝勾结以期‘削弱’曹雪芹的‘烦恼封建’主题思想。看着他们对120回本《红楼梦》那种‘痛心疾首’的‘革命’风采,人们真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7]12周汝昌的极端做法早已引起人们的不满,不满者这般质问:在这么多的“脂评”抄本中,有谁见过一部或一页曹雪芹或“脂砚斋”的原稿?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些辗转传抄的过录本都是最接近曹雪芹手稿的稿本?[6]152胡文彬指出:“至于红学界历年争论后40回究竟是否出自高鹗之手?这不属于阐释范畴,而是一个‘还原’的问题,需要拿证据来说话。一些人用‘大概’‘可能’‘我认为’,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只不过一场文字游戏。”[7]155如果胡文彬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形成一种“共识”,那么,人们不由得不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中“辨伪存真”这一原则的有效性发出质疑了——周汝昌“所辨之伪”和“所存之真”究竟是否符合曹雪芹创作之事实或《红楼梦》文本之事实?其实,这种质疑中还包涵对周汝昌自视其“辨伪存真”之言乃不刊之论的怀疑,这种质疑之举也与周汝昌那种常常葆有一种自视甚高的心理有关系。周汝昌自许“解味道人”而全享此能与曹雪芹相通的“独得之秘”,即对中华大文化的深刻解悟和对《红楼梦》文化真髓的精准体悟。如他所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开始,必须承认是由胡适先生开始的,别人都是一点读后感,没有学术实质内容,也没有体系可言。”[8]303这种“我占有真理”式的自我标榜不能不为他招来批评的意见,意气之争也在所难免,譬如因他“还红学以学”引起的大论争几乎可以取红学史上“钗黛优劣”这第一大公案而代之,可见其影响之大了。
冯其庸《红楼梦》“重校评批”的基本原则可从其“校评凡例”和“后记”中归纳:发明作者深意,决不空言误人;不妄语,不妄信,惟真是从。若用四个字概括,即“探赜从真”。冯其庸“重校评批”的基本原则应与周汝昌“辨伪存真”中的“存真”有相通之处,而与其“辨伪”似不合。之所以“不合”,是因为周汝昌是全盘彻底否定后40回续书的,称之为“伪续”,而冯其庸的态度则更加客观、圆通。他说:“全盘否定程本和全盘否定脂本只承认程本,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程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程本对脂本也确有删改,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实事求是地来分析它评价它。”[9]8也正因为如此平实的态度,才能避免招来质疑批评之声。冯其庸的“重校评批”在版本选择上兼顾程甲本,并对后四十回同样作了评批(包括正文和回后评)。冯其庸“重校评批”的这一做法是与“四家评”中的其他两家即蔡义江、王蒙是相同的(周汝昌则舍弃后四十回而不取),如蔡义江的“新评”后四十回有“题解”,而王蒙则直接选择的就是程甲本作为他的“评点”本。这种做法应如何评价呢?冯统一在《见识一个比较少见的版本》中说:“对于今人的《红楼梦》评点来说,当然应采用一百二十回的足本。”[10]1241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程甲本作为最早的印本,尽管已经与曹雪芹原作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比起程乙本则更接近曹雪芹原作,这已是“共识性”较多的结论。冯其庸“重校评批”的做法同样是易于形成“共识”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探赜从真”的“从真”与周汝昌的“存真”还是不同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在“存真”方面有相通之处呢?即担心“误导读者”是他们共同的心愿,其实也是当代“四家评”的共同心愿。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周汝昌“辨伪存真”的主观动机当然与冯其庸的“探赜从真”有着更多的一致之处。当然,由于周汝昌的“辨伪存真”已经比冯其庸的“探赜从真”走得更远,自不免因接受上的难以形成“共识”而为他招来质疑批评之声。譬如胥惠民就曾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对他的红学研究观点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其中包括他的“辨伪存真”的一系列做法。这一系列的文章包括《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11]、《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12]、《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13]、《不要把瞎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与周汝昌先生商榷》[14]、《〈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15]、《我为什么要批评周汝昌先生》[16]、《“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17]、《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18]、《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19]等,其中《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一文则将周汝昌“辨伪存真”的红学研究直接归之于“主观唯心论”,于是,他的所“辨”和所“存”竟都被看作“空言误人”了。
冯其庸则出于“探赜从真”的考量而对自己的《红楼梦》“重校评批”提出了看似常谈而实属不易的要求,即“疏解力求切实有据而又有新意,新评力求能发作者之隐微,能启读者之鉴赏而得其精义妙理。”[20]1要做到这些要求,当怀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的精神,冯其庸是具备这种“解蔽”自觉意识的。他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后记”中说:“《红楼梦》的评批工作,从我起意和作准备工作算起,已经十七八年了,从我正式开始评批至今,也已五年有余,从评批中我深感《红楼梦》的艰深,深感《红楼梦》文字之奥妙和多义,更深感一般的阅读《红楼梦》和要准备对《红楼梦》作评批的阅读《红楼梦》,真是大不一样。我在评批过程中,总要逐字逐句逐段的推敲,以至整回的反复品味,惟恐误解和失察,但要完全避免这两点是实在不容易的,我的评批,也只能算我个人的一点肤浅体悟而已。”[20]2036不幸的是,即便主观上“惟恐误解和失察”,客观上也不免出现“误解和失察”之处,这原本是难以避免的,但毕竟因为冯其庸是被称作“红学大师”的资深红学家,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为他引来“辩难”之声,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从冯其庸的被质疑批评的命运上说,他与周汝昌竟有如此相同的遭遇。“辩难”作者在《铜仁学院学报》连载了两篇“辩难”文字,即《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21]和《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续篇》,[22]归纳了二十五条不亚于几十处的所谓“失范”之评,其目的可参见作者该文的“摘要”:“资深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花数十年心血编纂一部长达160万字的巨著《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且被吹嘘为‘发前人所未发,为当代红学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可读性、欣赏性极强,且有极高收藏价值的关于《红楼梦》的传世佳本。’研读后始知此乃虚浮夸饰之词。仅从上卷前40回的评批中就凸现出包括常识性、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等方面的失范现象达14处之多。为减轻对广大读者和后学的贻误和不良影响,特逐条加以辩难匡正。”笔者以为,尽管“冯批”(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或“周评”(即《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引来了“辩难”“质疑”之声,但并不影响读者品鉴式阅读或研究者从“小说批评理论价值”和“文艺鉴赏价值”等方面展开评论。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冯批”和“周评”作为他们各自的“心力结晶”之作,其可取之处和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容忽视的是,因时代环境、阅读习惯、作者能力等各种原因,使当代《红楼梦》评点这一方式并不易获得好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冯其庸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难度,他说:“这个难,就是曹雪芹的思想高度和文字深度,这个难并不是光靠鼓劲干,靠不怕困难能够解决的。这个难,须要更高的思想和更高的识力,更丰富的学识。于此,我自觉深深的不足,也就无怪我会感到漫漫长途,举步维艰了。”[20]2039不过,冯其庸态度是值得“了解的同情”的,他说:“我自知钝根,积力太薄,所以所悟也浅,惟愿以后诸君子能完成此业。”[20]2039且看周汝昌如何陈述:“如果说这部三新本是我经历六十年努力的心力结晶,确是真实不虚,但并不等于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只是表明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报告和虔诚的献礼。”[3]1可见,周汝昌的并未“尽善尽美”说自比冯其庸的“所悟也浅”说自信得多,但同样值得“了解的同情”。
二、政治历史说
自从“新红学”以来,从政治历史的视角解读和阐释《红楼梦》一直都是居于红学研究主导地位的,“新红学”从胡适、俞平伯直到周汝昌对“自传说”的提出和诠释,尤其周汝昌更是“曹贾互证”而精心构筑了一个看似精密的宏富的红学体系。众所周知,“新红学”以来的“考证派”一直主导红学近一百年,这是不刊的事实,而“考证派”的主要兴趣是从历史(包括政治)的视角解读《红楼梦》,或者说主要精力用在“知人论世”上,即作者家世和时代背景。再以红学大家冯其庸为例来看,他的主要成果和影响是在考证方面,如他说:“我深深感到要研究《红楼梦》,家世研究和抄本研究是两大前提。不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遭遇,就无法理解他的这部书;不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不确切掌握曹雪芹的文字,就无法对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作出切实的评价。”[9]8-9其实,冯其庸的这一看法也可以看作“考证派”的基本“共识”。从这一基本“共识”的层面上来看,周汝昌和冯其庸是同大于异的。那么,他们的相异之处体现在哪里呢?
且看周汝昌在《红楼梦》80回回后评中如何说:“甄费贾化,真去假来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大纲领,此纲领又与史湘云之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密不可分。作者曹雪芹所经历之时代正值日月两皇帝同时并存,真者被指为假,假者却冒为真之际。作者一生经历皆在这一特定怪异的政治环境中,是故方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慨叹。是故读者欲解作者难言之味,必须从考知这一历史上少见的真假两皇帝并存的特异局面入手,若能破读此义,则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了。”[3]950这一段评点要点可以这样归纳:《红楼梦》所“隐”去的“真”事就是皇帝皇子的谋权斗争,是作者曹雪芹所经历的时代背景,《红楼梦》就是隐喻地写出曹家所经历的政治和历史事实。为什么说“若能破读此义”则一切“迎刃而解”了呢?且举例说明:1.评“香菱学诗”《咏月》:“是知香菱咏月者明写天象,实寓人间,有一明月全可与日争辉,而终难如愿,故诗人感叹伤怀,借景生情,非在景色之表面也。”[第58回回后评][3]585即香菱咏月关合日月两皇帝之争辉故实;2.评“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中“龙斗阵云销”句:“按此二句暗指雍正乾隆时代,康熙之诸皇子及其后人仍在明争暗斗,谋夺皇权。其斗争之激烈几有似天翻地覆。”[第58回回间评][3]598即湘云所联句暗喻皇权争斗;3.评宝琴《西江月》词:“开篇汉苑隋堤即已表露是政局中两方之对立,其下三春事业付东风所指失败者之一方,三春若仅指常言春景而言,而又何事业之可言。盖谓此番政局争夺已历三年光景,故谓之三春事业。明月梅花又已点破失败者乃是弘皙月派一方。下篇方写出失败者已分散流落大江南北,沦于不幸。”[第70回回间评][3]825即《西江月》词关合日、月两派(皇帝、太子)之政治隐情。由此可见,周汝昌“辨伪存真”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揭明宫廷政治斗争的隐情,即“隐去”的“真事”(“甄士隐”即“真事隐”)。那么,为什么必须从考知这一历史上少见的真假两皇帝并存的特异局面入手方能破读《红楼梦》真义呢?因为这与周汝昌坚持“史”“艺”不分的观念有关,他说:雪芹作书,是“史”是“艺”?老实说,在中华文化上,史与艺(文)从来就不曾“分家各爨”;因为,中华的文,本来就是从“史”开始[23]311。这样一来,一部《红楼梦》(《石头记》)首先就是一部“政治斗争史”或“政治阴谋事件录”,这就必然狭隘化了《红楼梦》的政治主题。并且这种处处坐实、事事关合的解读方法必然引向“索隐”的方向上,也就是周汝昌所倡导的“新索隐”学术一途,于是,这位红学考证派的集大成者便由“写实自传说”而归宿到“新索隐”了。周汝昌在《红楼十二层》“第十层:《红楼》索隐”中说:“拙见则以为:既有‘隐’,须当‘索’,不可以‘名’害‘义’;我试对书中若干词语作些注解,而方法不同于旧时的 ‘索隐派’,故特标名曰 ‘新索隐’。”[24]210他又在《寿芹心稿》一书的《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六十年追思简录》中直言正道:我的“考证”是人家给的名目,我的本心其实就是“索隐”。我以为,考证的真正存在价值和实际功能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索隐”[25]94。“考证”与“索隐”合流,实际上不仅意味着“新红学”的终结,也是周汝昌红学体系的结穴。如果周汝昌的红学体系由此结穴,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体系的寿终正寝。然而,问题在于他的这一体系繁复而非单薄,其政治历史解读只是这一体系的基础部分,而它更宽阔的视野则体现在文化主题的开掘方面。所以,周汝昌红学体系中富有启示意义的内容无疑会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生命力和影响。
处处坐实、事事关合的解读方法并没有在冯其庸的《红楼梦》“重校评批”中着意地运用,他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代序”中说:“一部《红楼梦》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红楼梦》的内涵是十分深广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含的。只有把《红楼梦》放到整个曹雪芹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书的深刻含义,如果用曹家家史来衡量这部书,是大大缩小了它的内涵。”[20]5不过,冯其庸同时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历史社会之要录”,他说:“《红楼梦》实一博大精深之杰作,以写实观之,则是康、雍、乾历史社会之要录;以艺术观之,则实康、雍、乾历史社会之艺术升华。”[20]2“社会之要录”和“艺术升华”这两个关键词可以看作冯其庸的《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他的《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具体阐发大抵没有离开这两个基本点。且看冯其庸“重校评批”中的几个例子:①第五回评:“宁、荣二公之灵之一段嘱咐,实暗寓曹家史事……此雪芹所隐之真事也。”[20]81②第五回回后评:“读此回宁、荣二公之灵所嘱,则世传曹家二次抄家论实为无据。其‘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数语,何有中间曾遭抄家之事?再参可卿之语:‘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之语,何曾有一点曹家以前已曾抄过家的痕迹?诚然,此是小说,那是真事,但人所共知,雪芹隐真事于其小说之中,所谓‘假语村言’‘真事隐去’,如‘省亲’隐‘南巡’事,‘树倒猢狲散’隐曹寅拈佛语事等等,故此处更是隐其家史之大者,读者不可不知也。”[20]89从上述举例可知,冯其庸对于《红楼梦》隐写清朝康雍乾政治历史的“探赜从真”的“索解”兴趣同样是很浓厚的,不过,他还不至于如周汝昌那样坐实于所谓“日月两派的政治斗争”。
可以认为,周汝昌和冯其庸的历史政治解读是与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批评一派的历史政治解读有相通之处的,也就是说,“新红学”或“考证派红学”在《红楼梦》解读方法和视角的这一方面,同于社会历史批评派,或者说后者借鉴吸取了前者。而社会历史批评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影响,譬如“百科全书说”、“四大家族衰亡说”等至今还写在教科书里。众所周知,历史政治解读这一视角或方法乃“旧套”而非“新径”,那么,“旧套”能不能“出新”呢?也就是说《红楼梦》研究运用“旧”的方法即传统的方法能否开出“新境”,这是红学研究者和读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俞平伯曾说过一段启人思考的“赞语”:“赞曰:以世法读《红楼梦》,则不知《红楼梦》;以《红楼梦》观世法,则知世法。”[26]270笔者试解:凭君“探源”何其难,寻得“真貌”费思量。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观察上的局限性,其实根本就没有绝对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全部的问题,正如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所以,不必自以为是地认为某一种方法就能求得《红楼梦》“全解”,所有的方法都在《红楼梦》里,取来一用便是。各有灵苗各自探,切不可标新立异、庸人自扰。笔者拟仿马克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的说法,即:《红楼梦》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红楼梦》。可见,俞平伯的“世法”说启迪人们:从某一特异方面入手来破读《红楼梦》即可“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了”的说法是虚妄的;“探源索真”的愿望和做法是可取的,而“全得真貌”的标榜则是虚妄的。“虚妄”使得《红楼梦》读解犹如雾里看花,“虚妄”使得红学论争的意气之争再难消歇。归结为一句话:都是“误解太深”惹的祸!
三、思想超前和伟大说
无论冯其庸的“超前说”和周汝昌的“伟大说”是否符合作者曹雪芹或《红楼梦》文本事实或本旨,但这些说法正在被不同程度地接受则是客观的现实。
梁归智说:“周汝昌的一切活动和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红楼梦》真正的伟大。”[27]286如若此一说法不虚,包括周汝昌的“校订批点”活动和说辞都该是为了确认《红楼梦》的“伟大”品质。那么,“伟大”二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则,《红楼梦》并不是普通的一部小说,它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应列为中华“经书”即“十四经”。周汝昌在《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批点余音”中说:“我对雪芹《石头记》的理解、认识、评价也有逐步的提高。大致说来,第一步,我正式提出《石头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第二步,是把它定位于新国学(见1999年北京大学学报2期)。第三步,提出《石头记》应列为中华‘十四经’的一个崭新命题。”[3]962这就为《红楼梦》研究红学拓展了新的思维空间与启示,当然也就为红学论争提供了新的话题。可以说,如果新中国红学没有周汝昌,也会因此没有了如此这般地热闹和话题活力。二则,曹雪芹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宗教家和伟大的文学家,作者曹雪芹的这一形象定位工作贯穿于周汝昌毕生《红楼梦》研究之中。如他在《为芹宣情教》中说:“雪芹创情教,我谓情教僧。皈依大教化,至幸超三生……孔之仁,佛之悲,雪芹情教总所归。中华文化何结穴,核心一字‘情’最奇。今后学人读者若欲读懂《红楼梦》,请从本篇创教宣言读起,当能迎刃而解。”[25]81-82“情教”说虽非周汝昌首倡,乃周汝昌所推许的民国之初一位重要的“评红”大手笔即陈蜕庵的发明,但一经周汝昌矢志不移的倡导,其影响已经渐广。当然,虽然这一工作的完成在周汝昌看来意义重大,不仅将曹雪芹的“伟大”形象化,而且也将周汝昌第三步即最后一步红学大业推到极境——把《红楼梦》提升为第十四部经书。但是,读者和研究者们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往往嫌其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倒不如“情本思想”说法更平实且易于接受,关于“情本思想”说法可参看发表于《文学评论》2006第6期署名孙逊的《〈红楼梦〉的文化精神》一文。不过,周汝昌这几步红学工作尤其第三步所显示出来的超常的“悟”性,以及开“新国学”之“新境”的学术用心实在令人感佩,即便有些人不同意他的倡导,仍然应当怀有“了解的同情”的。譬如他反复强调曹雪芹“他是思想家,哲学家,大智大慧之人。”[23]291《红楼梦》的“真正的意义也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一个‘唯人’的新高度。”[4]9他的这一阐扬今天看来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设若今天的世道人心能以“唯人”为尚,何至于世风日下、礼失诸野?《红楼梦》第18回脂批道:“所谓诗书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发,骄妄自大。”[28]255“偏是暴发,骄妄自大”——脂评早已描画出无礼可守者的嘴脸(为官者“骄妄”而“势利”、为学者“骄妄”而“势利”、为商者“骄妄”而“势利”、为民者“骄妄”而“势利”),何今世之“戾气”冲天气象竟早由脂评点醒?今世之人竟察之而无策?此又可窥见周汝昌彰明“中华文化说”、“新国学”、“唯人”之用心了,即经世致用于弘扬中华大文化之“伟大”精神以“济俗”。
如果说周汝昌是通过发覆中华传统“自古已有”的精神资源,以博观圆照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呈现的似“旧”而“真新”的境界,并将这一境界提炼为“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一个‘唯人’的新高度。”那么,冯其庸又将如何阐扬曹雪芹《红楼梦》“超前说”的呢?冯其庸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代序”中说:“贾宝玉的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代替封建制度的新时代的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有这样的思想形象,有这样耐人寻思的情节和语言,已经是大大超越那个时代了。”[20]13他又认为:“总之,曹雪芹能做表面盛世的当时偏去写‘末世’,能让他的全新的美好的人物和理想被旧势力彻底吞没,造成震撼人心的大悲剧,能从腐朽中写出新生,写出朦胧的曙光,这才是他选择荣、宁二府作为典型的原因,这才是曹雪芹的真正的超越时代的伟大!”[20]42可见,冯其庸看到了曹雪芹写出的“曙光”,这“曙光”能在封建末世被写出已经是“超越时代的伟大”了。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因为,曹雪芹正处在旧的封建制度的末期并正要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型的时期,即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从思想方面来说,无疑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转型期的新思潮的真实记录。我曾说过,曹雪芹批判的是他自己的时代,而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他的社会理想,如自由人生、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废除等级、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等等,无疑都只能是未来的意识,未来的现实,然而曹雪芹居然在十八世纪的前期就提出这些理想来了,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理解的,何况他又是用的‘假语村言’,无怪人们要把贾宝玉看做‘似傻如狂’了。”[20]45冯其庸同时看到:“从雪芹所处的时代来说,他虽然已经具有自生的(非受外来影响的)初步觉醒的人文主义思想了,但更先进的完整的社会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未出现,雪芹曾发出‘何处有香丘’的感叹,可见他没有解决理想社会的问题。因此他只能坚决与社会决绝。并写出自己具体的人生愿望,至于人生的道路何在,社会的道路何在?他走的还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宝玉的出家,是否也含有更深的意义呢?殊令人深思。”[第一百二十回回后评][20]2033-2034这也就是说,曹雪芹超前的思想不可能在“自古已有”的基础上生成,只能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生成,即资本主义“萌芽”是促成曹雪芹作为“超前的思想家”的时代背景。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坚信“自古已有”说,那么,势必形成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高度、思想力量和意义的不足估价。只有坚信“萌芽”说,才能揭示曹雪芹民主思想“新”而不同于“旧”(即“古”)的思想性质,也只有这样,“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的说法才能成立。人们不禁要问:“周评”与“冯批”的各自说法之高下优劣如何评价呢?或以为“冯批”之说似乎更加先进而时尚;或以为“周评”之论似乎更加切实而合理。其实,这是一个人言各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话题。并且,“周评”与“冯批”都同时在遭遇着“质疑”“辩难”的考验,定论为时尚早。当然,尽管冯其庸与周汝昌各自在阐扬曹雪芹作为“伟大”或“超前”的“思想家”时的着眼点和路径并不相同,毕竟各成一家之言。且由于冯其庸与周汝昌的坚持不懈的高度评价和不懈阐扬,很大程度影响着新时期红学曹雪芹或《红楼梦》思想研究上的学术方向与认知水平则是毋庸置疑的。
通观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文字,可形成这样的观感:重新释放和发挥他们此前已成型的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和思想是其基本任务,而阐发令人耳目一新的妙论宏旨则明显不足;“周评”则宏阔之谈和坐实之论兼善,“冯批”则笺证之好和平实之述偏重。尽管作为近年出版的“评点”新著所能给予读者的启发意义尚待阐发,但视它们为当代《红楼梦》评点的典范之作应无疑义。“周评”与“冯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将其对曹雪芹的思想艺术成就、《红楼梦》本旨论、人物论、结构论、笔法论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研讨,应当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鉴赏,有助于读者对当代《红楼梦》评点的感受和评价。
[1] 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2] 童庆炳.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5(4).
[3] 周汝昌.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M].漓江出版社,2010.
[4]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5] 周汝昌.周汝昌汇校八十回石头记[M].人民出版社,2006.
[6] 北京曹雪芹学会.红楼梦程甲本探究[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7] 胡文彬.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M].时代作家出版社,2011.
[8] 周伦玲.似曾相识周汝昌[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9] 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 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1] 胥惠民.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J].红楼梦学刊,1996(3).
[12] 胥惠民.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3).
[13] 胥惠民.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9(1).
[14] 胥惠民.不要把瞎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与周汝昌先生商榷[J].铜仁学院学报,2010(1).
[15] 胥惠民.《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0(1).
[16] 胥惠民.我为什么要批评周汝昌先生[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2).
[17] 胥惠民.“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1(2).
[18] 胥惠民.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1).
[19] 胥惠民.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1).
[20]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1] 王志尧.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J].铜仁学院学报,2010(3).
[22] 王志尧.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续篇[J].铜仁学院学报,2010(4).
[23]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作家出版社,2003.
[24]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上海出版社,2005.
[25] 周汝昌.寿芹心稿[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26] 俞平伯.红楼梦心解——读《红楼梦》随笔[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7] 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M].漓江出版社,2006.
[28] 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M].齐鲁书社,1986.
I207.411
A
1009-105X(2012)03-0114-7
2012-07-21
高淮生(1963-),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