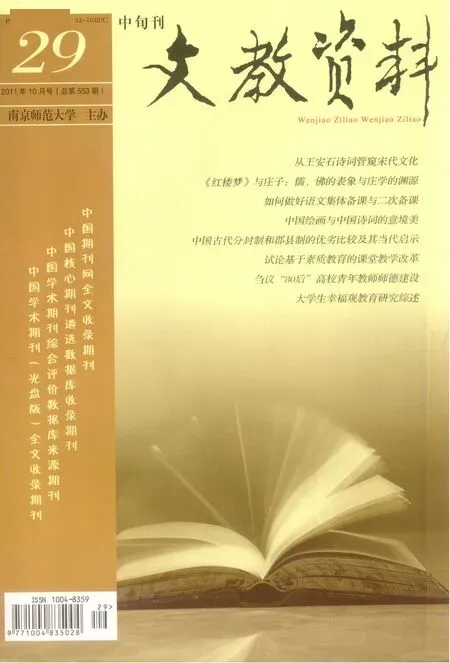傅山书学思想及其艺术分期浅议
2011-12-31刘琰
刘 琰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中国书法系,陕西 西安 710049)
有人说,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也有人说,他“书法图书,皆超古今”;还有人说,他是“晋唐以下第一家”,他就是傅山,那个主张文章“生于气节”的诗人,那个以妇科见长的名医,那个睿智博闻的学者,那个书画印皆通的艺术家,一个大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清史稿》记载:“傅山,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冘。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天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1]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名甚多。明清鼎革之后出家为道,道号“真山”。生于1606年,据白谦慎先生推断,其卒年“大约在1685年正月或二月”[2]1。 纵观傅山的一生,悲情而又绚烂。他曾仗义执言又身体力行,同奸臣阉党殊死斗争,获得了“义士”的美名;他也铁骨铮铮,秉持儒士的忠义,拒绝清廷的高官厚禄,誓不做贰臣。明亡之后,他奔走各地,为反清复明的大业劳心劳力,险些丧命,无奈“大局已定”、“天命攸归”,在光复大明无望之际隐居避世,行医著书,研读经史,留心考据,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钻研令人慨叹,并对各种思想流派与宗教表现出兼容的态度,难得的是他又能独立于各家学派之外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明朝末年,傅山的思想就已呈现出了进步倾向。有《霜红龛集》、《两汉人名韵》和大量医学著作存世。
然而,傅山最为令人称道的当属其书法。他五体皆善而尤精于行、草,不仅技法出众,而且独有一套精辟的书法理论,为后世所折服。
1.傅山的书学思想
傅山主张学习书法要取法篆隶,崇尚自然,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理论,并强调“作字先作人”。
傅山坚持取法乎上,特别将“篆书和隶书视为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2]2他曾说:“不作篆隶, 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 ”[2]3傅山对篆隶的热爱或许也是其钟爱充满篆籀笔意的颜真卿书法的重要原因吧。然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篆隶,白谦慎先生指出“是为了将这两种早期字体的笔法融入较晚出现的字体的书写中,以使这些晚出现的字体更加有古朴之意。”[2]4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当与傅山研究诸子学术、历史、考据、古文字的学问有关,他崇尚篆隶,体现的正是一种追本溯源的理念追求,我们又能否大胆地设想他的这种溯源或多或少地带着对逝去的大明王朝的一些依恋呢?
傅山说:“天机适来,不刻而工。 ”[3]1又说“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4]同样都是崇尚自然,追求一种不刻意安排布局的书写状态,实现书写者情感与笔墨线条的完美统一,这一切所说的也正是天人合一,人书合一的问题。傅山关于自然的阐发,他著名的“四宁四毋”理论应该是最确切的注释。
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5]1理论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美学品评标准,但时常被人曲解其意来为自己恶俗的“丑书”寻求书法史上的开脱,这无疑是一种悲哀。傅山所讲的“拙”、“丑”、“支离”、“直率”都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拙”乃朴拙之意,追求一种“大巧若拙”的状态;“丑”亦非不美,而是丑中有妍;“支离”与“直率”都在强调一种对传统技法的超越,务求达到无拘无束,率意而为的情感宣泄。而“巧”、“媚”、“轻滑”、“安排”所指的正是清初在赵孟頫与董其昌书法影响下所形成的百般造作的端正流美之风,傅山提出“四宁四毋”,目的在于矫正时弊,同时也凸显了其性格中的刚毅不屈。事实上,“宁”与“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应该辩证的对待。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四宁四毋”应是书法创作终极阶段而非学习与自我风格寻找阶段的追求,它的践行当在个人书法技巧纯熟之后。
傅山有诗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判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3]2这是傅山晚年写给儿孙的作书之道,指出字的好坏根本在于人品的优劣、格调的雅俗,人“奇”字方能“古”,笔墨技巧再怎样娴熟精妙都无法弥补人格的缺陷,作书之人的精神气节才是最重要的。他肯定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推崇颜真卿,鄙薄赵孟頫。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去探讨傅山在对待赵孟頫书法问题上的情感变化。之所以强调情感,是因为我们相信在傅山对赵氏书法的认识上,情感因素是大于艺术诉求的。他一开始学习赵孟頫的书风并一度以之为重要的创作要素,后因为明清鼎革,赵氏身为宋王朝后裔却变节为蒙古人做官的事实使得傅山对其人品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感,进而鄙薄其书法,这是由于相似经历下的不同道路选择而造成的,是牵扯民族情节与个人政治立场于其中的。再到后来,尽管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傅山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他明白了满清统治日益坚实,大明复辟无望,这一情感变化使得傅山对赵氏书法重新进行了客观解读,肯定赵孟頫用心于右军,却始终无法赞同赵氏的为人,这与傅山晚年坚决不做满清的官却不再阻止其他汉人为清廷效力的思想变化可以说是一致的。单纯就对待赵孟頫书法的问题,我们极易理解傅山推崇“作字先做人”的理由,这一书学思想的产生自然深受其所受教育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否认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变革有关。这种对高尚人品道德的追求贯穿了傅山的书法艺术始终。
2.傅山的书法艺术分期
傅山自言:“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东方朔》、《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似之。又进而《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 ”[3]3又云:“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5]2
根据傅山的自述与历史考证,其书法风格的变化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当为1615—1644年明亡之前的29年间。从八九岁起用心于晋唐楷法,到二十岁左右转为学习赵孟頫与董其昌圆转流丽的书风直至明亡,经历了近三十年光景,这一阶段正值傅山的青壮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腐朽动荡的时期。出身官宦家庭的傅山自幼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但是时值国家腐败不堪,政治日益衰竭,傅山耳濡目染,一颗心系民族命运的赤子之心也为影响了后期的为人处世与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的傅山对晋唐楷法是下过苦功的,但自称“无一近似”,因为傅山1639年之前的书法作品我们没有见到,所以无从判断其晋唐楷书的临摹究竟达以何种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期的楷书功底为后来行草的发展埋下了厚重的基石。傅山二十岁左右转学赵董,上手极快,我们从其现存的早期作品中都极易看出赵董的影子。例如1639年前后的《佳杏得红字诗稿》(如图1)与1641年的《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如图2),前者为行书墨迹,点画婀娜,结字清秀,章法疏朗,赵孟頫的痕迹清晰可见;后者虽为石刻拓本,但是依旧无法掩盖其潇洒流丽、圆转温润的面貌,一派赵董风姿伴着些许米氏神韵。傅山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沿袭了当时普遍的书法学习道路。

图1

图2
中期当是1644年明亡后到1662年南明永历帝被杀的18年间。这一时期的傅山致力于光复旧朝的行动,即便是1655年“朱衣道人”案获释后依然保有复明之心,尽管在行动上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的傅山由于赵孟頫的“贰臣”身份而对其书法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呈现出“因人废书”的状况。同时,他被颜真卿的高尚人格和绝佳的书法艺术所吸引,开始转而学习颜氏书法,在书法创作特别是楷书与行书手札中流露出极强的颜体风格,其间的大幅作品极尽张扬之能事,时常可见各种伸长的笔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如图3)与《饯莲道兄十二条屏》(如图4),前者为楷书,气象宏大,得颜体之精髓,结字上却又较颜体活泼险绝,整体的用笔和个别字的结体依然是颜体风格无疑;后者为行草书,逼人的气势中透露着桀骜的性格,字间可见颜体笔意,但笔画伸展穿插,狂放至极。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傅山书法风格求变真正的开始。

图3

图4
明组织遭
后期应为1663年开始各种反清复 到全面镇压,傅山发觉反清无望后心态转入平和直至1685年去世的22年间。这一时期,看到社会日益稳定的傅山用心于各种学术研究,重习王羲之书法,并再次肯定了赵孟頫书法的历史贡献。他的行书手札在此时表现出强烈的大王风姿,例如《论汝刻石鼓文》(如图5)笔法精到,始转提按极尽王氏书风特色,温润秀美中带着些许古意。大幅草书作品更是尽得大王神韵,并呈现出逐渐内敛的状态,罕有大量尽情舒展的笔画,抒情表怀之意却尤胜从前,从著名的《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可见一斑。此外,由于对金石与古文字学的研究与热爱,傅山亦在行、草书融入大量篆隶的书写技巧,并开始钟情于章草的书写。

图5
综上可知,傅山书风是随着其政治立场与个人情感的转变而转变的,每一次的转变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并将其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8:138,55.
[2]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6.7:326,302.
[3]傅山.霜红龛杂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4:6,11,24.
[4]傅山.傅山全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19.
[5]孙稼阜.朱衣道人—傅山的生平及其艺术[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6:49,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