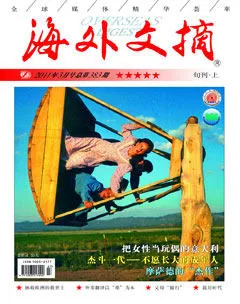混居时代
2011-12-29尤里娅.拉丽娜/文易文/译
海外文摘 2011年3期
在莫斯科,几人合租一套房比每人单独租一间房子既便宜又更容易租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租住在一起。除了物质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住户之间有共同的志向——低碳生活。
“生态阁楼”走廊的盒子里装着批发来的纸袋,该项目参与者之一塔吉扬娜·卡尔金娜(27岁)是一位教育规划项目经理,她已经两年没用塑料袋了,总是随身带着布袋。塔吉扬娜有12年没吃肉(“生态阁楼”的居民都是素食主义者),她总是避免使用塑料制品,只购买当地生产的食品(避免运输过程中浪费燃料),尽量不坐飞机。
她跟未婚夫伊万·尼涅卡一起住在混居房内。伊万26岁,是透明国际俄罗斯分部副经理,去年刚加入欧洲绿党执行委员会。他们婚后或许会住在单独的住宅内,不过现在他们尽量遵守混居房内的生活原则。
“生态阁楼”的部分住户只骑自行车,部分人乘公交,有的则步行上班。他们用太阳能电池给手机充电,希望所有的数字设备和家用电器都用太阳能。大多数住户睡在地板上,家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子里的东西可以二次使用。冰箱和洗衣机是别人送的,他们也把自己的东西送人:客厅里有一个自由交换平台,可以免费取用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说跟陌生人住在生态混居房里还可以理解,那么每周邀请陌生人,而且是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听课,则有点让人无法想象了。“生态阁楼”的住户们已经开办了多次课程,如“生态设想基础”、“国际生态志愿行动”、“自然饮食实践”等。笔者去采访的那天,有20个人正在听“都市生态主义和太阳能利用”课程,授课人是建筑师谢尔盖·涅勃姆南西,他是有效利用城市自然资源——太阳能构想方案的创始人。
“我对空间中存在的能量和分布到住宅的能量进行过测算,”谢尔盖说,“比较了照射到居民区的光源和住宅内部接受光源的数量,结果是,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只使用了大约1%的自然能源。”
这次课是在傍晚开始的,用人工照明。大多数听众已经坐在了地板上,新来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客厅门上挂着甘地的名言:“欲变世界,先变其身。”
前一段时间,“生态阁楼”的住户之一雅娜离开了这里,为了能住进她原来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网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有30个人想住进来。最终,他们选择一名女子加入,而为另外落选的29人上了一次“如何创建生态混居住宅”的课程。
“生态阁楼”走廊的淋浴间里嵌着一个收音机,它的任务是提醒人们在一首歌的时间内淋浴完毕(3-5分钟)。浴室的水表就装在变温器旁边,方便大家看到用水量。夏天房子内的部分住户(包括姑娘)都剃成光头,这样可以不用洗发液,不用摩丝,少用水。洗澡和洗橱具的清洁用品不能含磷酸盐和氯这些对大自然有害的物质,他们购买节能用具,用芥末刷碗,有人甚至用燕麦。
生态住宅房客安德列(25岁)是社会关系部门的媒体顾问,他说,即使将来搬到单独的房子住也会继续采取给垃圾分类的做法。他在国外生活过,去过很多国家,他尽量不用塑料袋,这在西方十分正常。在他看来,俄罗斯没有普及这种做法才是不正常的。
第5名住户罗曼·萨勃林(31岁)在社会关系部门工作多年,正在跟朋友们一起实施自己的项目计划:建立绿色至上办事处,将办公室改造成生态场所,尽量减少垃圾排放,将已产生的垃圾进行二次利用和无害处理,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浪费……罗曼并不打算一辈子都住在混居房内,春天他想搬到莫斯科郊区去,建筑或租一座生态房,他未来的邻居也必须是环保人士。至于讲到跟陌生人为邻的感受,他说:“有共同兴趣和共同愿望的人们多多交往,有助于促进项目成功。最近4个月‘生态阁楼’已经来过500个人,实施了10个生态项目。”
混居房的住户并不反对社会消费,重要的是,他们展示了积极的消费方式,他们宣传最低消费主义,而不是冲动购物。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既定原则,罗曼·萨勃林在网上计算自己的“生态足迹”。正如世界自然基金网(WWF)所说,“生态足迹是个标准概念,反映了人们对周围生态资源的使用,即生产我们所必需的资源以及吸纳和对人类所排废物进行再利用的地域面积。”根据2005年的资料显示,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态足迹平均2.7公顷,而地球所能承受的生态足迹大约为每人2.1公顷,俄罗斯的平均生态足迹为3.7公顷。
“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罗曼说,“我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译自俄罗斯《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