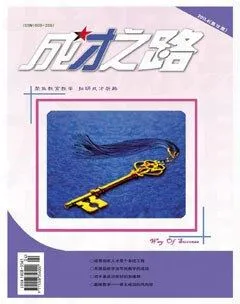歌曲《小河淌水》赏析教学中的美学探究
2011-12-29史建华
成才之路 2011年12期
中国音乐始终沿着以声乐为主的道路发展,这在很大程度缘于我们的音乐文化传统。李渔说:“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此处的“自然”并非自然事物,而是没有过多人为的“自然而然”之意。“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所以声乐是情感的最亲切、最直接的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的情感表达方式。
我国声乐的发展并非坦途,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儒家“文以载道”“乐以载道”的泛道德思想的影响下,“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使声乐逐渐失去了其艺术的本真面目,他们所创造的音乐,甚至连统治者本身听之也出现昏昏然的状况。与此相反,被儒家斥为“郑声”的民间音乐,却以其鲜活的生命力,非凡的艺术性,始终生机盎然,并得到蓬勃的发展。仅就建国后对我国各地方民歌的普查结果看,我国民歌有近四万首之多。其中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音乐思维和文化传统。
一、《小河淌水》体现着中国的艺术精神
有人将人类文化分为两次高峰,第一次即是我国先秦时的百家争鸣,它直接形成中国人的形而上的宏观的思维方式,并藉此使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二次文化高峰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形成了西方人的形而下的微观的思维方式,科学思想应运而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以儒家为主流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礼乐并举,“礼为天地之序,乐为天地之和”。礼是从外在方面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乐是使人在内心达到和谐。“尽善也,又尽美矣”即内容和形式达到统一。
《小河淌水》虽然是一首云南民歌,并且是描写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但是它却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的“乐”的精神(当然,中国传统的“乐”并非单纯指代音乐,还应包括诗歌和舞蹈。而本文所言的“乐”仅仅是指代音乐,以后不再言明)。
《小河淌水》是一首典型的云南弥度山歌,表达了一个少女在月下对情郎的思念之情。开始一个由弱渐强的长音,体现着艺术无言之美,含无尽之间见于言外。开始的长音,自由的节奏,毫无做作之感,率性而为,好似少女由远及近深情地呼唤,也似一缕温润的轻风,微微地拂过人的心里。更重要的是它引出了一串清丽和谐的旋律,毫无突兀之感。第一小节,羽调式上行的音阶,描写出月亮冉冉升起的景象。中国诗歌历来讲究“兴”的作用,见象立意。“月亮”作为“思念”永恒的象征物,被广泛地使用。两个下行旋律好像当空的皓月普照大地,仿佛使人能够洞彻每一个角落。
“看见月亮想起我的哥”是典型的睹物思人,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哥像月亮天上走”,旋律的下行音阶映射出少女淡淡的思愁,而音域的提高是少女想起哥哥时热血沸腾心潮涌动的外化,也是少女希望如清晰地见到月亮一样见到情郎的美好的愿望。
众所周知,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中国古代的青年缺少对爱情的直接表达。因此有人说西方人的爱情表现在婚前,更多是“慕”,而中国人的爱情多在婚后,更多的表现在“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经典的爱情故事多是悲剧性的。因此,这首作品便可能只是少女的一种美好憧憬和期盼。接下来高音区二度的下行,更像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撕心裂肺的呼喊,粗犷悲怆之情由然而生。最后的几小节以清新隽永的旋律,婉约、灵动的词藻表现出内心归复平静的少女心绪。
第二段歌词是思念之情的具象化,因为它具体到了“半坡”“深山”等自然的景物。一阵清风徐徐吹来,作为思念的载体,充满天地之间,弥漫于山野、河畔,飘到情郎的心田。高潮处的“哥啊,哥啊,哥啊”较之上一段旋律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在情绪上则更应该体现出荡气回肠之感。“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用设问的方式加重了语气,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达到了至爱至美的境界。
从民歌的创作角度讲,它基本是以即兴创作,并以口头传唱的形式进行传承,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众所周知,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都是在时间中展开,又在时间中消失,即所谓的“瞬间消失性”。也正是为如此,造就了无数二度创作者——歌唱家。歌唱家在演唱过程,又必须将自己的心智融入作品之中。带上主观的烙印,就这首《小河淌水》而言,原来全曲共五个乐句,自然流畅,首尾贯通,遥相呼应,形式上已经非常完整。但是在传唱的过程中有的歌唱家,在结尾处独具匠心地加入一个尾声“哎,阿哥”并在渐弱中徐徐结束,毫无蛇足之嫌,更无赘疣之感,反而使作品境界全出,并与开始处的长音形成一种循环往复、周流不滞之感。“哎”字,有似少女轻轻的叹息,相思之意皆在其中;更轻的“阿哥”则体现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美感,“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长歌之哀,甚于痛哭”,使作品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曲终人去韵犹在”的魅力。
二、《小河淌水》的美学价值
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艺术的二元。《小河淌水》既有由自然造化的实境描写,又有因心造境的虚境构建。流水、月色之为物,禀自然之秀。而由月亮引起对情人相思之苦,进而冥想出的半坡、深山则是以手运心的结果。中国美学对于艺术作品的品藻是有层次感的。“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地,余霞绮天。此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坂,泳鳞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然而远也。”“一境情胜也,再境,气胜也,三境格胜也。”《小河淌水》宛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三种境界用一条绵延起伏的旋律线连接起来。首先,羽调式确定了作品的基调,淡雅、婉约。而五声调式则处处体现着“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精神,多处音阶的级进进行是对月亮升起的直观写照;高音处二度下行级进进行与少女思绪共构契合。其次歌词引子处的一声啊,好似水墨的留白,衬托出一轮皎洁的明月,并由此兴发引出少女思念的对象——阿哥,体现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气韵生动。最后“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使作品格调更高,呈现出瞬间见永恒的主题——爱情,如流水一样不曾停歇。
然而,声乐归根到底还是属于音乐艺术。虽然《小河淌水》的歌词是一首优美的诗,但是它最终还是要融入音乐的形式之中。也就是说旋律和歌词在声乐中并非平等地位,歌词必须融入音乐之中,从属于音乐。优美的歌词对声乐艺术固然重要,然而它只能作为音乐创作的蓝本,启迪演唱者的乐思,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音乐。正如沈括所言:“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也就是必须摒弃口语表达时根据不同部位发言而划分的唇、舌、齿、牙、喉音的特点,统一发音位置,融入旋律之中,“使字字举木皆轻圆,悉融入声中”。进一步说,必须将对文字真实性的追求,变成对音乐美的追求。
就歌曲《小河淌水》而言,能够感人至深的还是其精匀、完整的音乐形式,流畅、质朴的旋律。“一切艺术已逼近音乐为旨归”是有道理的,因为音乐“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像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当然,如果演唱歌曲时能够在表现音乐的抑扬、清浊的同时,达到字正而腔圆的效果,使听者同时享受音乐和文学的复合审美,无疑是艺术家所求之不得的。
一蕾而知春,一叶而知秋。虽然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只是我国浩瀚音乐海洋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它以如诗如画的旋律,历久弥新,体现着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传统,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审美情趣。
(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