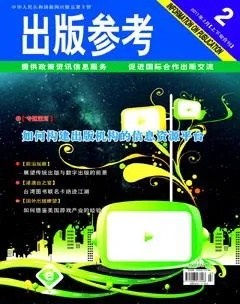学术出版推广平台的开发
2011-12-29刘德顺
出版参考 2011年3期
谈到学术出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难做”。并且很多人把这种“难做”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此类作品在编辑加工出版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编辑人员;二是此类作品的市场狭窄,或者说受众面小,读者群狭窄,最终无法实现大规模的销售。但不可否认,这样一种分析或想法的存在,使得众多出版方不愿意介入学术出版,并进而促成了另外一种局面: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由于门槛低、市场大,导致众多的出版方介入,并最终把原有的巨大市场份额摊薄;而学术出版,由于门槛相对较高、市场小,无人愿意进入,反而使得原有的小市场变成了“大市场”。
当然,学术出版中专业编辑的打造非一日之功,但是,如何面对茫茫人海之中的专业读者开展营销推广,同样也是关系到学术出版生死存亡的命脉。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学术出版所面临的境遇:其一,专业学术出版物的读者群小,销售周期长,因此存在着上架时间短、上架空间逐步萎缩的状况。换句话说,读者原有的通过逛书店直接和图书接触并随即购买的几率,在现实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小。其二,专业学术出版物所面对的读者一般均接受过专业领域内的训练,因此,对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信息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也就是说,专业学术出版领域内的营销推广,必须明确把握所要影响的终端读者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内容特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学术出版推广平台的筹划与开发变得重要起来。
当然,如果问到业内同仁,如何推广学术图书,大家都可以回答一二。原因在于,国外学术出版推广的经验早就被出版业内的先贤介绍到国内,如面向专业学术会议(包括专业学术团体的内部交流)的推广、以专业期刊或网站为平台的推广,以及出版方自身筹建的读者数据库推广,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面向专业学术会议的推广。以笔者参加的历次学术会议来看,我们同国际上大的专业学术出版社存在着以下差距:一是国内出版社考虑到参会和差旅等诸多费用的问题,很少参与这种会议的图书展示和销售,而国际出版社对于这种高质量的大型学术会议则愿意选派人手参与;二是国内出版社在会议的展示和销售活动中,忽视营销细节,形象展示不够。以国际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为例,该社在会议的展示和销售活动中拥有一整套的实施方案,既有专业的团队,除去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服务水准不谈,单单从团队人员的着装来看,就已经存在巨大差距。又有一整套的品牌展示的“道具”,比如在出版社品牌展示上,有带有社标的桌布、易拉宝、书架、展板等,无一不从细微处展示出版社对于品牌形象的重视;而在具体图书系列品牌的展示上,该社则会根据会议涉及专业内容的差异提供不同的专业图书宣传册以及样书等。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国际出版名社在营销上对于细节的重视。而反观国内出版社,有的仅仅纯粹从会议当场实现的销售额来看会议展示与销售的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会议展销所产生的销售利润是不足以弥补参加会议和差旅的费用的,或仅仅是敷衍作者的要求,对于细节不加重视。但是,不要忘记,面向专业学术会议的展示与营销,不仅仅是为图书寻求更多的读者,实现一些销售,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作者的需求,而更多的是让参会的专家学者看到专业出版社的存在以及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从而有力地争夺作者资源。
其次,我们来看以专业期刊和网站为平台的推广。专业期刊和网站作为专业读者和作者经常浏览及获取信息的平台,相对于其他大众媒体更具有准确的定位,而这种定位源于其自身提供的内容所能够集聚的小众。如果专业出版方所提供的产品与专业期刊和网站所针对的小众读者具有统一性,那么它们就是图书产品信息有效的搭载和发布平台。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这些媒体和网站比较欢迎同他们的内容趋于一致的产品信息,原因在于,作为出版方所提供的产品信息同样也为该网站吸引这些小众群体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其二,这些媒体对于出版方所提供的产品信息搭载和发布所要求的费用,一般要远远低于大众媒体,有些甚至是免费。
第三,我们来看出版社自身筹建的读者数据库推广。数据库营销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数量是拥有的终端读者的数据的条数,而质量是数据本身的有效性,也就是作为数据终端的读者是否与我们所提供的营销内容相匹配;二是以数据库为基础的需要推广的信息内容建设,内容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终端读者对于信息内容的接受度。有时候,很多出版方即使拥有了强大的数据,也会面临平台“失效”的困境。究其原因,正是在于出版方对于依托于平台的信息内容建设的忽视,在平台建设初期,终端读者会带有好奇心来阅读信息,但是,一旦终端读者发现这一平台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信息的价值较低,对于信息的接受度就会明显下降,从而造成即使拥有众多终端数据,也无法通过平台传递信息的困境。与此相反,如果出版方能够依托此平台精心策划每次信息发布,让现有终端读者发现信息的价值,那么原有的终端读者数据就能够得到很好维护。与此同时,由于每一位终端读者都拥有自身的专业小圈子,自然会在圈内分享该平台所获取的信息,从而进一步扩大原有平台的影响力。另外,数据库建设本身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想短期内拥有众多高质量的终端读者数据比较困难,这也有可能就是国内出版业数据库营销尚未成型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的建议是边收集终端读者数据,边依托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发布。由此以来,可以实现两方面的目的:一是避免了由于长时期收集终端数据而不使用导致的前期收集的终端数据的失效,终端读者的数据会经常发生变化,如果不定期向他们发布信息,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有的终端读者可能就不使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接收地址了;二是在继续收集终端数据的同时,通过精心策划每次信息发布的内容来吸引更多的终端读者,可谓是又多了一条渠道。当然,数据库本身属于读者的隐私以及出版方的机密,必须做好保护。
毋庸置疑,上述三种推广平台(当然,还存在其他平台,但是以上所提到的三种平台属于出版业内较为公认的操作模式)的筹划与开发将有效地影响专业读者对于信息的获取。当然,对于出版方而言,这三种平台自身所具有的利弊也值得考量。
在此,笔者把学术出版推广平台分为三类:一是自建平台,这类平台完全由出版社花费资金、人力、物力筹办,出版方对此平台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比如出版社自身的网站,刚才上文中我们提到的终端读者数据库推广,当然还有一些大型出版集团自办的期刊如《文景》,等等;二是半自建平台,这类平台由出版方依据其他媒体平台提供的空间,按照其他媒体的结构规划进行内容信息的添加和筹建,如目前国内诸多出版社以豆瓣、新浪博客等提供的空间设计的信息发布平台,这些平台的内容绝大部分由出版方掌控;三是搭载平台,出版方对于此类平台来说只是内容的提供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他人制造内容,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类平台包括专业的或者大众的资讯类媒体、书评媒体,各大网站的读书频道,等等。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专业期刊和网站推广平台。
以上的分类是按照出版方对于平台的自主性的差异来分类的。这种自主性的差异隐含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的差异。与此同时,它也隐含了对于终端读者数据占有上的差异。
自建平台尽管在筹建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出版方对于终端读者数据是完全掌控的。当然,这种掌控必然涉及对于数据和信息的经营,个中的利害关系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但不可否认,当自建平台完善之后,或者说拥有了自主品牌和对终端读者的影响力之后,可以成为其他出版方或者机构的信息搭载平台,并最终实现赢利。
半自建平台在初期就可以搭载现有的平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原有的媒体平台实现终端读者的集聚。从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来看,是相对较小的,但是,从对于终端读者数据的把握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终端读者的集聚同样需要出版方通过对平台的内容提供和设计实现,这需要一个过程;二是通过这一平台所集聚的终端读者首先是由半自建平台的提供方(比如刚才提到的豆瓣网)把握的,其次才是由半自建平台(即出版方)所间接把握的,当然,平台是由别人搭建的,主动权属于他方本无可厚非。待到合适的时机,可以以此为平台,让终端读者自己在此平台上向出版方提供数据,但这似乎是多走了弯路。与此相反的是,各出版方半自建平台所搭载的平台由于众多出版方信息内容的提供与设计,最终形成了一个拥有海量信息的“巨无霸”,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搭载平台在初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但是需要出版方考察搭载平台所集聚的终端读者是否与其产品信息相匹配,这是其一。同时,搭载平台有时候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并且这种资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减少,因为广告的价格始终是在上涨的。当然,出版方也可以随时不提供资金而实现信息的搭载,但是,如果出版方没有自建的平台,也就是说不自有终端数据,那么对于搭载平台的依赖将会延续下去,不同的只是被不同的搭载平台“剥削”而已。但是,即使面对“剥削”,出版方也必须对于搭载平台选择的投入产出比有清晰的计算。
以笔者接触到的中国邮政提供的针对终端客户邮发信函为例:中国邮政客户数据部可以按照出版方的要求提供各类人群的数据,客户数据属于中国邮政,出版方无法获取,并按照出版方圈定的客户数据,由出版方提供各类材料,面向客户寄发。中国邮政开出的价格如下:1条终端客户数据使用费为0.1元,邮寄信函重量在100克以内的为0.6元。假设出版方按照自己的需求,设计一张16开四色彩页,成本在0.2元,邮寄5000份,那么实现这次面向终端读者的信息传递活动所需要花费的费用为(0.1+0.6+0.2)*5000=4500(元),而均摊到每一位终端读者上的费用是0.9元。我们先不考虑信函邮寄到终端,终端是否打开的问题。让我们换一种思路考虑,如果我们搭载某一专业类杂志平台,在此杂志内做广告插页,同样也是一种16开四色彩页,广告费用是5000元整,而其发行量是10000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均摊到每一位终端读者上的费用就是5000/10000=0.5(元)。与中国邮政的影响一位终端客户的成本相比,专业杂志类平台节省了0.4元。当然,笔者在举例过程中对于诸多数据仅仅是一种假设,具体在涉及搭载平台的发行量及费用上,则需要出版方综合考虑,最终核定最优选择。
无论“剥削”与否,出版方对于产品信息的发布与推广是必须以平台为依托的。比如在短时期内无法筹建平台的情况下,选取合适的搭载平台成为最优选择。
行文至此,可能很多人对于自建平台或者说终端读者数据库的建设跃跃欲试。但笔者认为,上文中所列的各类平台的筹划与开发,是必须以出版方的出版方向或者说产品线为依托的。假设某出版方以法律类图书作为自身的主要出版方向,偶尔涉猎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律类图书的宣传推广平台的筹划大可以考虑建设法律类专业读者的终端数据库,而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则大可不必了,试想仅仅为了寥寥可数的图书品种花大力气去筹建该类终端数据库,是该考虑一下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了。相反,在这个时候,充分利用相配套的搭载平台,似乎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因此,学术出版推广平台的筹划和开发对于出版方来说所采取的必然是一种混合模式,并且必须以自身的产品构成为前提。当然,出版方在不同时期对于各类平台的选择也会略有差异。
(作者单位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