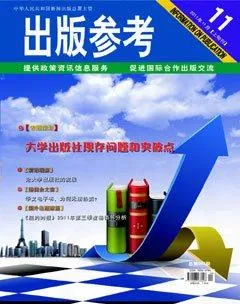数字时代传统出版物的传承与保护
2011-12-29李卫东
出版参考 2011年21期
我国已经进入到了数字化阅读的时代。这在人类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是一个全新的飞跃。然而,在从有形媒介向无形媒介、虚拟媒介过渡中,产生了两大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如何传承出版业固有的使命?二是如何确保思想产品的所有权?这就是本文的中心:传承与版权。
数字出版碎片化冲击着传统文化传承
自商周甲骨文出现以来,人类就力求将思想文化产品完整、准确地传播给下一代。《诗经》集合了周代民间的诗词歌斌,作者力求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在后人面前。东周时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藉,都是本着这样的一个思想。
同时,为了确保文明构架的一致性,一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都体现在“编”字上。《说文》曰:“编,次简也。”即将竹简依次序组合在一起。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编著者(社会主流意识)想告诉后人的历史,以及能够告诉后人的历史。因此,历代都将修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往往是政府的最高官员入主史馆,力争尽可能完整地将一个时代的文明思考流传给后世,《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都是在这一思想下完成的。
因为出版的这一任命,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从隋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科举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群体之上的。人们系统地阅读过往的文明成果,并形成新的思想成果。
然而,随着数字化阅读时代到来,由于出版形式的改变,带来了传统阅读习惯的根本变革。系统化阅读已经远离了大众,碎片化阅读、碎片化出版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爱好。
由于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化移动终端产品不断创新,在线阅读、手机阅读、手持式阅读器等数字化阅读方式迅速普及。根据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8-70周岁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人均每天上网时长为42.73分钟,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10.32分钟,国民阅读电子书超过6亿本。
在这其中,具有系统性、代表性的主流文化产品,渐渐远离了大众,比如经典作品,则明显关注度不够。
传统作品难以数字化的原因
在2010年7月结束的第四届数博会上,甲骨文大中华区产品战略部高级总监刘松先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现有数字出版的浅阅读、短阅读过多,而深阅读太少”。这说明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尽管数字出版产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在数字内容的生产上过于关注消费化的短阅读、浅阅读产品,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广告,这些数字内容本身只是浅阅读,甚至只是一种娱乐形式和信息形式。
缺乏系统阅读及深度阅读,将会对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对文明的传承产生不良后果。
造成碎片化浅阅读及碎片化出版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传统文化数字化的难度很大。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众多,将其进行高质量的数字化加工,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比如元数据的抽取是否有利于各种方式的检索;制作的格式是否能被各种阅读终端所使用等,这些都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与较大的资金投入。
第二,数字出版的外部环境目前还不太成熟。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型出版业态,尚属于起步阶段,除了内容的数据化,还有平台建设、数字版权保护、电子阅读终端的普及等环节。产业链上的这些环节不完备,传统文化大规模的数字化传播也就很难开展起来。
第三,目前,网络内容提供商过于宽泛,上传内容已造成内容泛滥、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缺乏优质内容,造成出版的碎片化,不仅有害于数字产品品牌的创建与打造,而且也很容易导致同质化现象发生。
第四,阅读的实用化、娱乐化。由于社会的压力及工作的需要,目前人们的阅读更加实用化、功利化,只关注与工作及自我提升有关的知识点,很少关注知识的系统性。而各网络平台的搜索引擎恰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需要。
同时,人们更加看重阅读的娱乐化。系统化学习是个艰苦的过程,而且“投入产出”不符合社会目前的标准。因此,随性阅读的时间增加,而有效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从2007年到2010年,网络游戏连续4年销售收入位于数字出版产业前三名,这说明数字出版的娱乐化倾向非常强,网络游戏以及SNS(社会网络服务)等已经成为人们比较喜欢的娱乐消遣方式。
但数字出版不等同于碎片化出版,这不是未来的趋势。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数字出版必然要起到引领主流文化的作用。因此,如何在数字出版过程中避免碎片化,这是决定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传统出版业要加速转型。数字出版已是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今后的出版社必将成为网络内容的提供商,借助传统出版社的编辑优势,为社会提供有系统、有深度的优良文化内容,避免目前的碎片化趋势。
国家已经启动的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等重大数字出版技术研发工程等,都将推动传统出版社的转型。
优秀数字版权保护亟待加强
2009年10月底,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未经许可,在其制作发行的4款汉王电纸书(国学版)产品中收录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史籍,构成侵权,并向海淀法院起诉并索赔400余万元。2010年,百度文库发生数字版权纠纷,一批作家和出版策划机构集体声讨百度文库侵权。
越来越多有关数字版权的纠纷,已经成为阻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另一大问题。传统出版社与作者,对数字出版单位的不信任感在增加,客观上也说明,数字版权已经成为目前数字出版业的症结所在。
美国出版商协会是这样来定义数字版权的保护:“在数字内容交易过程中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技术,工具和处理过程。”而在我们国家,数字版权保护的法律及技术手段都尚处于发展阶段。
《2011年数字出版产业报告》指出:“现阶段,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机制(包括技术手段、授权模式和保护体系等)的建立尚不完善。现有法律适用于数字出版明显滞后,有待进一步修改补充,且版权授权不规范,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和出版社的出版权益都难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有效维护。”
传统意义上的版权属于出版社、出版商、版权代理商等机构以及众多的个人作者,作者将作品交由出版社出版,这样作者与版权在一个时间段里相互脱节。而数字出版单位在进行数字出版时,搞不清楚版权究竟在哪一方。如果作者与出版社订立出版合同没有明确的版权时间约定,便会产生大量的纠纷。
由于新媒体的快速成长,博客等新的传播形式日渐增多,在国外,作者直接与新媒体合作,其收入比例已经和机构合作者持平甚至高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的版权制度也面临着变革需求,需要法律、技术、行政多方面的配合寻找出路。而我国对于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只有2006年由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目前《著作权法》正在修订中,新《著作权法》将会对新形式、新业态下的版权保护给予明确法律规定。
“法平如水”,法的本源是社会的平衡器,是用以平衡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知识产权法肩负着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对创作者利益保护之间平衡关系,无论偏向哪一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毋庸质疑,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免费大餐对于知识的传递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我们每个人都曾享受过它的方便,但当这种免费使用达到严重侵犯版权所有人的利益的时候,会直接打击创作者的热情,造成新的不公平。建立适合数字传播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在保证人类知识财富顺畅传承的同时,也对创作者的利益与积极性给予有效适度的保护,是目前立法者与管理者应解决的首要问题。
(作者单位系经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