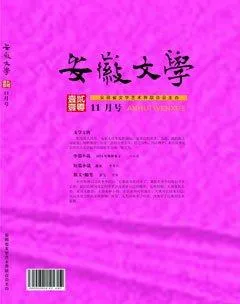口语的天堂
2011-12-29木叶
安徽文学 2011年11期
1976:地震
时隔三十多年了,童年的长天早已清空,难见半丝杂色。我心不在焉地牵着孩子,静静地站在超市门口,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始这段叙述。
1976年我六岁。那时候真的太小了,小到看见进城的路上远远驶来一部邮车或其他的什么汽车,哪怕是手扶拖拉机,都会止不住地激动、兴奋半天!那时当然不知道恶作剧的蚂蚱、收集的卷烟盒、潦草的地震棚,还有住在后院的小女孩,都会具有不可逆转的往事性质!——早知如此,我肯定会多加留意、多看两眼的。
当现在我来叙述儿时天堂般的无邪时,只依稀记得我们是“革委会”的干部子弟。大人们好像经常严肃地开会,会一开往往就要到深夜。我们的肚子饿了,就屏声静气地远远张望。我们闹不明白:难道他们就不饿吗?
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吵,就闹,往往是做“好人坏人”的游戏,并且乐此不疲。当办公的院落不得不对叽喳的麻雀开放时,偶尔也不得不对吵吵闹闹的我们开放。但大人们总会不耐烦,总会在赶麻雀的同时,也将我们驱散。
我现在已无法真切地再现1976年的“革委会”偌大的院落。紧挨着桂花树的,是一棵枝叶并不茂盛的枇杷树。初夏时节,“五一”才过,一粒粒枇杷还青涩地挂在枝头,我们就趁着大人们不注意,爬上树,把它们捋个精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也许并非如此,这棵枇杷树早早地就被伐去了。只是当年在这棵枇杷树下,那个回头冲我一笑,让我乐了半天的邻家小女孩,现在还好吗?她是否偶尔也还会记起“革委会”、记起这棵枇杷树和我吗?
1976年之所以让我记忆深刻,也许是因为那个奇怪的夏天——天空好像不知被谁划开一条豁口,闪电一次又一次地骤现,无休无止的暴雨和急促的喇叭声、喘着粗气的雷声,把孩子和大人们统统赶进了地震棚。可孩子却总不安分,对于地震的恐慌有着先天的无畏:红五,小六子,三宝……我们几个,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下,在水泥做的乒乓球桌底,打打闹闹地度过了一夜的幸福时光。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大人们似乎老是担心这幢坚固的房子随时会垮塌。实际上,建造这幢房子的用料,有多半来自于城东的一座古塔。破“四旧”之后,那些质地非常优良的古塔砖被搬到这里,用作了建筑这排办公室的材料。后来我们从大人们有些神秘又有些暧昧的对话中知道了,在离我们很远的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地震会是什么个样子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晓得“革委会”为此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房门口挂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牌子:“地震办公室”。还晓得后来在电影院门口免费反复地滚播着一场露天电影,电影的名字是:《地震》。
我对“革委会”的记忆也可以远溯到1968年。那时我当然还没出世。大人们在后来一提起那年的“文攻武卫”,就都绘声绘色,好像他们都是亲历者,或者都长了天眼,当时就在旁边冷漠地看了个一清二楚。
“……那天晚上,也就是在‘革委会’院子里,枪声不断……”;“……后来枪声终于稀落下来,‘联总’的人好像要散了……于是他从躲着的办公室窗户里往外看——只这一看,一颗流弹就从此带走了一个人的命……”
这故事就像祥林嫂的阿毛一样,确凿而真实,我因此才能倒背如流。后来我几次走进二楼那间办公室——现在还在被某个机关办公使用着。我会止不住地四下打量,莫非是想找出一两声早已风干的咳嗽?
“革委会”的全称是革命委员会。作为语词,它早已退出了许多人的视线。在它的斜对面是人武部、总工会,当时大人们对它更熟悉的称呼是(“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三代会。再往下走,就到了被改作印刷厂的废弃的天主教堂,和我们在那时无限向往、人山人海的电影院。
“革委会”的那些平房,后来在老城区的拆迁中,被后起的楼房渐渐地替代,已看不出它原来的模样,教堂原址也不再是原先那种古板的欧式建筑模样。
童年依稀的缝隙随着我的成长被渐渐地抹平;那扇儿时的天堂之门,也在时光的倾斜中,逐渐模糊、闭合。
往事:火葬场
多少年了……往往是草长莺飞的三月暮,西山脚下,那突起、古怪的大烟囱,总慢吞吞地吐出灰白的疑云,隔着二郎河发亮的流水,和满田畈涌动的野蔷薇。
我居住在离西山并不远的一个宿舍区里。周末里,有时候我也会带着孩子来到郊外的河滩草地上,放风筝、看看远处的风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的眼睛都会有意无意回避对面那直通通的烟囱,和它底下隐隐约约的建筑。但现在我不能!我不能拒绝父亲已略现佝偻的身影缓慢地浮现在山路的尽头。不!那时他也年轻,神采飞扬,身穿1974年的中山装,有时候也骑自行车来这里看望我的母亲。我母亲1964年被芜湖的一家工厂精简下放,回乡务农;10年后作为家属,成为了这座工地的一名临时工。
根据指示,这儿要修起一座移风易俗的火葬场。
母亲后来又招上了工,离开了火葬场,调进了城里,如今已经光荣退休。这些都符合我父亲朴素的期望。但在当时——无边的夏日里纠缠不休的知了……草腥味的绿色又浓又稠,和满山醒目的、肥硕的松毛虫害,一点一滴,洇开在我懵懂的少年时期,让迷糊的往事,时而有些发傻。特别是有一次,在司炉工诡秘的诱惑下,焚化炉前:我怯怯地注视着乌黑的炉门,心头也闪过一丝寒颤。
后来……混乱的弥散汗气的盛夏之夜,满天的星星疯长,山上的亡灵都已安睡,我却辗转难眠,圆睁双眼。又白又亮的木星旋转着滑过窗前。
1974年的夕阳已经沉落,就像大烟囱里逸出的白烟,终归都要淡去。我母亲曾经亲手为它添过砖瓦的这幢建筑,在西山下默不做声,保持了它应有的冷漠和尊严。我知道,在此刻它不会听见我女儿的笑闹,也不会关心我似有若无的沉思。
在当时,距离火葬场最近、也最显眼的一幢建筑,是国营的砖瓦厂办公楼——很小,很欧式,特别是它旁边的建筑,也有着椭圆形的大屋顶。后来我上了学,从图片上认识了雄伟的北京火车站——几乎是同样的建筑风格。现在它是很破败了,但还在。破败得足以做拍摄“二战”题材的电影背景地。
2003年初夏,在经受了癌症折磨之后,父亲终于走了。我因此有几日是天天守在火葬场。那天,追悼会后,火葬场孤零零地瘫坐在西山脚下,大烟囱突出、生硬、不合时宜,斜插进西山宁静的天光里,就像死亡总是勉强地斜插在贫穷而欢乐的人世,让好心人也终不免沉湎于暮色而目瞪口呆,让我看到三十年的光阴真的是瞬间的风景轮转。
最后,我和大哥一起终于走出了我在童年时代偶然曾进去过的焚化间,手捧簇新的、微热的骨灰盒,站到近前,硬着心肠,安慰我悲痛的母亲:
“……妈妈,今天当班的可就是当年的小冬宝,你瞧,爸爸的骨灰烧得多好,灰白,细碎,安详……”
老汪:知青办
叙述什么呢?叙述我对于知青往事的一知半解?我问老汪。可是老汪打着哈哈,说是孩子来了电话,要他到安庆去居住。
老汪后来去没去安庆,我不太清楚。他已经退了休,就像“知青办”漆色斑驳的木牌,在我们这座忙碌的大楼里已经悄无声息。但那些发黄的表格还在,躺在一格一格的抽屉里,好像早就在等待着像我这样的人来梳理。
不错,正是像我这样。我现在的工作是被告知:去配合着编纂这部续修县志里的相关部分。这好像让我大有作为。领导说。我有些为难,毕竟我太年轻,相对于“知青办”。可老汪就不,老汪三十多岁时,“知青办”才出生,新鲜、热烈,也曾让老汪真心实意地高兴。
老汪后来的半辈子,都是在“知青办”度过的。
闲着的时候,喝茶,翻报纸,老汪偶尔也会和我们谈起上山下乡,谈起那些好看的上海姑娘,她们就住在孚玉山背后,弹山大队的几间土屋里;谈起知青的招工、推荐上大学;谈起午夜热血沸腾的游行,庆祝伟大的最新指示;也谈起知青们的单纯,当然也有的不守规矩,比如为了能招上工,就有一个知青曾经送给了他一套合肥买来的《红楼梦》。老汪其实是很慈眉善目的,说起那些往事,语调不疾不缓,但声音总有些钝浊。
我对于上山下乡那段“知青办”火热、忙碌的往事,并不太分明,也不太热心。我只知道他现在所说的孚玉山,在我的童年里曾被严肃地叫做向阳山。山前是当时新修的烈士陵园,山背后有我几个小学同学的家。经常是端午节后,我们几个会在一起,偷偷溜到蔡家塘游泳。在水里,他们中的一个,曾得意地光着屁股,头顶花糊糊的日头,和我谈起他哥哥的宏伟抱负,那就是希望很快会讨到一个上海知青做老婆。
蔡家塘如今已沉淀为孚玉路——我们这座小城的一条主干道的路基了;我那位有着胸怀大志的哥哥的同学,也已经多少年没有见到了,据说,他已经成了干得不错的一个老板。
唉!多少往事,多少秋声,让我的毛桃、野兔、小铁蟹……又激动又忧伤,在那些二胡般喑哑的月色里。
但现在我正襟危坐在老汪的“知青办”,
看见丝丝缕缕的炊烟,缓缓地升起在绰绰约约的城墙坝后面,秋风粗砺着安抚那些离开了父母、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我忽然眼角有一些湿润。
安庆——老汪退休后要去安度晚年的一座城市,也是他当年为之忙碌的知青们所来去的地方之一。那些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回去了,留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并不再像原先那样的好看;老汪呢?自然也就真的老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不愿意辅导我编写这部续修县志里相关章节的真实原因?
但我还是能够把握当年的“知青办”在后来的一些基本的脉络——从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到劳动服务公司的待业安置,和就业局的劳务输出,忽忽悠悠就到了1998年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
那些后来陆陆续续加挂的,拗口、冗长的匾牌,就像一块块补丁,端端正正地,固定在走廊外防盗门的正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