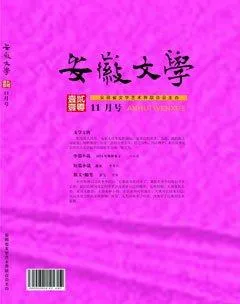剑门蜀道行
2011-12-29张武扬
安徽文学 2011年11期
人人都知蜀道难,而蜀道之行最难最险的,莫过于位于四川北部剑阁县境内的剑门关。这是川陕之间的大剑山中一座闻名遐迩的关隘,也是崎岖蜿蜒的蜀道由北而南进入天府之国的最后一处咽喉要道。这一段惊险穿越在史书上留下无数浓墨重彩的诗篇和文人墨客的华章,也让我们在感觉中抵达它的更深意义的层面。
传说中大剑山原是一条害人的巨蟒,被当地一对兄弟合力征服后杀死,侧身横卧在陕西与四川交界的群山之中,绵延两百余里,中间被砍为七十二段,后来崛起为七十二峰。于是,它就如同一列巨大的屏障,把中原与巴蜀相分隔,这边是秦汉古风,那边是巴山蜀雨。而那个川陕相依千年的著名关隘,就建在苍莽绵亘的大剑山中的一道缝隙之中,这也是蜿蜒数百里崇山峻岭的唯一通道。两侧峭壁悬崖夹峙中的峡谷长约500多米,人行其中受到绝壁的挤压,顿感险象环生。架道立关扼守于此,果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起了这么个很直观的名字——剑门。诸葛亮曾评价道:“大剑至小剑系隘束之路,尤以阁道三十里最险。”剑门关是蜀川锁钥,得与失直接影响政权的存亡。三国时,曹魏三十万大军进犯,蜀将姜维封关固守,仅以三万人马,就拒敌于蜀门之外。于是逼得悍将邓艾率队绕关裹毯滚下摩天岭,暗渡阴平,走江油,下绵竹,历经千难万险,最后才攻陷成都,弄出“当年后主已亡国,此地姜维尚守城”的尴尬来。过去每当读到《三国演义》的这一段,不禁欷嘘不已。身临其境,四下望去,仍能感觉兵戈撞击的铿锵与战马咴嘶的鼎沸。
剑门山是在漫长的地质构造运动中形成的一种巨厚砾岩,专家称之“城墙岩群”。这种岩层不长草也不生树,蹈厉起伏的线条与赤诚的袒露,使高耸的危岩远远看去险如其名,峻峭挺拔的群峰如城墙似峰堞。它的险峻与巍峨,客观上形成一种繁复的美,层层推进,洋洋洒洒,无边无际,使它变得格外扑朔迷离和不可捉摸。人人都知蜀道是条古道,但是,蜀道剑门到底开凿于哪个朝代,似乎在史书上也没有明确答案。最早将它连接成路的,传说是公元前300多年的武丁开道,到了楚汉相争时樊哙暗修栈道,虽是兵家计谋,但在客观上提高了古道的通行能力。使它成名的记载,应算三国时期诸葛亮筑阁,剔除所有不必要的细枝末节,史书上剩下来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文字。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迂回奇袭的冲锋号,吹乱了凭关固守的敌人军心,攻克了长征路上这个天险。时间裹挟着脚步和车轮,水一般从这里穿过。现在已通车的川陕高速公路,使过去悬挂在丛山峻岭中的蚕丛小道成了通达坦途。
蜀道主要不是为了旅行而是为战争而诞生的,包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古蜀道基础上改建的川陕公路,也是为了适应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的需要。与它相连的都是历史文化遗迹,无论是诸葛亮练兵的演武场,还是张飞夜战马超的战胜坝;无论是庞统以身殉职的落凤坡,还是姜维拼死拒敌的剑门关;无论是李白以手抚膺放声“剑阁峥嵘而崔嵬”的吟诗处,还是唐明皇得内乱被平的应梦台……史书上简略的记载,在这里都生动地展现出来,如珍珠般散落山谷中、栈道上。当然,最多的还是三国遗迹,如古关楼、武侯桥、武侯坡、插旗石、点将台、营盘嘴、钟会故垒、姜维神像、阿斗柏、张飞井、书箱洞、孔明杖、关刀石、邓艾墓、姜维墓、姜维祠、喂马槽等等,当你身临其境时,它们全都风姿绰约地活跃起来。少年时,我读《三国演义》,印象深刻的是诸葛亮率兵攻祁山,与刊马懿对峙之际,因粮草皆在剑阁,靠人力搬运极为不便。于是,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往来搬运粮草,自剑阁直抵祁山大寨,解决了蜀军后勤保障问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假如没有作为秦蜀交通咽喉的这段天险,就不会有这么多征战天险的英雄,割断了来龙去脉的片断,或许历史也会改写。因为,英雄向来是被历史表达的。
时光带走一切,带不走的是光照日月的文字。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无以计数的以剑门蜀道为题的诗词歌咏和著作文章,绵延着他们身后的时空。其中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剑门》、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些俯首可拾的传世名作,历史地根植于剑门蜀道的高山峡谷中,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高龄。它们是剑门蜀道培育出来的,也深知其性格与情感,于是毫不吝啬地扎根于此,在剑门蜀道的风风雨雨中又成为它的基本元素,被一代代传颂着。还有许许多多后来者的吟唱,那些沾染了剑门蜀道雄浑的字纸,涌动着诗意的灵性,在我们的眼前、耳边纯厚而绵长地闪耀着、波动着,于是本来是空野的山谷,在情感与心绪交相辉映的过程中就有了新的生命与价值!
途经跨溪的一座小桥,在灿烂的午后,莽崖野岭一派葱郁。千年逝去,当年千军万马的踪迹全无。隔着山谷,能看见盘绕在山巉岩绝壁上的栈道,尽管岩缝间的部分栈道被野藤山箐遮掩,时而仍能露出栈道上游人衣服鲜亮的色彩,美丽的质感愈加透出难言的魅力。此刻我们伫立的地方,或许就是当年诸葛亮、李白们停留的地方。再心高气傲的人,也不敢用睥睨或不屑的神情来面对。表面是视觉上的感受,其实内心不由地升腾起敬畏或惊叹,剑门蜀道就是如此神奇,能把崎岖变成雄伟,把瞬间变成永恒。远古的花,飘过时间的浩瀚天空,落在涧谷深处,那里通向的是三国蜀汉大军安营扎寨的危岩栈道,还是唐明皇避安史之乱入川逃生的悬崖小路?陡峭、雄奇、高蹈、执拗总是古诗的韵脚与注释。杜甫携家眷从秦州转徙成都,途经剑门时惊叹于地势之险要,其描述使人如临其境:“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白居易年老体弱,拄一根藤杖,在剑门的崎岖山路行走得十分艰难:“梓州二千里,剑门五六月。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栈热。何言巾上泪,乃是肠中血。”这些诗句的线条简洁清晰,直与自己的内心平行,挥洒眼中的剑门奇崛艰险。而陆游卸下疲惫与沉重,在剑门山中则行走得潇洒多了:“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细雨骑驴入剑门。”在变更的生活中,性情中倔强、兀傲的部分不再坚持了,迸发出来的都是随性真情,由语言搭建起来的精神关隘,铺设在通向现实之外的路途上,连树叶落下的声音都显得壮怀激烈。
就这么循道而行,左一脚李白,右一脚杜甫,深深浅浅的印迹带我们走到剑门关关楼。只见它雄踞关口,冷峭而恢弘,曾让多少后来者灵魂起舞,尽情释放尽情演绎。听当地朋友介绍,当年蜀相诸葛亮经剑门六出祁山,北伐中原,见此处壁高千仞,谷深树茂,便在此依崖垒石,建关设尉,并修阁道三十里,始称“剑阁”。斑驳而沧桑的剑门关关楼虽历经多次战火,却屡毁屡建,雄风依然。现在的关楼是三层木石结构的仿古建筑,底层以青石条错缝筑成,四面成墙,坚不可摧。在关楼上左右仰视,四周的七十二峰悄然围了过来,似仗剑持
戟的武士,倏然间造型动作凝固了,山风吹过的深谷里仿佛只留下呼啸的怒吼、奔腾的蹄音,峰峦深处躁动着一腔刚烈。想当年历代踞关兵将,一声怒吼,滚木擂石,轰隆齐下,让攻关者人仰马翻。此刻俯瞰楼下弯弯的山道,像一条长蛇在山间盘旋,一会儿游弋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一会儿又钻入深不可测的山谷中,金戈铁马的厮杀湮没在峡谷深深的皱褶中。四下鸟声啁啾,溪水湍流,安宁的关楼,看不出当年箭矢如蝗、刀剑相击的场景,重修的关楼仅仅是供后人凭吊的历史遗痕。静下来倾听风的轻语,似乎从剑门镇方向,隐约传来被空间距离减弱了的躁动、喘息、呓语、喊叫的嘈杂混合。那边是现实,而这边已是历史。
关楼的陈列室内有不少珍贵的文物古迹,内间壁上有清代果毅亲王允礼书题诗句:“谁携天外芙蓉锷,高挥层霄见太空。阁道摩空星斗近,仙风吹入玉屏行。”这里还陈列有历代书法家书写的著名诗文,如张载的《剑阁铭》、柳宗元的《剑门铭》等,读书识人,我们欣赏的不是真草隶篆的妙处,而是感受到那种苍劲与雄浑,当在剑门关上被它们再次照拂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拉入久远的岁月深处。古人的心事似乎比今人的要简单,但是往往会达到极致,那些诗句都有响声,有弹性,弥散着神秘而久远的吸引力。凭栏野望,关山重重,巍巍乎赫然在目,正如楼阁上楹联所言:“蜀道关头险,剑门天下雄”,联想一路所见“天下雄关”、“第一关”、“剑阁七十二峰”等碑刻,藻思绮语,思绪纷来,人在徐徐的清风中淡定下来,只觉得许多似曾相识的古人在关下依依不舍,挥手作别。其中的曲折幽微,缠绵绕骨,不可尽言,看不见的记忆的岩层深处,收藏着、沉积着的是层层叠叠的目光。
过了剑门关,险处不须看。我们的车从剑门镇去广元,一路所行高速公路,大多已经撇开古蜀道的路径,穿山越岭另辟坦途。但是,它曾经碾过时间走过的足迹,是从古蜀道脱胎而来的。从远古时期的羊肠小道,到官家驿道,再到川陕公路,直到如今的高速公路,游移在奇峭峻岭间的古蜀道功能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变,成为旅游的重要景观。时光的大书翻过的不是一页,而且整整的一章。然而,在历史的分水岭上,苍莽剑门关依然坚守着它的千古雄风,正默默地向游客们述说着世间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