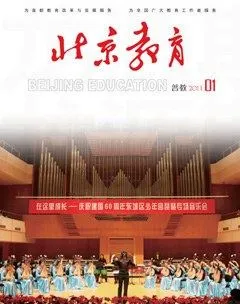中学学术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1-12-29邰亚臣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1年1期
编者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邰亚臣,1994年来到北京市第十五中学任教,2002年-2004年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自2006年任十五中学校长以来,他十分注重学校的文化建设,努力构建具有文学气质、有生命意义的学校文化生活,从而激发了学校的活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校文化。
邰校长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从他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教育理想与情怀;从他那诗意的表达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现实教育的冷静与沉思。
请走进邰亚臣校长关于“中学学术建设”的系列思考,一同分享他的教育思想吧……
今日在中学谈论学术建设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有对现在教师工作的否定之义,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在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像漂泊不定的一叶孤舟,多少有些悲壮的色彩。 中学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虽然每年有大量的研究文章产出,这个数字极其惊人,但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学学术建设极度缺乏学术精神,低水平重复建设比比皆是。
在中学进行学术研究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基础的教学任务已属难得,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坦率地讲,目前中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很大,确实承载不了过高的要求。但在现有的教师工作评价体系下,文章又是刚性指标之一,所以每位教师又被迫开展著文立说的工作。当然,即便是被动完成任务,很多教师还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思考。但不可否认,总体研究质量低下,有学术精神的文字寥寥无几。
中学学术水平现状
以下事实能够充分证明中学学术水平的现状。
文章极度缺乏说理思维
之所以说中学的学术研究处在低水平重复建设阶段,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我们大部分文章缺乏说理思维。在美国,小学六年级就开始特别强调公共说理的重要意义。重点内容在于区分“事实”和“想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备自动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才获得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想法必须加以证明,提供理由。四种常见的理由是: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
先不去比较学生之间的差别,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们所写的文章,我们都应感到羞愧。我们那些所谓的论点,大部分没有经过有效的论证,我们的那么多结论缺乏有效的数据和例证支撑。
学术的生命在于求真,或者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要有“较真”的劲儿,无论是文章还是教育行为,至少要言之有据,然后展开层层的推演,最后扣上主题。或者说要有统一的标准,要有根本的思考原则。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不少中国学者,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可以那样说。所以如果我跟着中国学者写我的书,那我就完蛋了。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错的,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我们有。”因此,学术研究重要的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是要有思考问题的程序,要有说理的思维贯穿,要有完整的逻辑结构。以这个标准来看,不要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教学都存在极大的问题。
纯正趣味的荒芜
我们并不缺乏研究,缺乏的是真正发自兴趣的思考。今天我们写的文章,日渐演变成了写作者和出版单位以及读者都心知肚明的行为艺术。大量重复的文章被不断地发行,同时伴随的是无人阅读的尴尬。因为很多文章,或者说绝大多数文章,连作者本人都不愿意去看,难道这不说明其学术研究水平很差吗?要么是经验总结,要么是概念的集合,要么是不知所云,要么就是正确的废话,比如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种现状表明:我们确实获得了一些功利的成果,但好像没有收获快乐。因为这并不是纯正兴趣带来的东西,也就推不开我们精神世界的门。
所谓纯正的兴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兴趣发自内心,或者是被引导和激发出来的,而不应是被导演,更不是从别人观点复制出来的。在信息比较闭塞的大学年代,某大学几个学生获悉图书馆里藏着不少所谓色情的禁书,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检索系统,考据和查找资料已经是个难题,而且这些书并不外借,到书库里找到它们就成了一个更难的题目。但在“性趣”的驱使下,他们努力钻研,潜心思考,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书籍并做了细致的摘抄。后来被老师发现,除了尴尬和窘迫,他们也有一个重大收获:在考证典籍上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由“性趣”到纯正趣味的转变。
王小波曾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这句感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现实是只有极少数人去做有趣的事儿,有更多的人去开创无趣的庄严事业。”
但今天我们的研究和思考,受到的干扰和影响无以复加,在这个现实情况下,无趣的庄严事业必定带给我们现实的、“明码标价”的成果。但回望历史,依然给我们以寻找趣味的勇气。上世纪20年代的南开中学,在学业传授上,老师经常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课本,没有成见,没有现成的框架和整齐划一的答案。学校自编的国文课本,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作品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后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也“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的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环境里,纯正的兴趣才有生存的土壤。
大而空的研究课题
前面说过,因为我们写了太多的经验总结和堆砌概念的文字,所以我们没有变得深刻,但这毕竟还属于前研究阶段,属于求真的必经之路。最应该让我们保持警惕的是我们写了太多的大而空的文章,类似于“阅读策略”、“课改的意义”、“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翻开我们的文章目录,我们很难见到小而精的题目。试想如果一个人为了快速获得成果或者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就肯定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更不要说耐心读书了,这样也就不能透过事物的表层而去看到更细致、更精微的存在。而讨巧的大题目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
原因探析
造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很复杂,但我认为从根本上和以下两个问题相关。
轻学重术的氛围
从根本上说,中学学术水平的低下是中学教师学术上的不自信导致,骨子里认为研究是大学的事情,基础教育就是要做和基础有关的事情——完成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送孩子们去读大学。其实,学术的核心思想是思考,如果把思考的机会拱手相让,那么,我们就会安于学术的初级阶段而不思进取,停止思考就会带来大面积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要么是经验总结,要么是概念的集合,要么是不知所云的文字,表现较好的,也是把研究的问题大多集中在方法和技巧上,而不去触及学科的深层次问题。
当然,这种研究的风格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媒体强势笼罩效应,让学术安静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百家讲坛式的风格得到了社会的追捧,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噱头经常性出现。当然,从文化普及的角度来看,传媒的发达加速了知识的传播速度,但如果教师定力不够,就非常容易造成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的轻浮学术之风,追逐方法和技巧而不去静静培养学术情感。真正的学术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其实我们在教育实践当中都有这样的体会,要做到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除了教法的新颖有趣外,更需要教师对自己所授学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依据本学科知识的特征,设计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案。又或者也许根本没有什么设计,却在举手投足间焕发出长期的学术修炼养成的奇异光彩,这对学生的影响已超出单纯的知识之外,而具有精神的力量了。
古典阅读精神的消亡
也许这么表达过于绝对,如果是杞人忧天再好不过,但现实是我们离美好的阅读越来越远。小黄灯、书桌旁,红袖添香肯定是昨天的事情了,但阅读的古典精神带给我们的快乐是跨越时空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跨过今天。有人充满警醒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时间的设备层出不穷,多到没有时间——使用。由于微博、iPhone、iPad、电子书等上百种随时随地转移注意力的设备,无聊终于放松了它对我们的控制。无聊消亡了,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创造力。当一个人思考问题时,键盘和触摸屏取代了想入非非。由于无聊消失了,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思考问题。我们成功杀死的不是无聊,而是时间,我们不再觉得无聊,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注意力永远像弹子球一样乱窜,通过超链接、搜索等方式无穷尽地跳跃下去,形成一个永无止尽的时间黑洞。以前你坐下来,没有多少可以打扰你的东西。你可以坐在那里工作或仅仅是坐在那里。但现在,你一旦坐下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许多事情还通过某种隐晦的联系与工作相关联,让你无法舍弃。我们就像不停按动电门寻找刺激的猴子,沉溺于克服无聊过程的本身,但这个过程在其他人看来是无聊更甚。已经不止一个朋友抱怨,见面时大家低头看手机的时间超过了交流的时间。”
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对生命的理解总会比别人多一些层面,更为精细,更为通达。有学者说:即或是流行小说,有时也会令读者灵光一闪,倘若由此起步,再上层楼,有一天在下水道里也能被黑格尔照亮。
正是因为我们被吸引眼球的信息和噱头不断训练,我们习惯了跳跃式的阅读方式,我们蜻蜓点水式的阅读轻功由此练成,但习惯了跳跃就会失去耐心去关注细致的描写和密密麻麻的数据,一层一层的分析就会让人生厌。其实,我们在理智上可能都知道,趣味、想象力以及微妙的智慧往往就在那些跳过去的地方。因为内力不够,所以就失去了判断力。让我们看看现在有多少伪书大行其道,《没有任何借口》、《加西亚的信》、《执行力》等等,甚至包括《细节决定成败》,我认为都没给过我们什么真正的营养。我们喝了太多心灵鸡汤的文字,这些不但没有让我们变得深刻和优雅起来,相反却使我们越来越浅薄。
不仅仅是我们的阅读习惯,可怕的是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大量充斥的是讲座的堆砌,大部分是概论、通论、原理、心得和浅说,严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掌握。知识就像一块巨大的七巧板,你绝对不能仅仅凭借几块就想恢复原来的样子。真正的阅读首先是接触好书,所谓好书当然是具有学术精神的作品,在现代学术史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代表,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伟大的著作,因为这是真正通过实地考察得到的东西。学术必须具有求真求实的精神,这是学术的灵魂。当年费先生和妻子在广西瑶乡考察,结果迷路出现事故,造成费先生受伤和其妻的死亡,如果是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他绝不敢在书的扉页上写: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也就不会有国外著名学者写下这样的评语: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编辑 王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