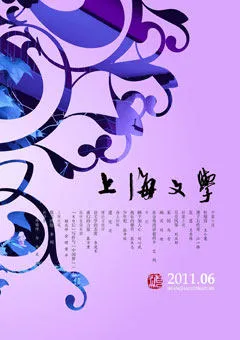散文两题
2011-12-29李娟
上海文学 2011年6期
随处明灭的完美
整个上午就只有我一人在家,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独自摇动嗡嗡作响的分离机。脱脂了满满两大桶牛奶之后,我洗净了器具,收拾完房间,裹紧大衣倒在花毡上深深睡了一觉。醒来时,一束光斑静静地打在身边的花毡上,像追影灯,笼罩着孤独的演出。被笼罩着的几行彩色针脚做梦一样地发着光,而四周空气幽凉阴暗。
毡房门外却阳光灿烂,不知雨停了多久。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裂开的云块大朵大朵地移动在高处,头顶上方有一大片干净的蓝天。木架子上晾的奶酪块一连几天都被蒙在塑料布下,此时塑料布已掀开了,奶酪一块一块新新鲜鲜地敞在明亮清晰的空气里,似乎还在喷吐奶香。
这时,有人骑着马从北面山谷的树林里缓缓上来了。
他笔直地向山顶上我们的家走来,边走边看着我。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自从到了吾赛,家里还从没来过客人呢。但此刻家里没有人,我又不认识他,便犹豫着要不要为他准备茶水。
那人走到近前下马,却并不系马,牵着马向我问好。这人看来是会说几句汉语的,他自称是杜热那边的牧民。
杜热离阿克哈拉很近,也在乌伦克河流域的戈壁滩上,我的妈妈就在那边种葵花。那里有连绵万亩的向日葵地。此时那里的大地一定金光灿烂,激情正酣。
我回答了一声:“哦。”却不知该再说些什么好,只能告诉他家里没人。本来还想问他有什么事情,但又觉得这样有些无礼。
不过看他的样子大约也没有什么事情。
后来我终于鼓足勇气说:“喝茶吧?”但他立刻辞谢了。他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似乎也在思量该和我说些什么好。他的马轻轻地啃着地上的短草,不时地左右晃着脑袋。过了一小会儿,他开口了,简要地告诉了我吾塞的北面和西面一带毡房的分布情况,最后还取出他的身份证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是漂亮挺括的新一代身份证呢,怪不得那么珍惜地包在塑料袋里,揣在怀里最深处。新身份证刚发放不久,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使用,我用的也是旧证呢。
他的身份证上清楚地印着汉字名“思太儿罕”,不到四十岁。
我看了连忙说:“真好!”想了想又说:“照片拍得好。”比他本人白多了。
然后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在放羊。原来只是路过吾塞啊,还以为是特意拜访呢。
和一般牧民不同的是,他不但使用着新身份证,穿的也干净整齐,有棱有角,衣服上没一个挂坏的洞,脚上踏着的军用大头靴看起来还很新。这身装束别说用来上门作客了,用来结婚都毫不为过。只是穿出来放羊的话未免太可惜。不过,那也只是我的想法。再想想,卡西兴致好的时候,不是也总爱往头发上浇满炒菜的油,梳得一丝不苟,再出门放羊吗?
这时,他又说话了:“姑娘,什么时候去我家喝茶吧!”
我很高兴,连忙说:“好啊好啊。”又问:“你的房子远吗?”
他指了指西北面方向,那里隔着阔大的峡谷有一座高高的山峰,高得山顶上都不生树木了。他说:“在那个石头山后面,只有五公里。”
我一下子就很喜欢这个人了。他是善良的。我猜想他放羊路过吾塞时,突然想起早就听说这里住着一个汉族姑娘,许多人都认识她,自己却从未见过,应该前来打个招呼,便勒转缰绳,充满好奇和希望地过来了。这个人是纯洁而寂寞的。
正想再问问他的家庭情况,好好聊一聊呢,这时突然又洒起了雨点。抬头一看,不知何时上方压过来好大一块深色云。我连忙跑到架子边把掀开的塑料布重新拉拢,盖住奶酪块,然后又跑到毡房边扯着羊毛绳,把毡盖拉下来盖住天窗。正干着这些事,雨水中又夹着冰雹急速地砸了下来,从烟囱旁边的破洞啪啪啪地撒进毡房。这时扎克拜妈妈也回来了,她一踏进毡房就看到卡西扔在花毡上的外套,便大声埋怨起来。天气变幻不定,忽冷忽热的,出门放羊还穿得那么少,真是臭美啊。
这时,我才发现思太儿罕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
我对妈妈说刚来了一个叫思太儿罕的客人,她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这个思太儿罕是谁。我形容道:“脸是黑的,牙是白的!”令妈妈大笑了起来。
我边想着思太儿罕的事,边生炉子烧茶。没带厚外套的卡西和感冒很久的斯马胡力一直都没回家,有些担心。又想到思太儿罕,他此时正衣着整齐地冒雨策马慢慢穿行在重重森林之中。那人笑起来的样子,温柔小心得像独自横渡宽阔河流的黑眼睛鼠兔。
喝完这道滚烫舒畅的奶茶,正在收拾茶碗,扎克拜妈妈却叫我放下,先跟她一起去爷爷家。去爷爷家能干什么呢?无非还是喝茶。为表示额外的招待,沙拉打开加了锁的木箱,取出一些平时不吃的糖果饼干撒在餐布上的馕块间。
外面雨不停地下着,木屋阴暗,炉火旺盛。十岁的男孩吾纳孜艾蹲在火炉边,专心地用一根烧红的粗铁丝在一块小木片上钻孔,钻一会儿,铁丝凉了,就插进炉火里重新烧红。他一共做了两块这样的小木片,忙得不亦乐乎,连今天餐布上出现的平时难得吃到的好糖果都吸引不了他。小加依娜紧挨着他蹲在一旁,无限期待地盯着他手中的活计,激动而耐心。我好奇地看了好一会儿,才知做的是一辆独轮手推车的小模型,准备送给加依娜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忍不住无聊地问道:“能拉柴禾吗?”没人理我。对于郑重地做着这件事的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小玩意能否派得上用场,而是它的确和真正的独轮车一模一样!
这时,拖海爷爷回来了,他持着一根系着一截羊毛绳的长枝条弯腰进门。正干得热火朝天的吾纳孜艾连忙放下活计,起身去拿水壶给爷爷浇着水洗手。沙拉赶紧冲茶,扎克拜妈妈让座。爷爷入座后,吾纳孜艾也跟着入座,陪着一起喝起茶来。但他惦记着独轮车,只匆匆吃了一碗就离席继续烧他的铁丝去了。兄妹俩面对面蹲在泥地上,不时小声讨论着什么。炉火投到吾纳孜艾年轻光洁的面孔上,他的眼睛里有更明亮的火。
餐布正中放着一碟新鲜柔软的“阿克热木切克”(酵化的全脂牛奶制成的奶酪),但和扎克拜妈妈所制作的大不一样——嚼起来没什么奶味,倒有沉重的豆腐味儿。爷爷很喜欢吃这种热木切克,他掰碎了泡进茶水里用勺子舀着吃,边吃边愉快地哼着歌儿。
小猫进了房子,身子湿漉漉地偎了过来。沙拉也给它掰了一小块热木切克。小猫趴在那里细致用心啃啊啃啊,小口小口地,半天才啃完。然后抹抹脸,舔舔爪子,优雅地向炉子后的土堆里一拱就睡觉了。前两天这只猫的右边耳朵不知在哪里蹭光了毛,秃秃的,今天另一只耳朵居然也没毛了,一边各露一团粉红色的光皮肤。
这道茶很快结束了,我收拾碗筷,爷爷躺下休息,扎克拜妈妈和沙拉并肩坐在木榻沿上捻起线来,各使各的纺锤。纺锤在炉光映照中飞快地旋转,蒙着塑料布的小方窗投进来一小团毛茸茸的亮光,妈妈和沙拉粗糙的面容却有着精致的侧面线条。火炉边,兄妹俩的独轮车雏形初现,车轮居然是我扔弃的一只药瓶盖子。
这时扎克拜妈妈和沙拉又聊了些苏乎拉的事。两人为传说中苏乎拉的行为反复地震惊、叹息。爷爷睡得非常香甜。大白狗站在门外的雨中,探头进来久久地瞅着木屋里的人们,很久都一动不动。
我又坐了一会,雨渐渐小了,便悄悄起身出去,站在门边的雨地里,先看了一会儿大白狗,再沿着北边的斜坡往下面的松树林走去。林子虽不密,但挡去了一大部分雨势。大都是纤细的幼林,少见粗壮的大树,并且其间树木几乎死去了一半。活着的树是笔直的,死去的树是弯斜的,树身还铺满毛茸茸的苔藓。死树们划出一道又一道弯弧穿插在笔直的林子里。林间青草叶片和林外的草地叶片不一样,很少有针状长叶,大都是掌状的。成片的毛茛淡微微地开着碎花。走着走着,渐渐靠近了一小块林间空地,那里的草地上隆起一团一团的草堆,一踩进去就是一坑水,非常潮湿。这片地方因为植物单一而显得整齐纯净,也不知是什么植物,密密地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圆形叶片。雨还在下,但云薄的地方已经裂出了阳光。这时正好有一束阳光从云隙投打进这一小块空地上,雾气濛濛的森林从四面八方围裹着这一小片阳光之地,激动地俯视着它。我在这块空地上的阳光里站了一会儿,直到这阳光渐渐收敛了回去。
穿过空地进入林子继续往下走,渐渐听到河水的哗哗声。很快树林稀疏起来,眼前出现了开阔的山底谷地。站在林子边,下方好大一片葱翠娇嫩的沼泽地,中间至西向东流淌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河,流速很急。我们的骆驼正站在远远的水边饮水。我沿着树林边缘继续往西走,路很窄,依稀难辨。路边白色的野菊花和黄色的虞美人在雨幕中轻轻摇摆。一抬头,对面山坡上好大一幅被雨水渍湿的草滩从半山腰一路拖到山谷底端,像滚落谷底的一卷布匹,一路舒展开去,整齐平直,色泽深暗沉重。这样的深绿和下面沼泽地的清茸之绿撞合到一起,整条寂静的山谷都充满惊叹。面对山谷站着,左边世界的雨越下越大,这一侧天空黑压压的。而右边世界却越渐渐开始放晴了,几缕阳光从云隙间淡淡地投向那边的山顶。
雨一小片一小片地下着,雨幕在开阔的山谷间一团一团移动,巨大的金色光斑也在对面山坡上移动。在这阴沉不定的世界中,那块光斑像是从天上投下来的探照灯,光斑笼罩之处有两三匹马正缓缓吃草。
出来很长时间了,我开始向家走去,但又不愿走回头路,便侧身往西南方向爬坡。路越走越陡,走得头发晕。奇怪,就这样慢悠悠地走居然也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知是海拔的原因还是我穿得太厚了。
走了好半天都没穿过这片林子,于是改变方向,横穿林子向西走去,一直走到两山夹隙间的林子边缘,再折回南面沿着林子往山上爬。这边倒是有一条布满牛蹄印的山路,但却从没走过。以前出门似乎从没经过这么一条逼仄的山谷,而且回家之路会必经半山腰上的一大块墙壁般平整的巨大白色山石。但走了半天,怎么也没看到那块白石头,只有脚下的路蜿蜒不止,没完没了地向上方延伸。难道迷路了?不可能吧,就这么一座山,来来去去一直在绕着它走,怎么会迷路呢?路很陡,越走越气紧,休息了一两回后,铁了心继续往上爬。虽然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了,越来越能肯定这条路真的有问题。然而,正打算放弃的时候,路一拐弯,视野突然大打而开,一眼看到两块大石头间开阔倾斜的绿地,及绿地上我们牲畜吃盐的木槽——呀!居然这就到家了!这是条什么路啊?为什么从林海孤岛往下看时,一点儿也发现不了它呢?
又紧走几步,再一拐弯,看到上方的远处,杰约得别克披着海拉提的绿色外套,正倒在爷爷怀里睡觉。
下着雨,风那么大,那么冷,可这祖孙俩毫无知觉一般坦曝在风雨中,依偎在山坡倾斜的草地上。在另一个方向的不远处,盐槽空空地横摆在草丛里,被雨水淋湿透了。继续往上走,更靠近一些的时候,听到爷爷正哼着歌,赶羊的柳条棍放在一边,他的肩膀上湿了一大片,正他柔情蜜意地抚摸着杰约得别克短短的黄色头发和他瘦小的肩膀。待一直走到近前,才看清了幸福的杰约得别克,看到他脸颊上和额头上的温柔雀斑。他并没有睡着,正睁着眼睛宁静地注视着我的缓缓靠近。就算没有爸爸妈妈,年轻的面孔上也毫无阴影。
“杰约得”是“路”的意思,“别克”是个普通的后缀。是否他和保拉提家的阿依若兰一样,也是在转场路上出生的孩子呢……
还是这一天的黄昏,奶挤完了,小哥哥系牛,弟弟在林子里玩球,加依娜在山顶荡秋千。雨还在下,这个女孩一个人在雨中孤独地荡着,荡得那么高,一来一去地穿梭在崇山峻岭间。再回头看去,沙拉提着满满两桶洁白的乳汁,从夕阳横扫处的大树边经过(这边还下着雨呢,那边的夕阳却平静而明朗),她身后是苍茫阴沉的远山。而她身穿红衣,多么美好。
汽车的事
哪怕在深山老林里,汽车也一天天渐渐多了起来。能通汽车的那条石头路将深山里最繁华的几个商业点联结在一条线上。从阿拉善到沙依横布拉克再到桥头,蜿蜒盘旋在深山里。出了桥头又往南延伸了几十公里尘土飞扬的烂土路直抵可可托海。到了可可托海,就有像样的公路去往县城了。另外,桥头西边还有一条石头路,弯弯曲曲插进库委牧场,再沿着前山绵延无边的丘陵戈壁地带通往喀吾图小镇。无论从哪条路进城,都得走两百多公里。
想要进城的人总是一大早就出发,骑马穿过重重大山,去到石头路边等车。于是,不到半天,“某公里处某人要进城”的消息就在这条路的上上下下传播开来。于是司机就赶往那边接人。等凑够了一车人,就跑一趟县城。
还在前几年,除了拉木头和贩牛羊的卡车外,这山里就只有那种啥证都没办过的军绿色北京吉普,也就是“黑车”。这些车结实得就像脸皮最厚的人,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连台阶都能爬,还可以当飞机使,哪怕开到四面窗玻璃和前后车灯全都不剩,开到拧根铁丝才能关紧车门,开到只剩一个方向盘和四只轮子——也不会轻易下岗。由于这样的车会吓到城里人,因此从不敢上正规公路,只在深山里和闭塞村庄的土路(由于是黑车专用的路,又称“黑路”)上运营,零零碎碎捡些乘客。它们一般只能将人送到桥头,胆子大的敢送到可可托海。一个个生意还相当不错。若是运气不好坏在了路上,司机和乘客就一起高高兴兴地商量着修理,你出一个主意,我出一个主意。女人们则解开包裹,把餐布往草地上一铺,切开馕块,掏出铝水壶,边欣赏大家修车,边悠闲地野餐。
那种车全都工作半年休息半年,大雪封山前往山口桥头的雪窝子里一藏一个冬天。春天雪化完了,推出来捣腾捣腾,加上油就出发揽活儿了。
不过这几年牧区管理严格起来了,在山野里,无论路况还是车况都大大整顿了一番。因此,一路上看到的车都有鼻子有眼的,可靠多了。
但一些司机们却还是过去的德性,不喝醉了绝不上路,右手握方向盘,左手握酒瓶子,一路高歌。那些迎面过来的车若不认识也罢了,若是认识,定然会各自熄火下车,大力握手,热烈寒暄。再掏出啤酒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然而乘客们却和过去大不相同,也开始要求效率了。于是等他们刚喝完一瓶,大家就开始催。喝完第二瓶,大家就有些脾气了。于是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告别,死不情愿地上路。
我从沙依横布拉克搭车去富蕴县,倒没遇上酒鬼司机,却遇上一个臭美的司机,开车时双肘撑在方向盘上,一手持小镜子,一手持小梳子,仔细地梳头,只有到了拐弯的地方,才腾出一只手去转方向盘。他的头发明明很短,有什么可梳的啊,还梳个没完。
斯马胡力也是这样,骑马的时候,骑着骑着,就会突然摸出一把梳子梳啊梳啊。而周围只有峡谷和河流,又没有漂亮姑娘。
对了,乡里开大会时,领导发言前也会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摆弄两下头发,然后才清清嗓子说话。
不过在同一件事上,所有的司机都显得很地道。当路面上有转场的羊群经过时,无论再赶时间也会放慢速度一点一点耐心地经过。有时索性停下来,等牲畜过完了才上路。他们尽量不按喇叭,若惊散了牛羊,会令赶羊的人不好收拾局面。
但牲畜哪里能明白司机的善意呢?有一次我们迎面遇上了马群,没驯骑过的小马容易受惊,看到有车过来,不分青红皂白扭头就跑。车开始还缓缓开着,希望马儿会转身绕过自己赶上马群。但那几个笨蛋笨死了,车一停,自己也停下来一动不动;车一开,也撒腿往前跑,以为跑快一点就能把车甩掉。于是离马群越来越远了,弄得它们自己也越来越惊慌。牧马人气坏了,沿着路边的树林策马狂奔,围追阻截,大喊大叫。
于是我们的车就停停走走,耐心地等待着那几匹笨马的悔悟。好半天工夫,它们才被牧马人集中起来,掉头绕过车向北踏入正轨。虽然耽搁了不少时间,但司机一点抱怨的意思都没有。
要是汉族司机的话才不管那么多,一看到羊群就拚命按喇叭,把它们哄散开去,生怕撞死了被索赔,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到牧人的管理。
我想,其中的差异并非在于有没有更细心的“关爱”。由于深知,才会尊重。当他们在羊群的浪潮中停车、熄火,耐心等待羊群缓慢经过自己……那是在向本民族古老的传统生产方式致敬。
另外,我发现,当汽车经过穆斯林墓地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哈族司机——不管是严肃踏实、爱听阿肯弹唱的中年人,还是染了红毛、整天沉浸在震天吼的摇滚音乐中的小青年——都会郑重地闭掉音乐,等完全经过墓地后才重新打开。关掉又打开,也就几十秒时间,我从没见过一次被含糊过去的。敬重先人,敬畏灵魂的话,心灵的洪水再怎么肆虐也不会决堤。嗯,最可怕的不是凶猛的人或愚昧的人,而是无所顾忌的人。
既然是“石头路”,那么这条路就全是石头铺成的了。结实倒结实,就是高低不平,满处大坑小坑。坐车走这种路颠得啊,简直比骑马还颠。身体在车厢里甩来撞去,浑身大大小小的裂缝儿。偏司机们都热爱音乐,音响总是开到最高音量,还总调成重低音模式。这样的音乐配这样的路,真搭。久了,心跳也跟着搭了起来。我哀求道:“我晕车,我要吐。还是调成正常效果吧?”那个年轻司机非常同情地调整一番,于是音响里那位唱歌的家伙一下子离我远了十来步。我长舒一口气,但没过两分钟,他又装作换歌的样子,悄悄恢复了重低音。还以为我察觉不到呢,真可爱。
有的司机极没人情味,一上车,先板着脸开价,并摆出一分钱不让的架势。但价钱一谈定,就变了个脸乐呵呵地向我问好,向我妈问好,还向外婆问好。我大吃一惊:“你认得我?”他提醒道:“今年你们过汉族年(我们这里把春节叫做“汉族年”,古尔邦节叫“民族年”),我还去拜了年呢!”
于是我一下想起来了。今年过年时,的确有一大帮子酒鬼大年初一早上就醉醺醺上门来讨酒喝。因为阿克哈拉只有我们一家汉族,还以为不会有人来拜年呢,就没怎么准备。冷不防涌进屋子一大帮人,七嘴八舌地嚷嚷:“过年好!过年好!”害得我手忙脚乱,半天才张罗出一桌子凉菜糖果招待他们。那天他们十来个人喝掉了三瓶白酒,并且把桌上摆的几盒烟全揣走了。原来也是阿克哈拉人啊。
亏他口口声声左一个“老乡”右一个“老乡”,五十块钱车费一分也没给我便宜。我说:“哼,别人的车只收四十!”他握着方向盘紧张地盯着路面,一声也不敢吭。
等从县城返回时,又遇到这小子的车。我板着脸,正打算开口,他就抢先说:“四十四十!这回是四十!”
从沙依横布拉克到县城,至少有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无论哪个司机,都会在中途的“可可苏”请乘客吃一顿饭,到了桥头,还要再请喝一道茶。谁教他们收那么贵的车费。
我搭过一辆羊贩子的小卡,倒是只收了我三十块。上车时,后车斗里只系了两只羊,等出了可可托海,就增加至十几只。一路上,他见到毡房就停车,做了一路的生意。我无奈地跟着他四处喝茶,帮他牵羊,替他算账,耐心地生着闷气。我对他说:“要是我坐别人的车,现在已经到了县城又回来了!”
他很愧疚,于是到了耶克哈拉,就给我买了一瓶“娃哈哈”。到了桥头,又给我买了一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爱喝“娃哈哈”。
在冬库尔时,从峡口西面的方向进城时,就会常常会遇到汉族司机了。那时,他们往往比你还要惊讶:“汉族?是汉族吗?你一个汉族,跑到这里干什么?”
那次,我天不亮就出发了,骑了三个小时的马,穿过三条山谷,两座大山,又绕过一个高山湖泊,经过两三个前山一带的小村庄,才到达能搭车的一条土公路旁。送我的斯马胡力把我的马牵了回去,我又独自等了两个多钟头才拦住一辆拉铁矿石的大型重卡。天哪,那天,二十公里路足足走了三个小时。车太重了,不知超载超成了啥样。
这三个小时里,那个司机不停地说话,说得快要吐白沫了。我也算是个话多的人,但遇上这一位,只好闭嘴——因为实在找不到插嘴的机会。我想他一定很寂寞。
他是河南人,才二十四岁,跟着一个本地老板来新疆干活。刚来不到一年,除了喀吾图,新疆哪儿也没去过,工作又辛苦单调——想想看,每天都以二十公里/三小时的速度在这条光秃秃的土路上来回,沿途一棵树也没有(环境有些像吉尔阿特),偶尔出现的搭车客全是语言不通的哈族。
等聊完了自己,他又开始聊家庭。他幸福地告诉我,自己刚结婚两年,孩子八个月大。等下个月老板结一笔账,第一件事就是寄回家买台空调。然后又向我请教,空调的哪个牌子比较好……感觉很怪异。在这条荒凉的土路上,在这异常缓慢的行进途中居然聊起空调的牌子……太不真实了。
聊着聊着,就熟了一些。于是这家伙又开始向我倾诉他对他老婆的爱情,说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是如何中意云云,还背诵起他给她写的第一封情书。
等再熟一些的时候,又忍不住向我透露他深藏的一个秘密。原来他还有一个小老婆——怪不得这么拚了命地打工,原来要养两个老婆。
他痛苦而略显得意地谈着这份计划外感情,并津津有味地描述了自己在两个女人间周旋时的种种惊险。
接下来还能怎么呢?以此种情形看来,只能越来越熟了。于是他又微微悲观地向我阐述他的人生观和爱情观,还认真并且深沉地说,其实,他真正喜欢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我无比惊吓!只好尽量不吭声。但不吭声又觉得大不对头,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大孩子,我要当真和他计较,就压不住阵势了。于是,便开始比他更深沉地发表看法,并且尽挑一些他绝对听不懂的词儿,组织成逻辑混乱的句子,以营造距离感。
幸好这趟行程只有三个小时,否则真不知他往下还要对我说出什么惊天的……来。
我想,大约由于这样的行程实在太漫长、太单调、太疲惫了,他便渐渐地把握不住自己的真实心意,无法确定此时此刻的想法,只好一边不停地叙述,一边不停地改变主意,不停地构思,不停地更换相处方式……以平息自己突兀的热情——它曾被漫长荒凉的寂寞所压抑。
上车时,讲定价钱是二十块。下车时他坚决不收钱。可我哪敢不给啊……
到了喀吾图,就全是熟人了,先串串门再说。还没串到第三家,就有司机找上门来大喊:“听说有人刚刚下山了,要不要去县上?”消息真灵通。对我这样一个刚下山的野人来说,无比繁华的喀吾图其实也是个小地方。
那辆车上坐的竟全是汉族人,真亲切啊。并且聊天内容地道多了。大家纷纷猜测我的来路,我高深莫测地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放羊的。他们当然不信,推理了一路,最后大家一口认定我背景深厚,肯定是高官子女,专门下基层夯实群众基础,丰富政治履历……等到了地方,我们还互留了手机号。天哪,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而且还全是汉话!
到了县城,汉族人就满街都是了,但我已经顾不上体会那种汹涌的亲切感。接下来还得马不停蹄地继续坐车——去阿勒泰的班车马上要开了!急忙买了一份凉皮(啊,亲爱的凉皮,好久都没吃了!)和两瓶酸奶就往车站跑。买了票就赶紧上车。
由于凉皮味很冲,为了能自由自在地吃,我特地坐到车门口司机旁的那个可以折叠的小椅子上,远远避开车厢里的乘客。结果车开动后,不时有人拦车上来,车停了又停,车门开了又开,我只好不停地匆忙起身让路,酸奶、筷子和纸巾不时滚落一地,很狼狈。司机慢悠悠地说:“别着急,慢慢吃。怎么就饿成这样?”直到上了公路才安静下来。那时我也吃完了。司机似乎百无聊赖,又问:“为什么不吃了?”“吃完了,饱了。”“怎么可能?一份凉皮能吃饱?!”——他不由分说,从座位旁掏出一个大苹果扔给我。真幸福啊。我咔嚓咔嚓吃完后,他又问了一遍:“这回饱了吗?”不等我回答,又说:“再不饱的话就没办法了,苹果没了。”车上的人都笑了。明明是他强迫我吃的。
后来他渴了,我就掏出自己的酸奶给他喝。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旅途很温暖。
由于这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六点就从冬库儿出发了,骑了三个小时的马,倒了三趟车,已经很疲惫了,便渐渐沉沉睡去。往下还有四个小时路程。公路正在翻修,汽车不时拐下路基,在漫天尘土中摇摇晃晃前行。
常常在山野里搭车的话,会成为某些司机的回头客。那时我们会惊奇地互相说:“咦?是你?又见面了!”寒暄完毕,司机一边打方向盘,一边叹息:“真看不出啊,都已经是有小孩子的人了……”我大吃一惊:“胡说,我还没结婚呢。谁说我有小孩?”他也大吃一惊,差点踩刹车,嚷嚷道:“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嘛,上次还说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奇怪,我居然也会如此无聊。
另外,作为在这深山里来去多年的人,在很多第一次进山的汉族人面前,我是很有底气的。陪老司机们吹嘘起最最艰险的库委大坂(在修路之前,那个鬼门关我至少经过了十来次)啊,冲过塌方路面的惊险瞬间啊,种种翻车经历啊……嗓门大,手势强有力,听得满车人默默无言。非常过瘾。
一次也在喀吾图转车时,同车有一个文静的高个子汉族女孩,说话举止像是城里孩子。开始一直静静地听我和司机聊天,后来,突然主动搭话,叫我“娟娟姐姐”,并很有些害羞地问我记不记得她。看我一脸茫然,又细声细气地解释自己是谁,说我们曾经是邻居。还说她小的时候,我经常领着他们一群孩子到处玩,还教她们跳过舞呢。我想了又想,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当年喀吾图的确有一群两到八岁的汉族孩子,常常来我家杂货店闹事。而眼下这个孩子都已经念高中了,成了真正的大姑娘了。当年的我也不过十八九岁。
——哎,居然还教人跳舞!想不到我年轻时居然如此活跃,还是社区文艺骨干。
能被人记着,尤其是被孩子记着,一直记到长大,感觉真好。哎,我的群众基础,不用夯也很实啊。
不知为什么,提到搭车这事,还总会想到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一位朴素而庄重的老妇人,拄一把非常特别的手杖。是手工削制的,用草汁染料染成不太匀净的黑色,一定用了多年,凸出的木节处全磨出了原木色。这本来应该是一根简陋平凡的拄杖,可上面却镶钉了许多菱形和圆形的纯银饰物,使之成为极体面的贵重物品。当时,她正拄着这根手杖纹丝不动地站在路口处等车,但是并不招手,也不呼喊,只是站在那里,像女王等待摆驾的仪式。
司机在看到她后,立刻关闭了音乐,并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慢慢减速,最后几乎是无声地停在她身边。他摇下玻璃,满车的人轮流以最繁复的礼仪向她问候。等这位老人上了车,司机重新打开音乐时,特意拧小了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