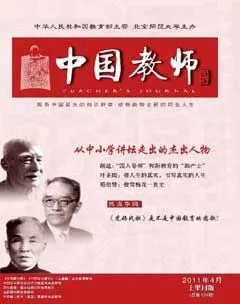从专识教育到通识教育
2011-12-29王庆
中国教师 2011年7期
2010年9月15日《参考消息》有一则消息,题目是《就业难与招聘难现象并存:外媒称中国教改势在必行》,其中有中国市场研究集团总经理肖恩•赖因在9月7日美国双周刊《福布斯》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令人惊异的失业问题》,该文章说:一方面,有很多中国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从高盛、英特尔到微软等公司都想大幅增加员工,却又招不到合适的员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赖因认为:“在过去30年里……中国社会几乎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远的改革。不过,高等教育制度却远远滞后。……如果中国想阻止社会动荡……首先就要改革教育制度,接受跨学科思想。”[1]其实,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呼声早就喊响了,可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制度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高校毕业生仍然存在专业知识及视野过分狭窄、工作中的调整和应变能力弱等问题,而且还有愈加严重的倾向。当前,每一个热心高等教育的人士也都在谈论如何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2010年5月2日,全球120多位大学校长齐聚南京,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纵论如何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作了《中国本科教育缺什么》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缺乏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本科教育是一个专识教育,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再选择一个学科进行学习。接触多个学科使学生有能力去对付一些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对不同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通识教育的模式。”[2]
莱文教授看到了中国大学专识教育的弊病,建议采取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式,这对我们思考大学教育以及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大学教育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特别注重专业知识及技术人才的培养,为新中国输送了大批的急需专业人才,为国家的各项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高等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学生数量、学术研究水平和办学理念等方面都比此前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同时,社会的人才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加入了更多的“创新”“一流”“前沿”等元素。为此,众多高等学校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战略,而且都从各个层面大力推进改革以期实现预期的目标。有些高校把“培养创新型人才”“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长远发展目标。如果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具有领导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占领世界学术的前沿是不言而喻的。但要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又谈何容易,并非能一蹴而就。除了要有相应的合理的学校管理体制、学术评价机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充足的人才储备。我们不能依靠海外的高等教育为我们提供人才,而应该更新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理念,自己培养造就我们所需的人才。“通识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高层次目标,这是保证我国学术长远发展所需人才的基础。
其实,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史上并非什么全新理念,早期的清华大学就有这种传统。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强调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并且开始在教育中倡导和实践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成为清华教育理念重要的成果。”[3]曾在清华学校学习、后来又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潘光旦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谈留美生活》中说:“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4]潘光旦先生讲的“通才教育”,说得普通一点,就是一种旨在开阔人的思想及智力的宽泛教育,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技能的培训(directed chiefly towards the broadening of the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