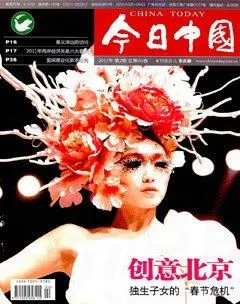淡
2011-12-29李国文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1年2期
刚刚过去的2010年,农产品涨价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辣翻天”、“油你涨”、“糖高宗”、“苹什么”……从这一串串网络调侃涨价的名词可以看出,这些农产品集体上演了一场涨价的狂欢舞会。
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有着诸多原因,社会普遍存在三种解释:“供需失衡说”、“中间加价说”、“热钱炒作论”。笔者认为这些并非其上涨的根本原因,它们只能短期影响农产品价格。从近年猪肉价格能稳定于高位可看出,去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其内在合理性,它们被低估了数十年,本身就该涨了,上述复杂多样的因素只是引子。
由于历史原因,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城乡建设方面存在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体现在生产上便是“重工轻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稳定农产品价格,促进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如今,理应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否则,农村全面实现小康将无从谈起。
事实上,以往农村低成本耕种——拼土地、拼劳动力等粗放型增长时代不复存在了。近些年,很多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大规模租地经营,抬高了地租。而全国各城镇郊区争相将农田开发为房产或工业区,使土地年收益立马增值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浙江省义乌市某城郊村一亩地盖房子出租的年收益是耕种农作物的数百倍。这都催高了农产品生产的土地成本。
有关劳动力方面,放眼中国中部数个产粮大省的农村,四口之家耕种6-8亩承包田全年的收益不会超过6000元。而在北京建筑及装修行业,无任何技术的农民工工钱已达到150元/天。于是数百人的村庄,在家的青壮劳力不用十个手指头就能数完。
可以说,农产品“高成本时代”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意味着长期被低估的农产品正通过涨价回归价值,进入趋势性的上涨通道。
有相当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农产品涨价通道中,菜农果农从农产品涨价中受益甚微,其大部分利润都归之于流通领域。也有媒体记者深入其流通渠道实地采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利润没有真正达到农户手中,而是被过多的中间环节蚕食”。
笔者认为,得出这种结论的记者首先缺乏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批发商2010年或许能以2元收购到后来市面上卖8元的苹果;但2011年卖8元的苹果收购价肯定会涨到4元。原因很简单,如今社会信息如此发达,果农并不傻。
其次,媒体记者忽视了一个常识:从消费终端追溯,产品的利润从来都是流通环节拿的多,绝大部分工业品也是这样。以流通、零售方面市场化都非常成熟的矿泉水为例,超市终端每瓶卖1元的“哇哈哈”,出厂价也不到0.6元。日前“康师傅”与“家乐福”的纠结也是如此。
社会为何对农产品多重而具时限性的流通环节如此苛刻,对其合理利润不甚谅解?要知道,各大中城市从事蔬菜、水果等的流通环节的,大部分也是农村出来的农民。他们中有些是有头脑、敢于承担风险、先富起来的个体批发商,有些是各社区里起早摸黑的小摊主。没有他们的春节期间,社区里的蔬菜价格可是翻倍地涨。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和生产者,这是个看似矛盾的两难问题:“谷贱伤农,各贵伤民。”
农产品价格急涨,市民显然要投诉,甚至怨声载道,但归根结底受益的确实是中国农民。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是压制了全中国几代农民的利益诉求而取得的,继续指望人均耕地非常少的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保持低位是不现实的。
如今投诉莱价的市民,还是比大部分农民生活得好些。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低收入者,而抑制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政府该做的事。笔者认为,即便是农产品持续涨价,使得大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收入者高,也是应该的,毕竟两者的劳动强度不一。
据统计,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7.9名;农村居民家庭为43.7名。这两个百分比便是国际通行的恩格尔系数,百分值越小,生活水平越高。从长远来看,要让农民的生活水平追上市民,唯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才行。
目前个别地方政府生硬地采取“限价令”,直接用管制价格来稳定农产品价格,显得简单粗暴,违背市场规律,终归是得不偿失的。政府应学习并借鉴“大禹治水”的办法,多做些疏导和监督工作:尽快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经济组织化程度,在生产设施、信息服务、储藏物流等环节加大投入,以保证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上涨幅度不至于失控。
农产品价格还要“飞”,目前尚未大涨的农产品在未来数年内将轮番上涨。以淡水草鱼为例,目前零售市场草鱼大概6-8元/斤,而10年前,草鱼零售价也在5-6元,斤。扣除10年通胀因素,草鱼价格实际上没有上涨甚至是负增长。可以说,如果有游资进行炒作,草鱼“飞”至12元/斤也不是没有可能,从食用价值来看,它应该接近于猪肉。
2010年各种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既是补涨的过程,又是农产品价值的理性回归。可以说,中国的农产品尤如2005年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价格快速增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