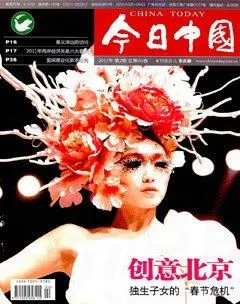“胡同台妹”的大陆情结
2011-12-29林皓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1年2期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个叫官铃的台湾女子,以“胡同台妹”的网名混迹于网上,与大陆博友隔空交手,被称为“在大陆互联网里走得最远的台湾人’。
官铃祖籍安徽,是典型的台湾外省人,有着10年的媒体经验。三十多岁时,把自已丢到了这片“以为熟悉,其实一点也不熟的土地”,而且一丢就是五年,她称这段时间是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段落。曾经非常失意(她提醒自己“没落贵族即便没落也不改其气度与优雅”),也曾经光彩夺目(2005年“两会”上提问温总理,以及后续所做的大陆网友问答马英九)。在她看来,北京就像是前世一趟未完的旅程,这一世百转千回到这里继续。有人以为她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实际上她住不起四合院,而在拥挤的望京租房。
官玲笔下,记录的是一个台湾资深女记者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无怪乎会引起大陆网友的强烈关注。在她看来,写书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没想到那么痛苦。“因为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这绝非容易。写作期间,她历经了忧郁的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
她挨过的板砖,典型的一次是,北京警方当场击毙一位劫持女童的嫌犯后,现场和网上一片叫好,唯独她不合时宜地说:“永远不能赞成或默许执法者‘便宜行事’,这是底线。否则,就别抱怨,有天这‘便宜’落在自己头上!“我不反对击毙,但击毙之后,必须要经过调查确认,情节严重到值得击毙!”
果然,她成了“冷血动物”,以及“被民主洗脑的白痴”。最多的质疑是:“假如你是小女孩的父母,你还会这么想吗?”“假如你在现场,你能保持冷静吗?”宫玲觉得这两个问题都缺乏逻辑:孩子的父母当然恨不得嫌犯死掉,以确保孩子安全,可是不能要求整个社会都像孩子父母一样思考问题,更何况讨论的是“事后检视”。至于冷静问题:“你是特警啊,你就是处理这个的,你不冷静谁冷静?”
被骂了两天,她去找一位大陆媒体朋友诉苦:“是不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够大陆,他们都听不进去?”朋友回答:“是你的整个思维方式就不大陆……”
在北京生活了5年,宫铃至今记得她的“第一次”,是2004年6月17日,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看到“北京”二字挂在机场大楼上,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从小听姥姥操着京腔,讲北京的典故,她总是说:“我们家在北平可是住在紫禁城后头儿。”
当时驻扎期限是3个月,忙得翻天覆地,无暇去看姥姥的天安门。临行那天,采访车送她回家。司机听说她的“遗憾”,不顾夜深,专程绕路去了趟天安门。月光下,官玲打开车门,让双脚在长安街上踏了一下,兴奋地说:“我终于来过天安门了!”
官玲喜欢北京的辽阔与苍茫,“尤其在黄昏时分,几个大街道,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与车阵,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身在大城市的英雄感。”虽然在北京只有五年,但她在这里的成长与历练,比起台湾的30年,“感觉更多更多”。
宋楚瑜为宫玲的书做了推荐序。他说:“两岸不只要三通,更要心灵相通。只有两岸双方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消除‘误解’,产生‘谅解’,再找出方法‘化解’,进而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
“对于这本书,我唯一能够掌握并负责的就是‘诚意’。”宫玲说。“如果两岸真能够亲如手足,如果两岸真能毫无芥蒂私心的合作,我想,我就勇敢并努力的做这个先行者吧,从民间开始,从自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