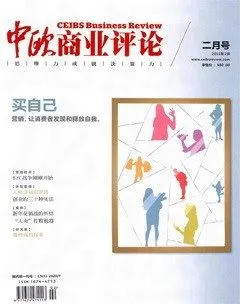终结外企“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2011-12-29穆胜
中欧商业评论 2011年2期
“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资企业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宣布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至此,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消息一出,外资企业齐声抱怨,纷纷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表示了“失望”,对前途感到“灰心”。
应该说,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我国面临巨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虽然此举将挤压外资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一些仅仅依靠中国市场规模得以生存的外资企业感受到强烈冲击,但中外资企业间的重新洗牌,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也正是政策导向用意之所在。换句话说,“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资企业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新木桶原则
尽管当前外资企业获取了不菲的盈利,但未来的中国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庞大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必将引致更多国外投资者前来逐利;另一方面,在愈加公平(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规则下,更具竞争力的本土民企也有可能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竞争的加剧将带来更多的产品供给,也使消费者的偏好更加难以捉摸,出于对这种风险的敬畏和觊觎消费者个性化偏好背后的巨大商机,企业必然走到一起,共同缔结价值网络。因此企业会由“大而全”走向“小而精”,收缩规模边界,纵深打造某一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结网进行联合。
结网这一企业间合作模式的转变,首先将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从成本上看,企业可以退出一些效率不高的领域,减少无谓的成本消耗,获得更大的柔性;从收益上看,能够以精准的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自由组合,通过杠杆效应获得自身缺乏的资源和能力,以联合生产的形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效应可以用“新木桶原则”来比喻,即众多企业放弃自己木桶中的“短板”,而将各自的“长板”放到一起,共同把“木桶”做大,以便找到丰富的“水源”,装更多的“水”。
其次,结网也会带来更加频繁的交易机会。由于企业并未被某一价值网络锁定,一旦其不能在网络上获得最充分的利益,在信息和运输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为不同的网络服务。即企业的“长板”再参与到“木桶”的组装,完成一次“装水”后,又可以参与到其他“木桶”的组装中。这样,企业由于规模缩小,退出产业链上某些盈利环节(放弃“短板”)的损失,可以通过资产更加频繁的组合变现进行弥补。
可以发现,新格局下,一方面,市场中的资源将流向由客户需求导向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型;另一方面,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也可以实现“强者通吃”,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事实上,从大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新格局的产生正是产业演化的必然趋势。
但这种意料中的演化却在我国遭遇了困境。部分外资企业在“超国民待遇”的庇护下,依靠成本优势,肆意通过扩大规模汲取利益。既得利益让它们不愿意寻求自身的改变——提高生产效率和进行技术创新。其行为不仅给我国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挤占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形态的良性演进。如此看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洗牌行为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新格局下的中外药方
新格局必然存在新的生存法则,价值网络中谁主沉浮,犹未可知。外资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应该开始思考如何适应未来的企业新格局。
鉴于不同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的差异,笔者暂且把外资企业粗略地分为三类,试图分别为之开出药方。
类型一:拥有品牌、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外资企业。其应该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价值网络中的“舵手”,通过灵敏地识别市场需求,指挥网络成员协同生产,获得组合创新优势。由于控制了整个网络,此类企业将拥有网络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往往获利最为丰厚。
类型二:拥有某一领域技术特长的外资企业。其应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供应商,获得基于技术创新的“熊彼得租金”。这些企业承接的零部件通常是终端产品的核心,自然也能获得丰厚回报。
类型三:仅仅拥有通用技术的外资企业。其应该争取融入更多的价值网络,为更多的终端产品供应零部件,获取基于生产经验和规模经济优势的“李嘉图租金”。基于其较小的贡献和极低的风险,此类企业无法在某一价值网络中获取丰厚回报,只有争取为更多网络服务,以规模取胜。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并无优势可言,除非其引进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仍是技术之争)。
而本土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也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新规则。以往,本土企业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往往是以OEM(贴牌生产)的生产方式融入产业链,主要承接生产加工任务,获取微薄利润,而想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又苦于外资企业的“整体技术壁垒”。倘若价值网络的时代来临,这种壁垒就有望被突破。
取消“超国民待遇”后的外资企业必将收缩规模,退出某些技术上的非核心环节,此时,“整体技术壁垒”就出现了裂缝。本土企业完全可以先以OEM的模式进入价值网络;然后逐渐承接部分设计任务,转型成为ODM模式(委托设计制造);接下来承接服务环节,转型成为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最后,转型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EMS(工程、制造、服务),而此类企业也通常被称为“交钥匙企业(turn-key)”。
这一过程中,企业已经掌握了“知识诀窍(know-how)”,而剩下的选择,就是“向前一步”建立自主品牌成为网络“舵手”,或者“原地不动”、甘当“专用技术供应商”的问题了。前者的典型是格兰仕,从单纯代工到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就后者来说,国内缺乏成功案例,但在国外,Solectron、SCI和Celestica之类的EMS虽然没有自主品牌,仅凭借为苹果、惠普、IBM提供解决方案,其业务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一度被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
可见,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终将被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市场主旋律所取代。未来中国市场将是全新的舞台,相应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也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