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信息公开 亟待制度规范
2011-12-28■米一
■米 一
官员信息公开 亟待制度规范
■米 一
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其个人隐私并不能与一般民众等量齐观,而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渡。如何让官员从“衙门深深”走向公开,进而更好地接受公众监督,需要一系列制度来规范。
2010年11月,《嘉兴市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预备人选公告》在嘉兴党建网“红船网”面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首次晒出了15名拟任提拔干部的家庭成员情况。
2011年1月,富阳市推出干部考核新模式,考察干部8小时以外“私德”情况。这些内容包括:生活作风、家庭关系、有没有拖欠物业费、有没有在小区乱停车等。
…………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纷纷把“晒家底”、“亮私德”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内容之一。不少政府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做法是为了让官员的考核更全面,也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而这,也让人们看到了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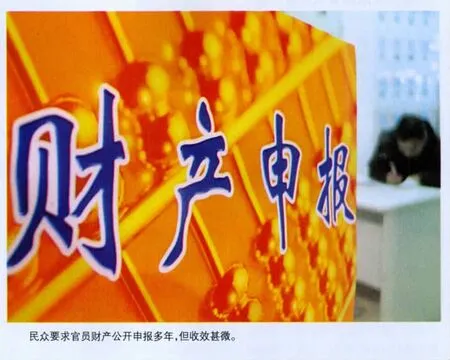
官员信息公开迈出第一步
相对于如今各地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如火如荼,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员对个人信息讳莫如深,民众对此知之甚少。这一局面,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1995年以来,中央先后发布了多份有关领导干部信息公开的文件,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等。政策层面的推动,掀开了官员个人信息面纱的一角。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官员财产公开乃至个人家庭情况公开等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官员信息公开的制度化。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民间对于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推动。在“天价烟局长”、“局长日记门”等网络事件中,颇具争议的“人肉搜索”让官员们看到了公众监督的力量。而在“最年轻的市长”等一系列公众质疑官员选拔公正性的事件中,人们看到了百姓民主意识的觉醒,期待通过官员个人信息的公开,加强对官员乃至公权力的监督。
这些民间与官方的合力,把曾经躲在“衙门”深处的官员从幕后推向了台前。然而,细观目前的种种举措,面向的多是组织内部,如官员收入和家庭财产只要求向上级部门申报、报告,“只报告不公开”、“报告留作待查”。这些“公开”都不面向社会公众,只属于内部监督,因此是有限度的,算不上真正的公开。此外,在公开的内容上,也停留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如多集中在官员的个人财产方面,很少涉及官员配偶的从业情况和子女的受教育及从业情况等。
2010年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5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8%的人觉得当前官员个人信息不透明,81.7%的人期待官员信息充分公开,其中49.3%的人表示“非常期待”。公众对官员信息知情权的呼声之高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现阶段所谓的官员信息公开,离民众的要求还很远,虽然符合了民主发展的趋势,但只能算是“公开”的第一步。
接受公众监督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让官员公开包括个人财产甚至家庭成员情况等信息,之所以进展缓慢甚至遭到部分官员的反对,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内容属于官员的隐私范畴,没有人愿意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然而,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公开部分个人信息,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在现代政治学中,有一句话最能描绘官员在对待隐私被公众放大镜般关注时应当持有的心态:“你要是受不了蒸汽熏,就别进厨房。”实践中,公众永远都想知道得多一些,官员则希望透露得尽量少一些,两者始终处在博弈过程之中。
从各国实践来看,作为公众人物,官员的隐私权范围比普通人要窄,他的行为和言行都要受到严格制约。“任何官员都不能以保护隐私为由,将私生活置于无人监管的真空地带”。这也被认为是作为公共人物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不少学者指出,当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应采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保护公民知情权,限制官员隐私权。这是因为权利本位并不等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当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一些个人利益是可以被限制或否定的。“公民知情权对官员的隐私权的限制,实际上构成了民主运作的一个环节。”一位学者如是说。

在分析浙江嘉兴等地的“公示拟任提拔干部家属身份”事件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解志勇认为:“这些做法的更大价值在于,它通过增加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内容,实现了对官员隐私边界的收缩,并在无形中再次宣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在公共利益面前、在监督制约权力的法治原则面前,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其个人隐私并不能与一般民众等量齐观,而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渡。否则,官员一面希望执掌公权,一面又不愿意牺牲部分个人隐私权,那么,被牺牲的必定是公众的知情权。”
事实上,官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他们掌握和支配着权力以及其派生的包括财政在内的宝贵资源,这对公众利益的影响是巨大的。按照现代政府运作的规则,公共权力必须公开透明,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公权私用,即防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好处。因此,官员的学历、出身、财产状况、任职能力、品德操行、廉政状况都直接影响到其能否胜任职务,影响到一个有效的政府或国家管理的实现,最终影响人民的公共利益。
“从公共管理学上讲,既然官员是公众人物,握有公共权力,那么官员的行为,包括8小时以外的行为,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哲学博士竹立家说,“因为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话语体系中,官员是从奉献角度、为公众服务角度来行使和运用公共权力的。公众赋予官员以公共权力,是对官员的信任。相反,官员要取得公民的信任,就必须把自己的行为摊在阳光下。”
“公众关心的并不在于其该不该位居要职,也不在于是否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而在于其从政之路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存在‘暗箱操作’。”浙江省嘉兴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谈到“晒”干部家庭成员情况的初衷时说。正因此,由于掌握着影响公众利益的公权力,官员必须要让渡出一部分个人隐私来接受公众的监督。
期待制度解困
虽然在官员个人信息公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各地创新举措的五花八门,也让人们担心当热潮退去,官员个人信息公开是否仍然遥不可及。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学者直指如今热议的“官员信息公开”尚不成熟,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
“首要解决的,是对我们俗称的‘干部’、‘官员’的具体范围的界定。到底是哪个层级以上的人员需要公开?在欧美许多国家,政府公职人员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只有政务官才会涉及公开的问题。哪些才是公众人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韩福国告诉记者,“此外,县、乡镇一级做了,省、市这一级呢?现在各地的做法缺乏系统性。”
“‘干部’一词把所有人都概括了,应当有所区分。”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解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在日本等一些国家,官僚的隐私权是得到保障的,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务官,才需要将个人信息‘晒’出来。而在我国的公务员体系中,并没有这样的划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在官员信息公开的做法上并不统一。如中央只要求处级领导干部必须进行财产申报,但不少地方均扩大了该范围。如浙江的临海市将级别下调到副科以上,但只针对新提拔的干部。此外,大多数地方的做法只是针对拟任官员的信息公开,现任官员的信息何时才能真正公开仍是个未知数。
而对于官员信息公开的内容,各地的情况也不相同。从家庭财产状况到父母、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的社会身份和财产状况,甚至是电话等联系方式,五花八门。但究竟哪些是与官员行使公权力相关、哪些是真正需要公开以接受监督的,依然无章可循。
更为吊诡的现实是,一方面,许多官员应当让渡的隐私权,往往没有让渡出来。比方说官员财产公开,社会舆论呼吁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落实。另一方面,官员应当拥有的隐私权,却往往受到侵犯。如重庆市酉阳县日前给每位党政干部发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让人感叹这样的监督未免把手伸得太长。不得不说,对于官员隐私权的认识和保护,眼下是存在扭曲和错位的。此外,不少官员自身缺少公共意识,更多地停留在被动公开的层面上;即使是主动为之,也带着“作秀”成分。
“谁来监督官员公开的内容?如果公开不实,怎么办?”不少网民还提出了这样的担忧。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规范。
2011年6月22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谈道:“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而对于官员信息公开,更是如此。
“不能为了公开而公开。”韩福国向记者强调,“必须注重制度建设的整体性。如果仅仅是一个公开的做法,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是不具有效率的。每个环节必须联动起来,才会有制度创新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