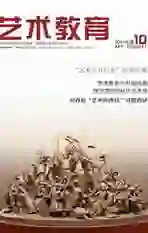艺术教育与创造性思维
2011-12-19戚灵岭
戚灵岭
在大多数人看来,艺术创作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是与艺术家或艺术作品密切相关以及有别于常人逻辑思维习惯的一种行为与方式。然而,若仅仅就是这样,古往今来凝聚着人类无穷智慧与创造力的艺术之作和艺术家们会否感到颇为沮丧呢?
值得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非凡创造力,作为人的一种特权,曾被往昔的一些艺术大师们看成是回应上帝赐予人性优良品性的某种彰显。毋庸置疑,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创造性思维模式的成果,颂扬了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道。如果说宇宙之神的创造显现于从无到有,那么,人类的创造力则是依据大干世界中早已存在的、可以利用的却无法预料的变化产生而来。人类将由此阐发的想象与幻想转变为人自身最优秀成果的这一过程,即艺术创造过程本身。
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大学教学改革的复兴运动,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其中不乏最先意识到恢复拥有人类创造性思维方式与功能的人文用语中所体现出来的优美感和艺术性对于人性价值的体现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优秀前辈。1492年,德国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特斯(ConradCeltes)甚感悲哀地感叹道,那些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师用语尽是这样缺乏优美感和艺术性,他们使用鄙俗、讹误的语词和信口而出的句子,粗俗、野蛮地糟蹋优美的罗马语言。他在给因戈尔施特大学(IngolstadtUniversity)的信中即写道:
“在这么多世纪里,这么多宣称具有学术优势的德国大学中,居然没人能用文明和优雅的方式写信、写讲稿、写诗、写历史,而意大利却不是如此,那里大学不多,但很有质量。我为德国感到遗憾,因为在那么多的大学中,我不曾发现有人讲述西塞罗(Cicero)。
在北方,恢复西塞罗等传统文人优美语言的迫切需求与大学课程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1338年,彼得拉克本人曾在其用拉丁六韵步体所写的名为《阿菲利加》(Afrlca)史诗起首的诗行中表述了自己的心愿:
我希望,我盼望,你(指诗歌)能比我长寿。未来的时代将会更好。在今后的岁月里不会再有健忘的沉睡。一旦黑暗划破,我们的后代也许能恢复纯洁质朴的光辉。”
值得庆幸的是,彼得拉克所期盼的“恢复纯洁质朴的光辉”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曙光。然而,如果我们对产生这一切的特定情境做详细的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明智地探讨促使这场运动在其所处社会产生影响力的真正原因。正如伟大的北方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Erasmus)于1517年所分析的那样:
苏格兰人、丹麦人和爱尔兰人现在正在耕耘几乎绝迹的纯文学园地。
正是在以上这些文艺复兴先驱者的种种努力下,艺术犹如植物复苏一般得到了复兴,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绘画与雕塑失而复得。评判优秀与优美的绝对标准亦在拉丁风格中,在由西塞罗和伟大的古典作者制定的表现风格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古典作者”被公认为是模范的作者,古典文化时期业已作为相对完美准则的象征,表述了人们的一腔寄托。文艺复兴及人文意识的觉醒告诉我们:艺术的创造力有赖于其生长或教育的人文环境,体现在每一个自我与个体所具有的功能之中。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创造力不仅体现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同样也蕴涵于每一个人的创造潜能之中。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杰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所具有的非凡艺术创造力,正是普通人在变动和改造旧事物时放弃某些通常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集中表现,是深深扎根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之上的。
人的这种能力同样还表明了,艺术的创造性基于的是其本身所拥有的整体谐调局部功能的特性。非此,则难以成就艺术的使命。每一个接受过艺术技巧训练的人,都能感受到艺术表现所具有的这一悖论关系。一个歌唱者,不可能在每一个音的音质都练习完美后,或在所谓的固定法则完全掌握后才能唱歌,只有在整体歌唱过程的谐调及其带动中,才有可能出现歌者与听者所向往的局部发音的优美与动听。一个绘画艺术工作者,从最初学画时,即被告知抓整体的重要性,唯有在整体位置的谐调中局部方能突出。这个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及想象与抵达想象的路径——技巧,犹如音乐中的节奏,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的律动。然而,这个节奏是有呼吸的节奏,是混合与无穷变化着的节奏,它们同处于一个矛盾体中的整体循环系统之中。正是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循环与统一,使得在艺术创造性思维引导下的各种艺术形式,不仅使人获得满足感,消除受挫感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与判断事物的标准。其告诫人们,人的一生始终都不应放弃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培养有利于人体机制本身能够正常运行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上。正常运行的人身体本身所产生的思想是整个人体宇宙的冰山之一角和人类思维的基础与平台,人的整个生命进程不但具有个体与永恒的不可分性,更是一个积极、广博、包容、富有生命脉动与吐故纳新的呼吸综合体。在宇宙的摇篮中,艺术家深感自己是那么渺小,却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这或许就是艺术创造力的奥秘所在。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人类共有的一种普遍的创造力时,我们深感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社会因此而出现的诸多弊端或认识误区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纵观我们周围的环境,多少家长、学子,他们是那样忙于保护自身或自己的孩子免遭命运的不测,却未曾意识到去建立和培养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与成长的思维方式与实际的能力,更不要说是创新发明的领域了。如果说我们以上提到的对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低估以及对创造力认识不足等现象是一种暂时和部分的社会现象,然而,令人反思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是缘于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和艺术教育上的偏颇等,其影响甚至行将或已经波及我们的后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在幼年被强迫学习各种“艺术”的技能)甚至已经对艺术产生了厌恶。这些被扭曲的思维方式永远难以理解真正的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即其愿意为理想、信仰乃至一种观念的实现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虽然这样一群人经常地被一些既得利益者认为是由虚假的宣传所安排或强加于他们之上的,殊不知,那些过去的“著名艺术家”在其生活的时代或者环境里,他们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我们会赋予他们以名人效应或种种的神秘性,而且当时的人们更不会因我们今天赋予他们的“神秘性”来左右他们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热爱。藉此,我们知道历史与社会的变更不是个别名人或伟人的功绩,而是大众或者整个文化环境变革的结果。“伟大人物”只是其所处环境创造的典型代表或必然的产物。认真研究创造力的人们终将懂得,思想意识与客观环境,伟大人物与具有创造力的人,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虽然我们不能预料每个世纪能否出几个像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这样杰出人物所达到的高峰,但努力接近促使他们所取得的伟大艺术创造力的崇高信念
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进行的深入研究都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不仅仅是由于对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进行探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不完全是由于它将会使我们理解和更好地欣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艺术创造的成果,而是有助于使我们习得一些创造性的生活特点,无论这些创造力是伟大的还是中等的,是普通的还是渺小的。艺术创造活动的过程必将带给艺术家心灵体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同时带给每一个热爱艺术者无穷的乐趣,犹如发动机般启迪着人性中的勤奋与探索精神。
值得反思的是,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同样也反映了人类与低于人类、反映方式有限的动物之间所共有的某种倾向,即按照固定不变的方式进行活动和建立联系的特性。在学习艺术时,人在处理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时,无论采取直接反映的方法,还是遵照复杂的符号与选择的技能,他们都会以一种常规的心理取向及其文化所形成的通常方式去行动。即其一般都会遵循亚里±多德所说的逻辑或正常的逻辑思维,用弗洛伊德分析学的说法就是遵循着激发过程的思维。而艺术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则是一种超出处理周围环境与自身的问题时所采取的通常方式,它扩大了——至少被某些人或被所有人所重视的或合乎规则的心理体验,不受制于社会的影响或赞赏与否。在生命的追求中,他们努力地去超越条件反射的天性并从习以为常的选择中解放出来。诚然,艺术创造力并不是简单的创新和无限的自由。当它运用不同寻常的思维方法时,也一定不能违背正常的思维方法。即其必须是某种能让正常思维迟早会理解、接受和欣赏的行为与方式,否则其结果就不属于创造性思维的范畴。
此外,艺术的创造活动不能仅从其自身来考虑,还必须要从其与世界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关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超越人自身,世界才能与其共存的关系之中。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理解这种真正合乎社会正常发展规律的体验是多么困难1它从人生理上到精神上,从实际运用到理论探索,所涉及的范围又是多么广。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使得人们既能够增添和开拓出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和潮流而使世界更为广阔,同时又由于使人的心灵能体验到这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丰富人的本身这一成果,充分体现于可见与不可见之中。与人类朝夕相处的这一摸得着、看得见、听得到的世界与通过艺术探索所欲触及的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相比是如此的狭小。一幅绘画艺术新作、一首诗歌乃至一项充满想象力的科学成就或哲理认知都能在人类未知的大海中增添一些看得见的岛屿,而正是无数这些新岛屿最终构成了稠密的人类各种文化的群岛。
艺术创造的显著特征告诉我们,艺术创造过程是满足人类追求生命活力需求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与在此之外的经验或实体所表现的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即其不仅在创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而且创作本身亦直接有所显明。特别是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创新中,作品常常不仅表现了物象客体,而且也表现出了创作者本身的强烈渴望,艺术家种种朦胧的追求和持续不断却从未完成过的努力以及蕴涵某种意识和意识不到的动机。因此,认识艺术教育与一般性文科或自然科学教育研究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心灵所具有的一系列直感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个人的内在品质以及过去与当前的经验,然而对艺术创造性思维方式的感悟、认识与确立,则不但关系到能够将精神流露当中证明没有用的成分加以排除,而且还影响到人能否最有效地确立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周围世界的程度来重新限定每个个体的开放性和自主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创造过程是促进和形成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一条必要的甚至最佳的途径。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都有运用艺术的想象力来进行艺术创造、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相反,一个职业艺术家如果对之没有充分的认识,那么,尽管他的职业是艺术家,但其所从事的过程也不属于我们所谈论的艺术创造范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就人类看似自发的,正常或非正常思维表象分析道:它们大都建立在当前的以前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的基础上,有些看上去好像是偶然发生的,却完全是或很大程度上是生物环境与过去生活经验特定结合的结果。它们在数量、顺序、强度以及其他各种特征方面的不重复性,足以解释人的独一性或独创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这一思维特性,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他们都站在同一起点上。然而,一个幼儿到了成年之后之所以会失去独创性而保留自发性,是因其在经历许多个人不同寻常的、非常主观的体验中没有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名称体系及其在成长与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社会给予其的观念与影响所致。当儿童接受了由社会所提供给他的习俗与观念,并学会了大量地使用它们,即我们以上所指出的——使用通常的思维途径时,他们无法再体验到先前通过自己特有的、个人的方式而获得的感受,因为这种独创性的内容是由其所无法回忆的没有名称的经验构成的,而要重新体验所用的是别的不同方式。于此,艺术教育十分有助于恢复人性中原本应有并渴慕的这种方式。然而,在艺术创作的空间里,创作者所依存社会对其理解与接纳的环境,决定着每一个个体得以发挥的程度。事实证明,社会与人的宽容、安全、友好、合作、允让等风气为社会之人的独创性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并制约着人有可能不被周围环境所接受的思想与行为。众所周知,但凡人做梦时,在没有环境的戒备中,他们只和内心的自我在~起。大量涌现的梦幻内容很少受到约束。每一个梦中的人物做着许多独创的事情,即便是重复出现某个主题时,都将发生预料不到的联系。人类在梦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解决内心冲突的心理企图,虽然其不足以与概念过程结合在一起,也不能完全按照原初的形态被他人分享或传达给他人,但人在梦中所体现出来的通常属于不正常的或无意识的人类的原始认识形态,一旦与艺术的创造过程构成一种恰当的配合,即能成为创新的力量。因为,艺术创造的精神并不拒绝这种原始的心理活动,它通过一种宛如“魔术”般的综合,将其与正常的逻辑过程结合在一起,从而展现出新的、预想不到而又合人心意的情景。
无数艺术创造者在他们的艺术创造中,正是以其自身朴实并虚己的品质使得艺术的天国属于他们,在艺术探索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以及由此而带给他们的哀恸,使他们在更深刻地理解艺术真谛中得到了安慰。他们在顺服自然世界的规律中,承受着大自然无私的恩赐,其渴慕寻求创造力源头的信念,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不断丰富着生命的意义,而这种创造性能量激发了人类在其他领域的创造智慧,艺术教育即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源泉。